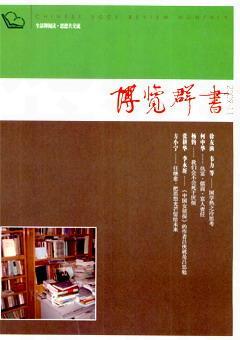慰藉
刘希全
灰暗:稀有的慰藉
“慰藉”这个词出现在一个天空灰暗的午后。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只记得天气有些灰暗,令人郁闷。每到这样的天气,我便会到外面走一走。有时沙子会吹到眼睛里,于是我常常盼望能下起一场雨来,如果能下一场大雨最好:如果不能,下一场中雨或小雨也行:如果再不能,吹来一阵湿气也行。我很简单地想,要是能有一场雨来,眼前的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景象。
奇怪的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有时竟会一下子想起许多的事物,会想起许多的人,包括多年以前的许多场景,甚至多年之前写下但早已忘记的一些诗句,也会返回来。它们一一浮现在眼前,直接,清晰,既汇集交融,又断裂散开,展现出一种无法言说的苍茫和深意。我感到这一切帮助了我,让我在这样灰暗的午后心有所感,心有所动。
就这样,那一天的午后,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词:“慰藉”!
我对于这个词,是陌生的,是远离的。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文字,我几乎就没有写过它,在我的纸张上它只偶尔出现过,对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是不是它在生活中太稀有、太珍贵、太难得,因而使自己潜意识里特别珍重它而不敢轻易地写到它呢?也许吧,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查看了《现代汉语词典》,上面对“慰藉”的解释只有两个字:“安慰。”没想到会这么简单和表面化,我有些失望。“慰藉”与“安慰”是两个不能等同的词语,不应相提并论。
在我的眼里,“慰藉”首先是一个宏大的词,一个动态的、延绵的词(它不是动词,既比动词大,又比动词静),是一个涵盖了开始、过程及结果的词,是一个包含了苦痛、酸楚、喜悦等深厚感情的词。其次,它还是一个细微的词,一个感性的词,一个温暖的词,紧贴着人心。它的凝重和庄严,让人不能轻易将它随口说出来。
母亲:生命的慰藉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对这个词语感受最深的,也许不是作家、诗人,而是天下的母亲。当孩子安全出生,当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她是慰藉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她因分娩而耗尽力气,显得特别疲倦,但脸上却是幸福的笑容。十月怀胎,所有的焦虑,分娩时巨大的苦痛,等等,都过去了,都消失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慢慢长大,母亲的担心和劳累越来越多,但拥有的欣喜也越来越多。比如,孩子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跑,后来上小学了,上中学了,等等。母亲们常常聚在一起,谈起孩子就唠唠叨叨说个不停。孩子的事情,她们都能记得,而且记得最清楚。讲到孩子们的一些趣事,她们常常会大笑起来。这样的场景,只有用“慰藉”才能描述,也只有“慰藉”才能包含和概括。
岁月如流,孩子长大成人,要离开母亲到外面开始自己的生活,母亲就会恋恋不舍,会偷偷地抹眼泪。过年的时候,孩子因为有事不回来,母亲就觉得日子无比地漫长,慢慢地,她的头发就由黑变灰,再后来就由灰变白。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母亲的身影,经常在我的眼前浮现。我用心写母亲,用笔写母亲,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也没有给她看过。父亲去世后,母亲像是一下子老了许多,最近一两年才好一些。现在,我更不能用自己的文字打扰她了。
我前面说过,“慰藉”是一个感性的词,我也愿意感性地去理解这个词。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地与其相融。哦,这句话可能说得有些大。准确地说,是有了与其相融的可能性!
家乡:回忆的慰藉
一个小小的村子,近年来也在我的视野里不时地呈现,这就是山东省莱西市南墅镇南宋村,我出生并度过六年童年时光的地方。
六岁已经能记住一些事了,那时我就知道南宋村是一个穷村,我也知道大人们经常打架,村民们分成了几派,都想把对方搞倒。现在看来很可笑,其中大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比如,有人的菜地里少了几棵菜,马上就怀疑某某偷了,某某听说了就找上门来,不承认,结果双方很快就打骂起来了,各自的亲戚闻声赶来,都帮着骂、帮着打。但没过几天,两家人又和好如初,好像几天前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
到了晚上,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大人们经常会自豪地聊到村里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是我们本家,但关系有些远,我应该叫他大爷爷。解放前是地主,表面上是保长,实际上是地下党。后来,他告别妻子和三个儿子,加入了解放军,南征北战多年,当上了师长。
六岁这一年,因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全家迁居到莱阳。尽管两地相距不到百里,但因种种原因,此后的好多年,我只回去过一两次,平时也很少会想到南宋村。2004年父亲突然去世,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南宋村,把父亲葬在村东的土岭上之后,我才有机会和叔叔、婶婶、堂哥、堂弟们说说话,谈论起过去和现在。那天谈到了那个长辈,那个师长。四叔告诉我,他前些年也去世了,骨灰现在西安,听说以后还要迁回来,坟地都准备好了。不过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村里人的生活和命运,比如某某早就死了,某某是前几年死的,等等。说实话,对谈论到的人,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四叔说我:“真忘了?你小时候整天往人家家里跑。”见我真的想不起来,四叔有些不太相信。
那些日子,我还祭奠了爷爷、奶奶、大伯、二伯。在他们的坟前,我下跪,叩首。他们去世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他们最后一面,都没赶回来。父亲和四叔都是在事后告诉我的,说路太远了,回来一趟不容易。
说这话的父亲,已经不在了;而四叔,现在头发也早已花白了。
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谈话,引起我强烈的心灵震动。我想到了许多许多,心里很乱,久久不能平静。在我的眼里,南宋村,绝不仅仅是地域上、地理学上的南宋村。它是简单的,只有几十户人家。它又是繁复的,对我来说,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村庄都要大,并且意味深长。对南宋村,对它所涵盖的一切,我感受着,理解着,既以它理解自己,又以自己理解它,彼此确认,彼此唤醒,彼此想起。我力图使南宋村在众多的地址当中,在模糊不清的背景中,变得清晰一些,变得近一些。这两年来,我写下并发表了多首关于南宋村的诗作,感到安心了一些。
四叔和南宋村的亲人们,是不会看到这些诗的,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不想打扰他们。我只告诉自己:南宋村清晰一些了,南宋村近一些了!
这几年。我回过南宋村两三次,每次回去,感慨都很深。不知为什么,每次回去,就想再多写一点南宋村,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写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冲动,也随之越来越强烈,这两种念头彼此相连,但又完全迥异,界限分明,像是对峙,但又像是呼应。在这个年代里,在我的纸张上,在我的诗歌文本里,它们通过具体生动的自身,仿佛建立起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具有长久联系的、别具深意的特别关系。
“慰藉”这个词里,有现实生活,有人生,有生命,有疼痛,有爱,有回忆,有遐思。它们的存在,以及对它们的体验、描述和叙述,是真实的,是持久的……
(本文编辑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