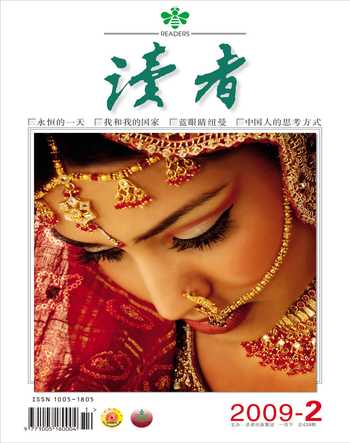门为谁开
程玮
2008年10月初的诺贝尔奖,倒是让不少中国人想起了钱学森——他的堂侄钱永健因为发明了测定活细胞内分子的新方法而得了化学奖,更诗意的描述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点亮了活细胞的内部结构。
跟钱永健一起平分奖金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日本裔教授下村修,另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丁·沙尔菲。
6年前,精通科学史的饶毅列出“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到现在为止名单上21项已有9项获奖,其中就有这3位。在他列出的第8项中,与钱永健并列的还有一位名叫Douglas Prasher的人,他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GFP,在2002年时,他在美国农业部麻省Otis植物保护中心工作。
而现在,Douglas Prasher正一身蓝领打扮,为阿拉巴马州的一家丰田汽车经销商开一辆接送客人的中巴。不少人一定记得同样来自阿拉巴马的阿甘。《阿甘正传》中喜欢跑步的阿甘,穿过美国中部一条条宽阔无人的公路。对阿甘,人生就是一次没有特别原因的跑步,但对Douglas Prasher来说,没那么简单。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还是一位科研激情高涨的生化教授,正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申请一项5年基金,以期找到可以发荧光的蛋白的基因。他设想,这种发荧光的蛋白的基因,可以用来作为光线,点亮细胞内的结构。可惜5年基金的申请被拒。同时他向美国癌症协会的申请获批准,但只有两年时间。两年结束,他分离出了基因,但因为经费问题不能再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他一边慷慨地与钱永健以及另一位哥伦比亚的教授分享了这个基因,一边开始寻找新工作。只是很快他对新工作环境的管理方式心怀失望,又开始寻找下一份新工作。好不容易喜欢上NASA的一份科研项目,又因为预算问题,NASA取消了项目,他再次陷入情绪低谷。在失业一年后,迫于生计,他开始为一家丰田汽车经销商开车。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干了一年有余。
诺贝尔奖的一个奖项,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个得奖者。现在,当司机的Douglas Prasher心态不错:“有比我更适合领这个奖的……他们一辈子都在搞科研,而我没有。”
还有更酷的。2006年8月,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因为破解了世界级难题而被授予菲尔兹奖,而他竟然拒领这项诺贝尔级别的数学奖。此人说,自己工作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得奖。一位同行评论:“可能他已看透一切,认为数学很悲哀,对钱也不感兴趣。大奖对他来说只是检验他理论的工具。”
读过一本畅销小说叫《诺贝尔的囚徒》,刻画了西方科学界的某些潜规则。写这篇小说的,是一位被冠以“人工避孕药之父”美称的科学家,当选多家学院院士,还曾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力的30大人物”。退休后,他试图用文学的形式,来帮助普通老百姓去了解一下科学界的“部落文化”。
小说中的康托教授,终于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时,他读了艾略特的诗:
为了要到达现在你所在的地方,
离开你现在不在的地方,
你必须经历一条,
其中并无引人入胜之处的道路。
英国《自然》杂志曾采访过韩国的黄禹锡,说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上4点半起床,总是最早出现在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在他的实验室,根本没有星期六和星期日,实验工作小组中的许多年轻男女,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只好内部解决配为夫妻。
但仅靠勤奋还不够。一个领导几十号人的研究组的教授,还必须懂经营。他得募集研究经费,还必须担当在重大科学会议上的发言人……就像康托教授对他的学生说的:“现在研究需要花很多钱。没有钱,你就无法进行认真的研究,想一想购买你所用的那些设备的费用吧。当你送上经费申请时,你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会坐在那里审核你的申请。”
“发表、优先权、作者的名字排列、杂志的选择、大学里的终身职位、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诺贝尔奖、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包袱。”《诺贝尔的囚徒》中的这句话,勾勒出了现代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在今天,自选择科学那一日起,每个曾经从小立志做科学家的人,就同时选择了当代科学的灵魂和包袱。除非他像那个拒绝领奖的酷数学家一样,纯粹以解决问题为乐。或者像Douglas Prasher一样,内心平静地坐在方向盘后,继续行驶在阿拉巴马宽阔无人的大路上。
(贾 强摘自《南风窗》2008年第23期,喻 梁图)
——浅析《阿甘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