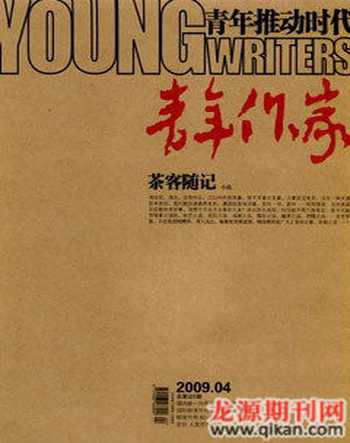分行
于 坚
分行,作者一声命令,汹涌澎湃转瞬即逝的语言之间突然被一脚刹住,停下来,那几行出列,犹如群众队伍前面的敢死队员,立刻光辉夺目,与众不同了。为的是不朽,不被遗忘。当然,也有哗众取宠之嫌。
一般来说,诗歌就是分行排列的文字。古诗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都是分行排列。古代,说诗的时候,是说分行,五言、七言、古风、长短句等等。诗是什么,没有定论,诗言志,是说这些特殊的分行存在的语词的内容。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分行。这是诗的基本存在方式。取消了分行,关于诗歌,我们就将陷入本质主义的深渊,诗是什么?诗言志,诗缘情,是说诗要表达什么。小说、戏剧、散文都可以言志抒情,不独诗,这就扯不清了。分行,我们立即可以定下来,那是一首诗。至少这些文字有朝这个方面努力的企图。
七言排列或者五言排列,那就是诗。至于这些分行排列的文字给人什么感受,它的语词组合的效果、韵律、词汇,朴素、华丽、空灵、恢弘,雅致或者粗俗,这是另一回事。各时代对此的感受不同。在此时代崇尚浮华伤感,措词严谨,在彼时代尊崇朴素中正、韵律奔放自由。但诗是分行出现的,文字一分行排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是一首诗。古代诗如此。现代诗也是。汉语诗是,外国诗也是。不分行排列的,就是它的内容是诗性的,我们也总是首先不把它作为诗来看待。
押韵、词牌都是为了分秆。为了区别不分行的诗。
诗词格律的产生。是为了正声,在分行出现之前,语言乱糟糟堆在一起的,鸟语、方言,诗被鸟语遮蔽着,分行使诗鹤立鸡群,是文明的一大升华。书同文,使各地区的鸟过文字沟通。分行,确立了诗的独立地位。先分行,是不是诗意的,再说。在古代,但仅分行是不够的,必须建立格律,更精致的分行,因为古代汉语有一个正声的任务。五音使人耳聋,押韵的出现,是为了正声。“乐而不淫,衷而不伤”不积极是正风俗,厚人伦,“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巷闾,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己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朱熹《诗集传序言》)分行,而且“协之声律”,就是为了“其言粹然”。
“其言粹然”,有点像1949年后推行普通话。普通话当然与诗教不同,但“其言粹然”是一致的。“协之声律”,“其言粹然”使得诗成为语言的最高形式,成为汉语的标准、典范。而语言就是存在之家,诗作为语言的最高典范,当然也就是这个“家”的家规、伦理道德秩序的象征,天地神人四位一体之神的代表。“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从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所以《诗》之为诗教矣”。分行,到后来,在中国发展为一种话语权力,知识分子进取功名的工具,就是因为“诗教”,西方是政教合一,中国则是政治家首先要学会诗教,要会分行押韵,先要是个文人。政文合一后来科举考试要考填词做赋,就是这么来的。
对李白这样的诗人来说,格律化令他窒息,他意识到危险,格律将使诗的自由分行被束缚起来。他是自由分行的大师。
《蜀道难》:
“噫吁喊,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它回川……”
屈原、李白、都是古代少数有自由灵魂的诗人。他们是最明白诗人何为的诗人。
从诗经开始,分行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诗歌的分行史,往往是在文明的格律化与自由分行之间运动。从诗经的四言,到汉诗的七言、唐诗、宋词,元曲……宋元,自由分行的冲动就消失了,格律成为诗歌的绞索。直到白话诗,诗才重新自由分行。
在文明历史上,重新分行总是出现在伟大时代的开端。自由分行是语言的一种解放运动。
诗是什么,像胡塞尔启示的那样,将这个我们数千年来一直企图定义而总是悬而未决、语焉不详的东西就继续让它悬搁着吧。存而不论。未来数千年,如果语言继续存在的话,这一点将继续争论下去。我们先来分行。
分行,是诗歌最表象的、一望而知的东西,诗的物质外壳。
一旦分行,我们就知道这些文字要“与众不同”,“诗意”一把了,已经约定俗成。
那些不分行的文字,那些文字的群众,我们叫做散文,但散文里面未必没有我们感觉到的那种所谓诗的东西。
但是,激发我们将这些文字首先用“某种诗的东西”来要求的是那些分行的文字。在“某种诗的东西”这一点上,我们对分行文字比散文有着更直接的敏感和要求。
我们容许散文毫无诗意,比如说明书、文件、社论等等。但如果这些文字已经分行,而毫无诗意,我们会大失所望,那就是搞怪,文字游戏。
诗这个词,总是被诗意和分行所裹缠。诗意是广义的,可能性存在于一切文体。诗就是被分行的文字,也许它毫无诗意。诗就是那些分行排列而不是集群混杂的语词。这是一个定义。诗是那种我们感觉到所谓诗意的东西,这个东西不见得是语词,一种状态、一个行为可以是具有诗意的。
历史上某些曾经被认为具有“诗意”的分行,今天未必具有“诗意”,我们依然承认它是诗,仅仅因为它“分行”。例如:“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诗经《天保》)今天阅读,也许不知所云,但在当时,它确实是可以招魂和九鼎之言。
(不知所云,是因为它的分行已经陈旧,需要重新分行。诗意已经被时间遮蔽了。时间会敞开诗意,也会遮蔽诗意。)
分行确实不意味着就有诗意,但分行,就意味着这些语词有明确地要召唤诗意出场的倾向。分行,就像巫师做法事时的道具、动作、声音。最终,是魂是否被招魂到场,另当别论。但我们承认这是一场巫事。
分行,就像京剧中的脸谱,一旦你把脸画成那样,就是你还没有唱,大家已经将你视为演员了。现在,你的一切行为都是演戏,你可以杀人,可以放火,这是演戏。
脸谱、分行,其实就是划一条线,划界,语词的分行排列、生宴净丑的脸谱这边,是诗、是戏剧,别当真。
文章为天地立心。分行,是为了立心。先要分行,然后才谈得上立心。心很复杂,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心,有“众生之心,犹如大地,五谷五果从大地生。……以是因缘,三界唯心,心名为地”。《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之心,有安心之心,有心灰之心,有“哀荚大于心死”(庄子)之心,有心曲之心。“若善男子,于彼善友。不起恶念,即能究竟成正觉,心花发明”(圆觉经)之心。有解心释神,莫然元魂”(庄子)之心,有心思之心,“有空留锦字表心素”(李白)之心,有虔诚之心,“吾心为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诸葛亮)的公正之心。有“虚其心,实其腹”(老子)之心,心术心算心计
之心,有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唐张彦远)之心,有心寄之心,有心许之心,有心酸之心、有心灯、心树、心斋、心茧之心;本心之心、心灵之心、开心之心、违心之心、昧心之心、恶心之心、随心之心、慧心之心、童心之心、心醉之心、心旌之心、心仪之心……各时代的心声、心旌、心仪的是什么。这不一定,此心生彼心灭。超越生死的心是大道,道心。
文章为天地立心,诗意就是心立,心是什么,自古以来,说的都是心的各种状态,这些状态通过分行的文字表现。也通过不分行文字表现。
作为写作,分行就是从世界中出来,文明黑暗的世界。文,怎么文都可以,重要的是立心。但是,文明向着雅驯流去,文明的源头被遗忘,为什么要分行,每一代诗^都要重新问这个问题。朱熹问道: “‘《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也,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也,则言之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己焉,此《诗》之所作也”。诗是思的文字记录。思是什么,就是心的田地。心灵的大地。(这个思不是思考的思,思考是认识论的,思却是本体论的。思是存在于世界中,感悟。思考是认识,解释世界。)诗之所作,还不够,还要正声,不能只是“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己焉”,于是要“去其重复,正其纷乱”以至于雅驯。
当雅驯已经完成时,诗人感到窒息,就要重新分行,仅仅是“自然之音响”的分行,就是革命,白话诗就是如此。但是,白话诗出现的背景与原始时代黑暗荒野上的“安静”不同,白话诗的背景是一个巨大的古典诗词支撑着的雅驯传统。千年雅驯的结果,使汉语被音乐化了。汉语就是不谱曲也具有音乐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就是五个音调,就像古代音乐五音的五种调式:宫、商、角、徽、羽。明朝释真空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收藏《玉钥匙歌诀》如果夸张发音。那就是歌唱。方言本来声调更为丰富。例如现代粤语分为九声“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和“阳入”就像宫商角羽。在请教的影响下,汉语一直在调整雅驯它的音乐性。这为分行奠定了一个音乐基础。从格律回到分行并不是回到“自然之音响”,而是回到雅驯后的音乐汉语。
现代白话诗取消了格律。因为分行的排列方式可以取代固定的韵脚。汉语原始的、内在的韵律音乐性获得了解放。五声就是乐谱,现代诗摆脱了格律的束缚,丰富了诗的韵律。现代诗更吻合诗人个人的语感、生命律动。格律化的末路是使分行成了依样画葫芦的填写游戏,取消了韵律的个人风格。
格律式的分行也遮蔽了诗意本身,格律取代了诗意,只要符合格律,那就是诗。相当于,只要分行,那就是诗。只要押韵,我们就将这些文字作为诗来反应。
分行,诗与非诗的区别,其实只是这样分行而没有那样分行。
分行,是一种解脱,从语言历史、秩序、约定俗成中解脱,只要一分行,怎么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了。菜谱、学术论文、社论一旦分行排列,就使人误入“这是诗”的陷阱。
分行其实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诗一旦诉诸文字,它就要分行。分行是语言的一种解放,这几行脱离了语言的汪洋大海,脱离了一般的语境和逻辑关系,忽然间充满魅力,出神入化,神籁自韵、神采奕然了。
分行是诗最基本的、开始的自由。分行就是自由。然后,诗向着雅正发展,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七律、七绝、五律、五绝、词……是诗分行之后的雅正。雅正到了极端,就是雅驯,诗就要重新回到分行。诗经是民间的分行、屈原是独行特立的分行、李白是一次分行,苏轼是一次分行,白话诗是另一次分行,分行是获得自由、开始。分行也是从分行的雅驯、规范中的一次次解放。
“雅正”是诗的极致,雅驯则是束缚、暴力。一旦“大雅久不作”(李白),诗就要重新分行。
分行排列的语词,意味着它们不再是普通的日常语言,不再是口语或者书面语。分行与日常语言划清了界线。至于它是什么,可以争论。我们不会对没有分行的日常语言发生怀疑、争论,好奇。分行使我们关注语言。分行有一种祛除遮蔽的直接教果。
诗可以视为语言的去蔽过程,语词从陈词滥调的汪洋大海中脱颖而出。分行就是去蔽的动作。至于去敞的程度,去敝还是祛魅,那是另一个问题。
西方现代艺术在二十世纪意识到这个,杜尚是个分行的大师。一个小便池,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小便池。但放进博物馆那就完全不同了,它立即成为惊世骇俗的艺术。博物馆是一个界限,它暗示摆在里面的就是作品。其实小便池并没有任何实质改变。是什么使得观众将这个小便池视为作品,区别于世界是沙漠殷密集的小便池呢?分行。博物馆就是一种分行。杜尚与那些学院里靠技巧和艺术理论混的家伙开了个玩笑。他嘲讽了博物馆。他的小便池祛除了博物馆对“生活就是艺术”“世间一切皆诗”这一真理的遮蔽。安迪·沃霍尔将杜尚的这一套继续发挥,他进一步直接解构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贵族关系,可口可乐筒、电影明星梦露这些俗不可耐的日常生活符号被升华到艺术的层次,而艺术的狭窄空间也被解放了。这是一次分行。波普要玩的就是生活就是艺术,但是如果没有划界迭个动作,生活就是艺术就体现不出来。西方的博物馆这根线,没有古代中国划得好,博物馆的实质是教堂的延伸部分,不说教,但依然是观念,教育而不是教化。杜尚对博物馆的解构不自然,也是从观念到观念,要解释才可以接受,杜尚养活了一大群批评家。
中国早就玩这一套了。瓷盘上的青花、粉彩、景泰蓝、花瓶、花盆、园林、画舫、……那都是划界,一个普通的实用的盘子,描上青花,它还是盘子,还是可以用来盛菜。但它也是一个作品。一般普通的船,开个画框式的窗子,自然景色就成了作品。船还是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去杭州的时候,乘画舫游西湖,他说没看见画舫里的画挂在哪里。嘿嘿。
分行就是艺术。人为就是艺术。生活就是艺术,生活是人为的。生活不是自然,生活是道发自然。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
诗意是先验的,诗是诗意的敞开。诗意如何敞开,分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分行方式,诗意的敞开并非一劳永逸,诗意总是在分行中被敞开,定在雅驯中被遮蔽。
中国没有准宗教,李泽厚说只有半宗教。半宗教的东西就是诗教。诗意的敞开,就是教化的开始,而教化总是走向雅驯。于是,重新分行。
只有人可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小便池是一种分行,塞尚、齐白石、巴尔蒂斯、莫扎特都是分行。但是,孰高孰低,这里有一个分行与他者的关系。你在乎他者,他^就是地狱,分行就有是非。你不在乎他者,分行就你自己的游戏,日记本,怎么都行。小便池是杜尚的游戏,杜尚不在乎他者。这个游戏之所以轰动西方,进入艺术史,是因为通过杜尚,西方首次意识到生活就是艺术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有些惊世骇俗的观
念。对不起,再冼把小便池放进博物馆,没戏了。行为艺术的依据就在这里,只可以搞一次,行为艺术必须绝对自我,白恋,非历史化。行为艺术是空间艺术,它每一次都必须横空出世,占领新的观念空间,行为艺术必须斩断与时间和历史的联系。但是,空间是有限的,行为艺术必然山穷水尽。杜尚开辟了后现代的游戏时代,但也就是到他为止,知道了杜尚,安迪·沃霍之流玩可口可乐的波普化,其实相当乏味。波普,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词,其实中国玩得太大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整个国家的广场和主要建筑物都用黑布和白纱裹起来。包裹德国国会大厦那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与盘子上描青花一样,黑布包裹广场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展览,而是真正的悲哀,悲哀并没有被游戏化。而小便池放在博物馆里,它只能思考、解释。游戏,而不能小便了。中国的伟大是宣接把这个小便池做成作品,而不必送去什么博物馆。有一天翻清宫画册。看到光绪皇帝的景泰蓝马桶,那真是做得美到平庸的地步,而皇帝先生也天天拿它便溺。看看卫生间里的白瓷马桶,模仿西方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只是实用,各式各样的实用被严格分类,马桶就是马桶,量杯就是量杯,其它什么也不是。前天去一朋友的古玩店里转,看见一红色小桶,清末民间的作品,当年很普遍,腰上箍着两道铜环,打制得很美,问是什么家什,马桶。不用了,还可以留看养眼。
艺术不在乎他者,玩不长。一招鲜。这个世界毕竟是个他者的世界,他人不仅仅是地狱,也是历史、经验、时间,终极价值、普遍性。对于诗人和艺术家,他者是先验的。是被抛入世界所必须接受的前提、存在。有些自恋者,一方面,他的分行仅仅是自我的野怪黑乱,另一方面。又渴求他者的承认。他者不承认,就通过理论、解释、甚至于行政手段。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诗歌其实相当自我,所谓“中国特色”,完全无视他者的存在,依靠行政力量维持。自我可以玩。但是只限于自我。自我而野心勃勃,企图以自我意志统治世界,那就是只有独裁、纳粹,希特勒就是个自恋狂。
1993年我在北京与牟森搞贫困戏剧,贫困戏剧玩的就是从“三一律”回到分行。拒绝传统的话剧表演,将日常生活通过舞台划界。一旦上了台,你无论做什么,都是演戏。在《与艾滋有关》这一场中,我、吴文光,舞蹈演员金星、作家贺奕等人其实只是应牟森的要求在舞台上做了一顿饭。上了这个台,无论做什么都是戏,所以牟森训练演员只是训练他们放松,戏剧就是解放。放松什么?放松他们生命的深度,让生命越过舞台、面具。不需要再表演了,也不需要再戴一个面具了,上了台,就是分行,就是越界,就是到了那一边,就是表演。直接做就是了,怎么做都是戏。舞台是一个解放区,不是在上面表演,而是不表演。
人不是小便池那样的符号。人是一个有生命的舞台,一个天生的面具,文明已经赋予人舞台的意识,表演不仅仅在舞台上,“人生如戏”,中国早就知道。戏剧的力量在于将人从那种无所不在的表演中解放出来。人生就是戏剧。专业的戏剧被解构了。贫困戏剧其实就是杜尚一路。中国文化的奥秘,就在于将人生戏剧化,艺术化。这个戏的正道,是仁者人也。用仁来教化人生,通过人生如戏。
演出时,观众也可以走进舞台,舞台是开放的。这是要将人生如戏,具体化,现场化,但没有观众敢于走上来。他们还是害怕人生与戏剧之间那个界线。舞台、博物馆还是有着巨大的威慑力。一旦要上台,马上想到一招一式、唱腔、做派。就像写诗,拿起笔来就分行需要很大的勇气,人们被分行的雅驯史所震慑。
现代主义是一种文明的解放力量。这个力量的契机就是回到分行,现代主义不是二十世纪的事情,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现代主义。李白是唐诗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不是一种“我们时代的主义”,简单说,它就是回到分行。
分行就是划界限,所有语言都是一个现实,分行将某些语词从语言中分行出来,这些语词就不同凡响了。汪洋一片的汉语,拎出几行来,就光芒四射,说着玩的?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你那几行读者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就来玩解释、理论,玩“你不懂”。这是二流。这个时代确实不懂,但这个不懂不是那个不懂。不懂李贺、阿什伯里是一种不懂,不懂李白、王维、弗罗斯特也是一种不懂。前者是知识的不懂,可以学习嘛,后者是根本不懂,只有由它不懂啦。
分行之后又如何呢?基于自我的分行可以忽略不计。
分行的结果是使天才重新得到承认。
分行,这要看是谁分的行,如何分行。李白的分行显然与张三不同。
读者再次参与进来,他们将心比心,越过韵律、熟语、意象等造成的审美藩篱,根据个人的人生经验、感受、阅读史、知识水平判断诗的好坏,而不必顾及雅驯的模式。其实雅驯已经成了平庸诗人的掩体,任何一个庸才,只要掌握了诗词格律那一套知识,就可以混成个骚人。
每个读者都是一个孔子,都有删诗的权利。但伟大的孔子是一个他者,他代表着文明的最高核准权。他代表“周”。诗三百,不是孔子的自我意志,而是他者的意志,是历史、经验、智慧、时间的意志。
自我只是一个分行的冲动,分行的结果是文。文就是诗,就是先验的诗意被照亮。文明,现在听起来很深奥。在开始的时代,无非就是野蛮人在自己身上纹身以震慑野兽。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所以要把握中的尺度。
在数码相机没有到来的时代,照相机非常昂贵,谁有钱买照相机谁就是摄影家。现在每个人都有一部照相机,分行吧,兄弟。
分行不是诗的开始,而是结束。孔子也是一位诗人,诗三百也是一种分行,为什么是这三百不是那三百呢。孔子既是史,也是野。
分行肯定会导致鱼龙混杂,因为谁都可以分行,不必诗人。而诗的伟大就在于它在每个时代总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场。翻翻唐人选唐诗,李白杜甫排在后100名。诗是文明的开始,也由文明来不断澄明、选择。诗是由长时段的文明选择,不是由短时段的时代选择。一般来说,时代是看不见它自己的诗的。不必担心鱼龙混杂,诗不害怕时间,杜甫早就说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天地无德,文明最终选择哪几行来塑造民族人性,诗教,这不是我们可以判断的事情。评奖、写教材什么的其实都是时代中的事情,但很有用,诗人也要有个饭碗嘛。
诗人要有一个先验的基础,然后分行。先验是黑暗的,这是天才、历史、传统、智慧、时间、经验在个人生命中的黑暗地带。当你分行的时候,这些就被照亮了。
黑暗深度决定光的亮度。伟大的诗人是那些生命最黑暗的人,因此光辉灿烂。
当然有专业诗人,当我说专业的时候,那意思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诗是少数通灵者的事业,决不是只要掌握了诗歌知识就可以混的饭碗。李白是一位分行的大师,什么古风,就是抢着金箍棒分行。这个行是李白分的,那就是大雅。
分行,是一个动作。排列语词的动作。把诗这个字视
为动词还是名词,是诗人和诗人之间的分行。
分行是个照妖镜。别贴什么先锋派、后现代、象征主义、垮掉、托什么马斯的标签,就是朝那浩如烟海的汉语踩一脚刹车,看看你分出的这几行,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立起心来。没有,再被辩也是白搭。一个悖论,读者只是读者,读者不是先锋、后X、象征派、垮掉……读者没有垮掉。读者不必知道这些。西方诗歌的策略是,拒绝读者。这有西方个人主义的悠久传统。但中国是一个他者的社会。诗承担着宗教、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抛弃这一使命的结果是,诗被关进象牙塔。在西方,象牙塔是一个沙龙。在中国,象牙塔是一个监狱。在西方,无论诗如何拒绝他者。诗人不会耐抛弃,因为这是社会游戏的一项。我不懂你的作品,但我尊重你的游戏,中国不是,诗歌不能蛊惑人心,读者也不尊重诗人。诗在中国,不是游戏,与三教九流不同,诗是诗教。
拒绝隐喻就是回到分行。
隐喻就是他者,他者也是一种暴力,文胜质则史,史一旦成为雅驯,成为“存天理,灭人欲”,一旦只是玩平平仄仄,尾韵、颔联、额联,就必须回到分行。新诗重新回到分行,看起来完全是非诗。太容易了,是的,就是这么如此简单。
分行使诗重获自由。
但是,自由不是诗,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好诗诞生,分行没有那么容易,分行就像一直都在押韵游戏中滥竽充数,忽然,真正吹簧管的那人来了。雅驯闪开,重新分行,天才脱颖而出。
分行是回到神话,神话是空间性的、平行的,直接就是。后现代、杜尚、波普都是一种神话方式。神话的危险是切断与时间、历史、他者的联系。但神话确实是文明的一个动力,有时候我们需要神话,当时代雅驯过度。“文胜质则史”。有时候我们需要隐喻,当时代野怪黑乱过度,“质胜文则野”。神话就是直接赋予语词“它就是它”的力量。直接就是。
隐喻则是一种解释。隐喻是历史的,垂直性的。历史就是他者。
言此意彼,先有一个意义的转移,这个转移就是解释,好的隐喻利用神话的直接就是,将意义的转移、换位。看起来像是直接分行。
分行,使诗从语词空转的压韵修辞炼字游戏回到兴、观、群、怨,回到比兴……这些诗歌最原始的神话功能,重新焕发招魂的魅力,获得诗最原始的巫性力量。
诗经、屈原是开天辟地的分行。李白、杜甫、苏轼、新诗是雅驯后的分行。白话诗或许是最后的分行?我不知道,只有天知道。
分行不腊的开始,而是诗的结束。开始就是结束。
说这些有个前提,就是,诗是先验的,天地有大关而不言,世间一切皆诗,诗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诗先于语言、分行、人的存在而存在。
诗是元,我们只是将无“分行”为有而已。
分行吧,就在你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现场。但要记住,君子三畏,第一畏是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