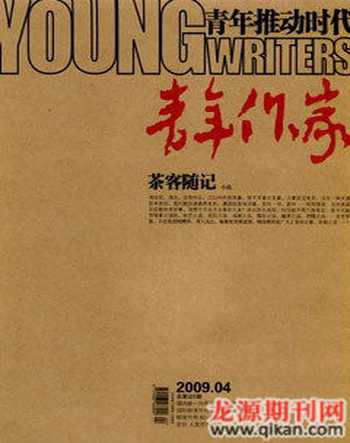孤独漫步——卢梭《—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陈 陈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是卢梭最后的遗作,它不纯粹是《忏悔录》的补遗,而是卢梭与自己的灵魂进行最后深入交谈的絮语。生命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灵魂将要最终摆脱躯壳,摆脱人世这个大的炼狱。
这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怎样的一个生命啊!社会是灵魂与生命所投身的最大外部舞台,它们的命运很可能取决于某些特定的时刻。如果一定要寻出卢梭个人遭际命运之后的根源来,就会寻到《忏悔录》。“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连续不断地记录下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由于这些书所引起的我和父亲之间的谈话,我的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便形成了,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也就形成了。在我一生中每逢这种性格处在不能发挥的情况下,便使我感到苦恼”。“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不幸。与社会的冲突似乎是注定的了。如同罗曼·罗兰所说,大家都在一个公共的槽里饮水,把水都搅浑了,灵魂能不因此而浑浊吗?而谁又敢将自己的灵魂在公众面前坦露无遗,谁又觉得有此必要,如若不是对此有另一番理解、另一种期许、另一种力量?
在巴黎郊外踽踽独行的这位老者,尽管厄运曾将他推到了疯狂的边缘(他自认为有一个强大的阴谋集团在暗算他,他怀疑所有跟他接近的人,只接待少数朋友,而且不断发生争吵),但并未能真正击败他。“在这不幸中支撑我的只有我的清白无辜,设若我将这唯一的、强有力的源泉抛舍,而代之以邪恶,那我将是何等的更加不幸呢”(《散步》之三P53)。他一直就用这种清白无辜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体系。“我在相应的精神秩序中(这个秩序是我探寻的结果),找到了我为忍受一生的灾难所必需的支撑。在任何别的体系中,我只能无能为力的活着,无所希求的死去。因此我还是坚持这个体系吧,不管命运和那伙人把我怎么样,只有这种体系能使我幸福”(《散步》P48)。“廉洁、正义感是一笔财富,是人可以随着灵魂带走的无价之宝”(《散步》P55)。“德行是灵魂的力量”,多亏了这个灵魂,这个灵魂的高贵,他才没有被厄运所压垮。最后,在11世强呱盏虫的残年,索性又将自己的灵魂交出去,“它可以做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忏悔录》)。把他的最后奉献给了对自我的探索、对人的研究。教会、政府、欧洲舆论原本想将他打翻在地,涂抹成一个千古罪人,而我们却在《忏悔录》中看到一种悲愤的力量,又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看到一个人类心灵所曾经达到的境界。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人不是最后的尺度,就像迫害、驱逐、厄运所密布而成的厚重的云层,仍无法阻挡像阳光一样透射下来的欢乐。这欢乐一直可以追朔到早期的沙尔麦特。《散步》(之十)中,卢梭回忆了这一切的根源,回忆了在华伦夫人身迷所度过的那些时光,“我没有一天不在快活而动情地回味我一生中那绝无仅有的短促时光,那时我是完完全全的我,纯粹的我,无羁无碍。……设若没有那一段短暂而珍贵的时期,我也许至今还不了解自己的天性。……对幽静和沉思的爱好从我心中产生了,因为我的心需要自然流露的、温柔的情感去滋养它。这种情感由于环境的喧闹而被压抑下去,又由于宁静与平和而复苏和激昂起来”。在《散步》(之五)中卢梭又无限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被驱逐的间隙,在圣皮埃尔岛上度过的那两个月幸福的时光。驱逐把他还给了自然和自我,既然“我身外的一切都和我无缘了”,既然“我在这个地球上,恍如活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既然“他们已从我手中夺走了我对社交的柔情”,既然“我在尘世上散失了一切希望”,那就全身心的沉人与自然与我的灵魂交谈的温馨之中。
晚年的卢梭,在经历了八年漂泊动荡的岁月之后,才得以重返巴黎。他住在普拉蒂也街一所简陋的住房里,以抄写乐谱为生。深居简出,与上流社会一刀两断,过着隐遁的生活,在孤独与漫步中度着余年,每日流连于郊外的自然景色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记录的就是这些孤独的散步和散步中的遐想。文字和心灵一样上升到一个随心所欲的高度,“那时,我的心无拘无束,思潮可以尽情涌流,唯独在这些孤独和沉思默想的时刻,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和我的天性相符的我。我才既无烦扰又无羁束”(《散步》之二)。“通过自身的经验我懂得:真正的幸福之源就在我们自身,对于一个善于理解幸福的人,旁人无论如何是不能使他真正潦倒的”。“只要我一想到我的心灵曾经达到的境界,我就会把那深重的苦难、我的迫害者以及我蒙受的屈辱统统抛到脑后”(《散步》之二)。卢梭的心灵已经在厄运的涤荡中净化了,这才是命运和人无法从他那里夺走的。
那时候的巴黎郊外,尚有一片“招人喜爱的风景区”和“一些穿过葡萄园和草地的小径”。卢梭生命中最后的七、八年时光,就是这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度过的。“大自然,我的母亲,我现在是在你单独的守护之下了,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奸诈邪恶的人插在你我之间了”,“我生来就是为着独自一人在闲暇中沉思默想的”,“我独自沉思默想二十年,也抵不上我在人事的纠缠中生活六个月”(《忏悔录》下)。“我从来不曾真正适合于社交活动”,在那里“我永远也达不到我心灵所要求的那种境地”,“当我把社交界的纷扰所引起的尘世欲念摆脱掉之后。我的灵魂就常常超越了这个氛围,去与天使们提前交往了”(《散步》)。
写完《散步》后仅仅三个月,卢梭就溘然长逝了,到一个没有纷扰、没有苦难的世界里去了(到华伦夫人身边去了)。那些昏沉、痛苦以及幸福与欢乐的时刻,已成为永存的精神财富,已凝结成为泰戈尔的一首诗:
如果所有的人都害怕而离开了你,
那么,你,一个不幸的人,
就敞开心扉,孤军前进!
如果无人在狂风暴雨的茫茫
黑夜里高举火把,
那么,你,一个不幸的人,
让痛苦点燃你心中的明灯,
让它成为你唯一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