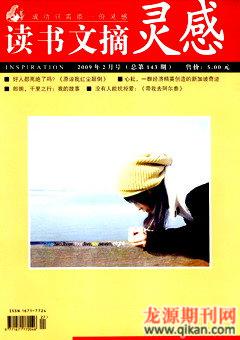张大春:《聆听父亲》
李宗陶
夹着两天里染上的一点京腔,台湾作家、《小说稗类》及《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作者张大春跟沪上文人小宝切磋起来,声若洪钟。
从京城来,从故知阿城、莫言、余华处来,他有欣喜:“走进一看,嗬,都是朋友。”在弄堂深处的老洋房里,他有怡然:“台湾找不到这样的房子。”他的一部分视线,早已透过车窗,透过房间的窗棂,去偷看初春的上海了。
留在室内的这部分,有小说家的敏锐、评论家的直截、旧体诗作者的情怀、梨园的嗓音、电台主持人不慌不忙的节奏以及藏书3万册(其中三四千册线装书)的对岸传统丈人的气韵风度,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因为有了牵挂
“1988年3月第一次来大陆,刚出首都机场,路边树木都是枯枝。40多天后回台湾,去机场路上再看,全都发了绿芽。笔直的路上,新绿的芽,白的树皮,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诗经》中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四季如春,看不到这种景致,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大陆。
“昨天在北京,莫言说起一段跟我父亲的闲话。莫言说:‘张叔叔,您跟大春的感情很好啊。我父亲一声叹息:‘唉,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他是我哥哥了。这话我从没听父亲提起过,也没听莫言说过。乍听之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他不吝展示感性的一面,却轻淡,煽情处一点即宕开。
《聆听父亲》是家史,是写给父亲和孩子的家书,也是张大春第一次边写边哭的小说。山东济南张家“慧德堂”,曾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家世显赫,代有功名。从高祖捐官被骗三百亩地开始,贴在门楣上的家训“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悄悄改换成一副与“福”、“贵”相关的楹联。曾祖、祖父、父亲、母亲、五大爷、六大爷……最初写成的5万字搁了4年半之久,因为本是写给“未曾出生的孩子”的;儿子呱呱坠地,活生生就在眼前,他写不下去。妻子一句“我们要付房子贷款”,令家庭责任感苏醒,他用一个月写出了另7万字,薄薄一本,英文名可能更贴切:As One Family(一家人)。
“莫言说,这个故事在他手里可以写110万字,但我写得很小。历史长河中,人就是一个小点,浮华散尽,最后留下至多一个名字。人们正在努力的,无非让这个小点的位置高一点,世俗生活富裕一点。基于这点考虑,我写前跟自己订了一个契约:不用任何虚构,用最洗练的笔墨,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细节,用简笔,所谓‘一笔勾魂。”
2003年《聆听父亲》出版后,获得当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奖、《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金石堂年度双奖。朱天文说,这是张大春暴露弱点的一部作品,因为他有了牵挂。张大春自己说,“从来没有哪本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这一次,他没有掉书袋、玩典故、扮顽童。
“这个高阳啊。财务上不好的”
都说张大春是高阳先生的入室弟子,为何不曾拜师?张大春呵呵一笑。
当年,高阳只与台静农、张大千来往。一次朋友引荐,同入饭局,“我忽然跟他讲,听说您在研究义山诗,我总感觉这里面有跟小姨子的奸情。他几乎站起来了:‘我正在写这个小说。你怎么知道!”
“我就讲,‘望帝春心托杜鹃等典故过去解错了,还讲了几个细节,譬如‘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是针对有人劝他念兹在兹,不要把心思放在小姨子身上的反应。高阳于是滔滔不绝讲起他的考证,哪首诗什么意思,清清楚楚。”
“没多久,我们就看到《凤尾香罗》的连载预告,小说出来了。因为这个,他把我当哥们一样,没事打个电话,‘什么时候进城呐?”张大春戏仿高阳的钱塘口音。“我说现在就可以啊。来!他说。于是进城,喝酒。”
后来,两人参加《联合文学》组织的代表团参观日本,相处多日。
“每天早上起来,我拿着稿纸去旅店传真部。敲开他的门,三张稿纸递出来,一起拿去传真,给不同的报社——为什么?我付钱呐。一顿饭,一次旅行,就是这样一段因缘。
“他待我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过世前我去看他,他女儿还说,‘爸爸想要收你做弟子,你都一直没有磕头。我不是不想磕这个头,或者说吝惜磕这个头,是我爸爸跟我讲(我爸爸很有心计):‘你小子要记得,这个高阳啊,财务上不好的,你当了他的弟子,我都要倾家荡产。”
哈哈一笑过后,张大春正色道:“我因此觉得对高阳先生终有一分亏欠。”高阳身后,张大春写了一系列文论及一篇祭文,追忆从这位前辈身上习得的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正是他此次从京城讲到上海的题目。
工匠与大师
这个聪明绝顶的男人,认字前会将《三国》、《水浒》的地名、人物安插在自家院落的不同部分:20年里遍玩小说形式,认真又彪悍,40岁在一片惊讶声里结了婚(朱天文语),现有一双儿女。儿子问一句他常给十句答案——他此次离家,儿子的感想是“家里安静了”。他喜欢给孩子讲故事,譬如商山四皓在“橘”中下棋,然后驾祥龙而去,隔段日子从孩子嘴里听到“喏,那老头儿骑了条大龙走了”。
现在,他顶着自来卷的长发,以眼角余光照顾X80度的视野,说累了站起来说,搭着椅背说,请求“撒个尿”接着再说,但听汉字一颗一颗、铿锵有力、稳稳落在地上,发出金石之声。
面对“带着一大堆看不见的文化准备”阅读他作品的人,他是恭敬的;如果读者不买账,他也能平衡:我写给一个读者看,是谁不确定。
他概括自己前半生:“生活是浑浑噩噩,要赚什么钱,达到什么地位,统统不知道。但在所学、所事这件事上,我是义无反顾。”他讲“局”字的来历,引申出这层意思:再高的人,想要有所建树,影响周遭,就要“入局”。此番他入了书商的“局”,一笑自嘲。
他自谓“工匠”。剃头学徒3年期满不肯出师。为什么?因为跟着师傅可以由着性子刮,尝试不同方法,不必挑担“待召”(古时对剃头匠的称谓)。又说:“工匠不对自己的作品形成美学,这就没有天良了。”
所谓大师与工匠的区别,小宝代答:张大春8岁知道“致仕”是辞官、告老还乡,是为“工匠”;余秋雨先生58岁称“致仕”是获得官位,别人指出还不肯承认,是谓“大师”。张大春呵呵一笑,补个注脚:致,归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