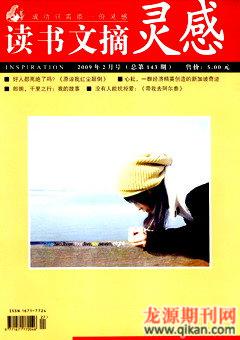灵魂似乎还活着
布里斯班的某个下午,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NO,NO,NO,虽然很多小资杂志的文章是这么开头的。我用iPod,但是里面是昆曲。我用八行笺纸写信,写给国内,用邮票,用钢笔,竖着写字。电子邮件很方便,但是没感情。所谓的什么复古是个噱头,我只是骨子里传统而已。再这么发展,我就去买身长袍穿了。
在北京图书馆里,我亮出我的身份证,但是他们却不让我进。在澳洲的一个小图书馆里,我竟然发现了窦唯的唱片《镜花缘》,我借来听。我比较喜欢的还有《明报月刊》。
有些在澳洲拿了绿卡的,对留学生说话就换了个味,就像拿了北京户口的就瞧不起拿暂住证的。周末去逛IKEA(宜家)家俱店,人爆满。老外装修房子很简单,不用什么高档材料,然后经常更换家具,给生活增添色彩。更换家具是个生活方式。国内装修房子,用上大理石,用上高档的材料,装得像个宫殿,然后打开家门,以示他人。
卡斯特罗来澳洲时说,澳洲就是将来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模型,各个种族,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但是我却觉得人们依旧活在各自的文化里,而白人文化是共同消化的东西。我可能不吃印度餐,也不会看全是黑人演的电影。黑人也未必会看宝莱坞的电影,但是人们都会看好莱坞的白人电影。白人文化依旧是强势文化。关于台湾,关于大陆,关于政治,每天都有人在说事。我的感觉是,无知不可悲,最怕的是偏见。韩国和印度人不讨人喜欢。印度人似乎总是喜欢自以为是,而韩国人很能吃苦,但是喜欢造假,说谎,不守规矩。我不是歧视,我是说个事实,当然这本身也可能是就是个偏见。
中国自古不惠寡,患不均。毛曾经建立起一个共产的雏形,大家互相帮助,共同富裕。只是这个雏形是建立在低的物质水平上的。邓则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部分先富起来导致的结果是必然一部分要先穷起来。邓的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分化。澳洲的留学生们,登陆着Facebook和校内,他们是物质时代和邓小平政策的受益者,如果你只看他们招贴的西化生活的照片,你会觉得中国的物质生活真不错。早些年罗大佑唱,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而现在大批的留学生却是未来的中产阶级。毛试图消灭的东西开始崛起:那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车,有房,会外出用餐,度假,熟悉国外的品牌,观念,生活方式,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政府的开放政策和自己的个人奋斗,但是私底下却可能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大加批判。
工友上班闲聊,聊来聊去,就是怎么跟房东斗争,怎么跟室友斗争,怎么跟房东斗争,据理力争,怎么泡女人,女人的身体。我的小侄女快要进幼儿园了,我母亲告诉我说,现在幼儿园的小孩基本就把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学完了。压力巨大。中国短时间内出现的繁华荣景,带来了未曾梦想过的自由,以及新的焦虑。我想到了鲁迅说过的,祝福我的小侄女和和她一样的小朋友:我希望她们将来不这般辛苦姿遂而生活,不要像闰土,也不要像豆腐西施,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我们未曾经历过的。
美国经济大跌,《时代》杂志新一期杂志专题是“新的困难时期”,报道美国经济危机,同时不忘盘点他的进口国:如果美国大叔的口袋空了,怎么买你们的东西。台湾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口。大陆百分之四十。东南亚大量制造厂已经倒闭。我在火车上,听有人接电话,用东北话跟家里人讨论汇率的事。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
父母在我上学的时候,永远给我高的要求,让我成为第一,让我出人头地,但是我一走出国门,家人就只字不提了,说的就是,你一定要吃好,喝好。我相信你的父母也是这样。我的变化就是这样,还是在变胖。我不写博。太长时间不写东西,以为自己麻木了。在开往Logan的火车上,我想到了我已经结婚的初恋,我想到了曾经的暗恋,所有的所有一下子全都涌出来。这可能跟星座有关系,比较悲观,比较情绪化。呵呵,你看梁朝伟,你看王家卫,许巍,周星驰,这些巨星真的都不爱讲话。我曾以为出走就能解决问题,忘掉所有,实际上却没有。我不断地回到最初。这是个可悲和可喜的事情:这些年过去了,我还是没变。来澳洲整整三年了,我的灵魂似乎还活着。
在年轻人泛滥的“豆瓣”里,到处都是小资和西化的趣味,我还真没看见有几个“跋攵”帘和“霸诙”帘几本哲学书的。当然,我不是贬义,最起码,弹钢琴的孩子没有坏孩子。我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聊天。以凶狠诤言著称的耿剑不留面子的教训我,他批评我在以生活的压力为借口,缺少读书,逃避精神探索,导致后劲不足,并且大力推荐我读《金刚经》。《金》我还没读,但是他讲的话都对。我已经自以为是太长时间了,是时候如堂诘科德般再度出发了。在此感谢。一并还要感谢雨后同学,她总是建议我看圣经。是的,要stayHungry,Stay Foolish.
现在的房东是个单身母亲,带着三个小孩,有天小女儿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爸爸有新女朋友了,有新女朋友了。中国没有这个。单身母亲说她儿子说,请把那个杯子拿过来,谢谢你。中国也没有这个。我跟工友说,我30岁的时候,如果我有点钱够我上路,就去来个环球之旅,绕世界一圈。工友说:你也没车,你也没房子,也没女朋友,也没个正式工作,还什么环球之旅,中国没有这个。
South Brisbane火车站台,疲惫的下班人群,都呆坐着,等着城铁到来。一个老头来到,坐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口琴,开始吹。琴声悠扬,动听。那几分钟,我感受到音乐的飘逸。一曲终了,站台静静的。疲惫的人群还是疲惫的人群。只有我一个人地给他鼓掌。老头见状,有些感动,走过来对我说:这一小块破铁,我已经练习了五十年。它很小,但却能随时随地制造音乐。后面有打盹被吵醒了的中国学生骂:阿,我操。
小时候造句,总有两个固定的句式:她的脸红扑扑的,像红苹果一样,另外一个是,时光如流水。现在女孩子脸上都是化妆品,红扑扑的不多了。但是依旧不变的是时光似流水,再也追不回。周六和工友下班了去打球,和一些刚来澳洲的二十岁的弦子打,我们像老油子一样打球,把球吊来吊去的,而他们则有着强壮的身体和似乎使不完的劲。我们还很年轻,但是更年轻的出来了。我已经不能更年轻,父母也也不能再年轻回去。这就是生命么,一次性,不能退回去?家乡的朋友跟我说,你快回来吧,高中同学差不多都结婚了。我一直觉得我跟别人一样,最近才知道我的想法以及在别人眼里,有些不一样。
工友说,你回国还担心女朋友么,潜规则么,女人多得是。有些人可以红旗彩旗一起飘,有些人一心不能二用。我还记得贾宝玉被林黛玉逼着交心的时候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我想,只爱一个人是多么浪漫的事。取一瓢饮应该不是孤注一掷。
有从斐济岛来的同学告诉我,她在斐济种了十几年地,从来不吃过夜的菜饭,吃菜就到院子里摘肉呢,则养着牲畜,吃海鲜呢,就乘船自己到海里打。人们不偷不抢。买东西不讲价。别人有十块钱,他看到你没有,他就可能给你五块,因为他觉得那五块对他来说也价值不大。听到这些,我想我真的是井底之蛙阿,真的还有共产主义。这不是人应该的生活么?等我老了,等我没有亲人需要照顾,等我再没有什么梦想可以追逐,我就到那个岛上去,作,吃,等,死。
但是现在,别看我在微笑,也别觉得我轻松,只有我回家单独严肃时才会感到忧伤。
谢谢。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