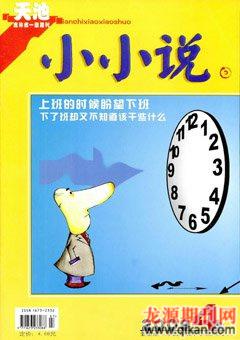丢鞋子
王振东
我们黄土洼人生了病,很少去看医生,也没钱去看医生,实在扛不住了,就用偏方治疗。有些偏方还真管用,有些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可人们实在没钱治病,效果好坏都要试一试。有效果的,人们自然高兴;没效果的,人们会期待奇迹出现。
丢鞋子就是治疗老痫(疟疾)的一个偏方,大家都相信,把发老痫的人穿过的鞋子丢在路上,谁若踩到了,这个人就带走了鞋子上的老痫,发老痫的人病情就会迅速减轻。
童年的每个夏天,我总要发上几场老痫。每次,我仿佛置身于冰窖中,冷得上下牙直打架,伴着寒冷,高烧随之而来。为缓解寒冷,母亲给我捂上两双棉被,让我发汗。我被捂在被窝里,昏迷过去,仿佛被一根荡起的绳子拽住,一会儿飞到天空,一会儿又掉在地上……几场老痫过后,我孱弱得像棵秋后的野草,一丝风就能吹倒。我特别害怕发老痫,以至多年后,每当想起发老痫的滋味,还是不寒而栗。
十三岁那年,我又一次发老痫了。母亲看我烧得直说胡话,坐在床沿上拉着我的手,心疼得直掉泪。父亲外出修水库了,家里没钱请医生。母亲曾多次想到用那个偏方给我治病,可一想到都是乡里乡亲的,让谁带走老痫也于心不忍,迟迟下不了决心。
又一阵有气无力的呻吟从被窝里窜出,母亲赶忙弯下腰,用自己的额头“吻”了一下我的额头,感到还是很烫,眼泪又流了下来。之后,我恍惚看到母亲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毅然走出了屋子……不知过了多久,母亲踉踉跄跄地回来了。母亲俯下身子,对我轻声说∶“娃儿,娘为你丢了鞋子。”说这话时,母亲没有喜悦,相反还有些不安。
就在母亲为我丢鞋子的这一天,从水库工地传来了父亲不幸遇难的噩耗。父亲是在排除一枚哑炮时被炸的……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欲哭无泪。我哭得天昏地暗,被两个人搀扶着送走了父亲。也许是悲伤过度,也许是病体被风吹后受了风寒,回到家,我的病又加重了。越来越弱的呻吟声预示着我可能很快就会去另一个世界。
正在这时,邻居大婶大娘们来看母亲了。兰花婶摸着我的额头,焦急地问母亲∶“给娃儿吃老痫药没有?”
母亲眼里掠过一丝无奈∶“没吃,没钱买。”兰花婶和同来的大婶大娘们的脸上都露出无助的表情。兰花婶叹了口气∶“谁叫咱们都这么穷呢,连娃儿的病都没钱治,让娃儿遭这么大的罪,咱是做的哪辈子孽啊?”
母亲说∶“要搁往常,烧几天,发发汗就好了,这次拖了这么久,还不见好,也不知为啥?”
忽然,兰花婶问母亲∶“你给娃儿丢鞋子了吗?”
母亲一听,满面通红,像蚊子哼哼似地说∶“丢了。”
“那咋还不见好呢?”兰花婶像问母亲,又像问自己,“你把鞋子丢哪儿了?”
“丢到村东的那条小路口了。”母亲心虚地说。兰花婶责怪母亲道∶“你看你丢的地方,你不知道那条路走的人少?怪不得娃儿的病不见好,肯定是鞋子没人踩到。”大婶大娘们随声附和道∶“就是,就是。”
母亲说∶“丢鞋子毕竟不是啥光彩事啊。”
兰花婶说∶“这也没啥丢人的。娃儿小,又不像大人一样能扛住。”接着又对母亲说∶“往后有啥事给姊妹们言一声,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大婶大娘们又附和道∶“就是,就是。”
劝了母亲,兰花婶和大婶大娘们要走了。兰花婶拍拍我的头,疼爱地说∶“娃儿,你的病快好了。要挺住。”
送走大婶大娘,母亲又来到我的床前。我说∶“娘,我渴。”母亲说∶“我去给你烧水。”母亲去水缸舀水,可水缸几乎是干的。母亲说∶“娃儿,你等着,我去担水,很快就回来。”
母亲担着水桶出了院子,朝村东的大口井走去。刚到村口,看见小路口聚了许多人,走近一看,兰花婶和大婶大娘、大伯大叔们正在母亲丢鞋子的地方,起劲地踩着地上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