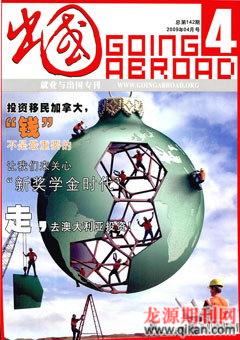美国行医记之一 谋事在人
李强,1960年出生,现定居美国。职业医生,在国内从事医学临床和科研十年,为中国中医学会、康复医学会、人才研究会会员,入录《当代中国骨伤人才》一书。发表专业文章十多篇,多篇论文在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中国儿童发展研究会获奖,合作编写的《中医急诊医生手册》在国内出版。1993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奖学金,以访问学者赴美留学,从事“骨质疏松症”课题研究,多篇论文在美国学术会议交流发表,美国骨矿研究学会获奖。1997年获美国政府“特殊人才”绿卡,从事过中医教学及理疗、针灸临床工作。现为美国公民、美国国家针灸医师资格特考文凭、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担任美国精益针灸医疗服务公司总裁。李强新近出版的书《经历》真实地记录了其坎坷经历和不懈追求,是一部具有个人思想,表现人性、人格与智慧的自传作品。我们将从本期开始对书中跨出国门以及在美国的奋斗历程进行摘要连载,以飧读者。
1978年秋季是文革后首批应届毕业生经高考直接升入大学的日子,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其实就在这批人进校不久,一个里程碑式的对外举措同时在中华大地发生着。这年12月26日,50名中国专业人员奔赴大洋彼岸,以访问学者身份,开始了在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进修生涯。他们是中国与西方世界隔绝近40年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中国的大门也因他们的成行,不可逆转地向着发达国家洞然大开。随着中美建交,这种交往愈发不可收拾。公费、自费、自费公派,读书、进修、工作、旅游、考察、探亲、移民……出国逐渐成为部分中国人生活类别的一种新选项和追求的目标。
翻开共和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新时代的出国大潮实际上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1978年3月,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中国恢复了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以科技人才为主的留学生。那年的7月7日,中美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中方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年底的首批出国者就是这次会谈的“产物”。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组织按指标、名额“安排”或“挑选”的公派人员,在国外工作学习期间可以领取固定的生活补助,回国时还被允许购买免税配额商品一“八大件”。次年,邓出访美国,将上一年中美关于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使得更多中国学生有机会赴美留学。
但即使到了1980年代初,出国仍然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一些幸运的名牌大学高材生才能享有。当时规定,长期驻外外交官员和公派一年以上留学者可以携带配偶,于是有了“陪读”以及类似的出国方式。1982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七个部门申请,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1983年,自费人数1千多;三年后,数字增长十倍;1987年再翻十倍,突破十万,成为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与此同时,1985年,国家放宽了中国公民赴海外探亲的条件,有亲戚在国外居住者,可以探亲出国。无海外关系者也开始寻找别的途径,涉外婚姻为主的移民应运而生。由于旅游和考察人员可以在海外合法转成读书、工作乃至移民身份,后来有些人便选择这种方式先走出去,再“跳龙门”。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简称TOEFL(托福),是为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申请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就读高等院校提供的一种英语水平考试。1981年中国举办首次考试时,全国考生共285人,两年后增至2500人,到了1986年,报考者达到1.8万人。按照当时美、加两国高校要求,TOEFL达到500分就能申请本科教育,超过550分可以申请研究生教育。而对于自费者来说,通过托福考试,获取经济支助,得到留学签证是最为单纯的出国方式。它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主要依靠个人实力就可以完成。继读书之后,寻求对方支助的进修或工作也逐渐成为有效的白费出国方式。两者不一定要求托福成绩,但前者与留学生相比更强调专业水平;后者则要求工作技能,只有本国无人胜任的工作,才会考虑引进。在没有奖学金或工作的雇主时,只要有经济担保人出具得到公证的收入、银行存款证明,以支持其经济能力和担保留学者生活费用的真实意愿,同样可以用来申请签证,有些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支助形式跨出了国门。
《出国出国》是1980年代国内出版的一本热门书,它以报告文学形式刻画了那时人们对出国持有的心态,以及该现象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应该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人员交往的增加是一个必然趋势,其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影响。但由于当时真正“入道”的人在整个社会并不太多,因此在多数平民百姓眼里,出国仍然是神秘的,认为出国人员是国家骄子及杰出人士的私有“财产”、国外关系或达官贵人“奢啬品”者不在少数。随着国家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198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群加入到这一行列,使人们的认识得到提高,我院前后几十人跨出国门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骨科,肖少雄医生是第一个尝试“吃螃蟹”者。
肖外貌酷似相声演员冯巩,毕业于武汉医师进修学院医疗专业,比我早一届。从专业上看,我们中西医之间矛盾大,容易爆发冲突。但经过共事,我俩成为了朋友。我对肖比较了解:反应快,工作认真,讲究效益,为人直爽,不藏心计,不缺幽默和灵活聪明。但含蓄不够、城府不深使他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我俩的区别在于:肖点子多,我韧性强。也许源于早期经历的磨炼,在我决定做某件事情以后,总希望坚持见到结果,这一点对我人生帮助不小。所谓“有恒为成功之本”,我是深表赞同的。
最初肖与国外联系时,我并不看好。在他陆续收到回信后,我开始转变认识。通过咨询已出国的同事陈强华和留美多年的金乔等人意见后,我成为肖的积极支持者。肖对我比较信任,给我阅读了联系单位的回信并征求意见,我也乐意给他当参谋,毕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在肖的鼓励下,我于1992年开始与国外联系。准备好简历和信件,妻子帮我打印后发了出去。
有一天,肖收到一位英国骨科教授的回信,对方同意提供薪水供其到英进修,但必须通过一项考试。因该考试在中国无考点,与拒绝无异。幸运之门并没关上,不久一位加拿大骨科教授回信,愿意资助他到加作研究。如果说没有薪资不可能实现出国进修,这一次可算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加国大门,不过对方留有一个“尾巴”,希望与肖电话聊聊。肖作了准备。因担心口语有限,于是请经历过EPT考试的杨国平代其交流。对方准时电话到医院,双方开始交谈较为投机。但后来有个简单的专业问题难住了“非专业医师”,杨频频问肖。或许对方发现破绽,放下了电话。极好的出国深造机会手指间滑过,我为肖深感惋惜。这也应验了那句名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国外对我院骨科医生的兴趣并没有停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位骨科教授来信,接受我去进修,但无资助。有别于欧
洲或日本的进修者,中国医生没有支助不可能拿到签证,实现进修。这时,一封来自纽约州立大学骨科研究所教授的回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中写道“目前我们没有进修位置,过一段时间如果有也许会考虑你的申请。”
三个月后我去信询问,对方回复道“不知是否有位置,我想先了解一下你本人。如有熟悉你的专业人士推荐,请将他们名字和推荐信寄来。”当我告知同济医大骨科博导王教授和我院骨伤专家鲁主任后,他们非常支持,立即作了推荐。同时我直接拨通电话,用有限的英语向对方表达了我的进修意愿。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方接受了申请,并于1993年4月回信“从王、鲁两位教授的推荐信看,你是一个受尊重、有潜力的专业医师,我愿提供你来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机会,给予一年1.2万美元的资助。”消息令人兴奋,因为国家公派出国进修者月薪仅五六百美元。这时密尼苏达州立大学一位骨科教授也回信:“同意你的进修申请,我可以提供一年免费吃住和基本的生活开销。”在联系的二十多所相关专业机构里,居然两处提供资助,令人吃惊。经过仔细斟酌和与朋友商量后,我最后定下了纽约。
现在回忆起来,亲朋好友的帮助为我冲出国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初我与国外联系时,电脑在国内还是稀罕之物,很少有E-mail交流。采用常规信件,从中国到美国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返回又是半个月,遇节假日或其它因素,耗时更长。然而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工作市场,情况瞬息万变。于是在确定方向以后,我用电话取代了普通邮件。哥哥、陈杰、李毅、廖祝仪等帮我发过传真。有些表格则是先发给洛衫矶的金乔,经其过目后再转送给有关机构。大学同学赵卫星有位朋友在美国进修,那时刚好回国度假。在收到美方正式邀请函和表格文件后,他专门与我谈过相关文书和签证的处理原则。
我还记得发生在我们医院的一个插曲。有天肖在住院部大楼顶层阳台看见电话接头有条线,便将其牵到科室,用于拨打长途,不过从未用过。医院知道后,院周会追查,科主任找肖谈话,那时医院不知道我也正在与国外联系。当时有个准备电话英语交谈内容的笔记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我写在封面上的一句话。其实我很想写上“一鸣惊人”,但我知道这次命运不由自己主宰。老天爷似乎理解我的心理活动,给予了厚爱。
然而回信后一个月过去了,接着是二个月、三个月,一直到四个月都没见到下文。询问方知,原来该大学的外国学生学者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处理文书时,把我的简历弄丢了,于是对方决定把我进修开始的日期推迟到11月份。这一耽搁使我有机会与大陆观众一道,同步观看了当时引起全国轰动的那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
《北》剧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华人在美生活的系列长片。其新颖大胆的拍摄手法,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伤感煽惜的音乐融合,加上大腕姜文和在美华人及西方明星的出演,使其一上映便吸引了众多的电视观众。该剧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艺术家王启明携妻郭燕来到纽约,他找到女老板阿春开的中餐馆工作,郭在老板大卫的制衣厂做工。大卫爱上郭,郭离开王时,将大卫的客户名单交给了他。王在阿春帮助下,办厂获得了成功,并把资产投资办公楼修建。因经济萧条,王的投资损失惨重,试图在大西洋赌城翻身,却输掉一切。大卫发现郭的背叛,将其赶出家门;女儿到美后,吸毒并出走,结果一家人妻离子散。在联系出国时,纽约是我的首选,因此对该剧看得格外仔细。那段“纽约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以及阿春对王启明说的“既非天堂,也非地狱,而是战场”的哲言,给我印象极深。
接到纽约州立大学外国学生学者办公室的正式来函后,我将材料翻译成中文,送到院长办公室,并找到了李恩宽院长。希望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停薪留职手续,这是我首次为个人私事与他打交道。李出自中西医结合内科,先任副院长,在原任院长李辉樵升任卫生局长后,他被提为院长,曾多次访问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多国,具有典型的官员派头和形象。
听完我的叙说并审核材料后,李官事“官”办,不同意我出国。理由是联系出国需经医院同意,免不了“培养多年,祖国需要”之类套话。不过全院职工都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早已被送往日本进修。也许中国的事情只能靠“中国特色”来解决,正好卫生局一位前任副局长在高干病房住院,朋友胡玲的姨妈带我跟他谈过后,对方满口支持。不久院长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同意我的工作时间计算到年底,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停薪留职,而且一留便达5年之久。
填好因私出国护照申请表,我将医院介绍信、照片和美方邀请函,以及100元人民币手续费随表格一道交给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一周后拿到护照。然后坐上38次特快列车来到首都,并找到住所。次日一早便去了位于朝阳区秀水北街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看了签证申请表后方知它们也要个人简历,因事前没有准备,我乘当时已经风靡北京的黄色面的赶到电报大楼,要妻子从家里传真了一份。返回使馆后,众多排队签证的人群让我一阵紧张。我填好签证申请表,再次清理所有的材料,并静静地排在了队列之中。
这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因公,因私,有的甚至已有十多次签证经验。只要有人办完签证从使馆出来,外面的人们总会凑上前去打听结果,试图获取一些信息。出来的人有愤怒,有埋怨,有懊悔,有惋惜,当然也有高兴,不过被拒者不成比例地多过拿到签证的人。大部分人从使馆出来便快速离开,也有个别人乐于回答大家的提问,或者介绍一下签证官的“好”与“坏”,同时没忘作番提醒。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终于进到了签证厅内。
里面的人群还是被一行行金属绳索分隔成队列,我只得继续耐心地在等待中慢慢前行,不过倒是可以看到签证的程序了。厅内工作与等候区通过墙壁分开,里面大约有三四个窗口,为全封闭玻璃屏障,西人模样的签证官与申请者从玻璃窗底部空隙传递材料。对话听不清时,他们会用麦克风与外面进行交流。最侧边是个开放的带门窗口,一位华人模样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先对申请者材料进行预检,通过以后才能进入签证的窗口。
从开始到结束,近两个钟头的排队,最后终于轮到了自己。我走上前去,将预检通过的美方邀请函、IAP66表、签证申请表、中国护照、照片以及办理签证缴纳800元人民币收据等材料从玻璃窗底部递了进去。这时签证官朝我看了一眼,把不需要的材料退了回来,接着用英语问道:“去美国干啥?”答:“做研究。”问:“在什么地方?”答:“纽约州立大学骨科研究所。”问:“哪里?”“什么?”我不解地反问道。对方加了一句:“哪所分校?”答:“石溪。”结束问话,签证官签字盖章,将一张条子通过窗口递到了我的手上,这是完结的标志。我没细看,拿着纸条便走出了签证大厅。不过我清楚是张黄色纸条。这时,有经验的申请人已经冲着我喊了起来:“你过了!”原来凡是未通过签证的人,都会
拿到一张自条,告知被拒的原因。只有通过者可以凭黄条在规定时间取回带签证的护照本。那么这张不起眼的小纸条意味着美国的大门终于被我叩开了!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我马上找到一家私人电话亭。一通号码拨过,传来父母关切的询问。“签了,我的申请批了!”听得出对方也在为我高兴。是啊,这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听说精英云集的清华大学,学生发出高达300封信件,却没得到资助去美留学的不乏其人。我放下电话,一组数字从窗口进入眼帘“1993年10月26日”,这天恰好是我来到人世间的33周年纪念日。
一周后返京取证。拿到护照本后,我来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看着熟悉的纪念碑、天安门、大会堂和纪念堂,心情难以平静。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作为在校生代表,我有幸参与了文革后第一次的激烈竞争。1978年,我成为首批从中学经统考直接入大学的学子,并见证了轰轰烈烈的那段历史。在当年底开始的对美开放留学15年后,命运再次把我推向幸运者之列,让许多人心中遥远、缥缈而又色彩斑斓的梦想,在自己的努力下成为现实,使我有机会即将跨出国门,到地球的另一边去真实地体会“另一种活法”,这怎能不令人欣喜万分?
就在我漫步在广场四周时,大约下午3点左右,一组车队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车内走出高大魁梧的江泽民总书记,原来当天国家有重大外事活动。迎宾礼炮让我兴奋,感觉仿佛包含对我的祝贺之意。
回汉后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去武汉市工艺美术大楼购物时,我的一辆崭新永久牌26型自行车在马路边被盗。真所谓有得有失,动态平衡。按照院方不成文的“规定”,在医院内不得声张,也不能与同事告别,因为我必须“工作”到年底才能公开身份,颇有文学作品描述当年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后区的感觉。于是我请了一个自从到医院工作以来最长时间的“事假”,这个假期一直延续到了一个多月后的1994年,所有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福利”也享受到了那个时问。
11月14日是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们全家人去了武汉市中山公园。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妻子、侄儿、儿子和我一道,在这片十分熟悉、进出无数次的景地合影,留下许多珍贵的纪念照,后来在去幼儿园接孩子时,我为他在那里拍下了出国前的最后两张照片。
最后与家人分别的时刻来到了。11月22日下午,当我离别生我、养我并抚育我成人的父母和从未长久离开过的家,看到5岁儿子期盼的目光,心里一阵酸楚。我坚持着没让他们下楼,然后和哥哥、嫂子、妻子乘省公安厅专车来到武昌。嫂子的单位姚家岭一家豪华酒店为我举办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处长、科长均出席,大家给我许多良好的祝愿。晚上胡安荣科长开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哥嫂、侄儿一直送到站台。随着火车一声长笛,带着故乡一片深情,我和妻子一道再次奔向了首都。
那年冬季,北京的天气特别寒冷,白雪覆盖了整个大地。到达当天,我花了大约8千多元人民币买下飞往纽约的中国民航机票,然后去拜会母亲认识的一位洪湖的解放军战士。他在北京卫戍区工作,住故宫。自从1990年第一次到北京以来,每次到首都我都会去看望他,但他那天刚好不在家。我和妻子在故宫匆匆转了一圈便回到住处,晚上吃了到京后最为丰盛的一顿佳肴。
第二天,我在北京机场拨通了出国前给父母的最后一次电话,他们话语流露出十分的关切和依依不舍。办完登机手续并与妻子道别后,进人行李检查通道,不知何故对我随身包裹检查得特别仔细。坐上位置方知,因飞机故障全体乘客必须改乘次日航班。意外,却又无奈,我们被送到了市郊的回龙观饭店住宿。该店店名由胡耀邦题字,在胡任领导人期间,我很少看过他的题字。此时见到,倍感亲切,也颇有几分感慨。
次日中午再次登机顺利了许多,当波音747班机飞向蓝天,大地渐渐远去时,我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的曲折经历,心中不禁一阵翻腾: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和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