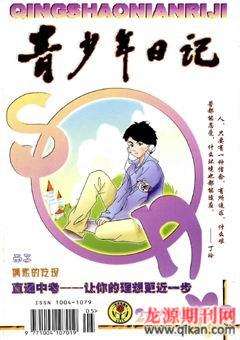想念故乡的枣树
王黎冰
2月2日 阴
想起故乡,就很自然地想起外婆院中的那棵老枣树。
这些年,似乎所有关于故乡的回忆,只需一棵老枣树就能代替一样。于是,想家人的时候,总是有树的影子像幻灯片一样闪过,在记忆的深处,在浓浓的月色里,在蓦然回首的那一刻投影到我的眼前,让我那浮躁喧嚣的内心一下子沉静下来。
那棵老枣树是祖爷爷小时候种下的,粗算起来至今已经有80余年了,虽然它主干有些歪斜,分岔处只剩一半的身躯,但这丝毫未影响它顽强地生长,更未影响它用枝叶给老屋撑起一伞的荫凉。它的皮肤被岁月雕刻得粗糙无比,但它依然会在每年的秋季结出又甜又脆的枣儿。
小时侯,基本吃不到什么刚从树上采摘的水果。于是,外婆家枣树上的枣便成了我们所盼望的美味。我和姐姐往往等不得枣儿半青半熟,就偷偷地拿根小竹竿悄悄地打枣,或者拎只鞋子扔上去,这时候便有枣儿被打下来了,我们趁机过过馋瘾。
好不容易等到枣儿熟透,盼到“打枣”那一天的来临。外婆一般把“打枣”安排在星期天的清晨,并且提前告诉我们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尔后准备好竹篮、大笸箩、盆等盛枣的家什。外公则提前绑好打枣的竿子担当了“打枣”的重任,而我们和邻居的孩子们负责捡枣,外婆只管守着大笸箩收枣。
外公让几个表哥先是“噌噌”爬到高高的枣树上“晃枣”,那个时候是令我们最兴奋的事情。他们一起用劲摇晃树枝,那枣儿便铺天盖地地砸下来,落到屋顶上,打到盆里、笸箩里,打到我们头上,到处是“叮咚”的声音,我们争着、抢着、笑着、捡着满地乱跑的枣儿,那一刻满院子的枣儿,满院子跑着的孩子,满院子的笑声,和着被惊吓的狗的汪汪声、鸡的喔喔声,在清晨的阳光里跳跃着飘荡着,就那样永远地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晃枣”结束后,外公便踩着椅子拿着长长的竹竿“打枣”,而我们疯抢着把枣捡进盆里,然后倒进大笸箩里。这并不妨碍我们嘴里塞满甜枣和把那又大又好的“枣王”偷偷塞满裤兜。打完枣后,邻居家的孩子各自用衣服兜着一堆枣儿回家了。
剩下的便分成几份给本家的大爷、二爷还有姑姑。外婆手巧,把剩下的硬硬的枣先在酒碗里蘸一下,然后把它们放进密封的坛子储存起来,这便是“酒枣”了,直到明年开春这些枣也不会坏。
老枣树是有生命的,所以它一定有记忆,看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归的温暖,一种没有纷扰的宁静。它让我以善良、淳朴、执着的本色迎接路上的风风雨雨。
我知道老枣树的记忆里有我,我的记忆有老枣树,那棵饱经岁月沧桑的老枣树用它最自然、最顽强的生命写在了我心的深处,成为我生命中最深的回忆。
四川绵阳三台县芦溪镇南外街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