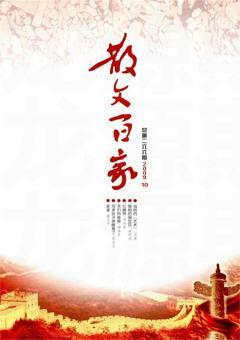玻璃
戴天孚
玻璃,带有很强烈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它是在什么时间、由什么人发明的。大概是在二千六百多年前吧,也许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的一个莫名工地上,或许是在古埃及的一个手工作坊里,那一次偶然的、从未有过的、不受人控制的超高温中,它绚丽地诞生了。
从它诞出的那日起,似乎就与同时期的东方瓷器有着某种暗合,只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对此做过比对——对它们的诞生、对它们的性格、对它们对人类想象的丰富和推动。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最初的玻璃一直不是透明的,它每一次的诞出,都携带着不同的色彩和器状。我想,那大概该是混沌一片中勉强透露出的些许色彩。但是,这对于远古的人类来讲。对于一直在素色器物里生活的人类来说。那种难得一见的、偶然出现的色彩也足够引起长久不衰的兴奋了。后来,在漫长的一千年里,不管它的工艺和面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玻璃,都一直是摆在贵族家里的奢侈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玻璃曾经是人类的信仰!
古老的历史、变幻不定的色彩、专属于贵族的奢侈品,其中单列出任何一种元素都值得人们去敬仰,更何况它聚合了人们所有对器物的宠爱。有人毫无节制地收藏它,直到倾其所有;有人旁若无物地终生研究它,终无结论。那份投入,怎一个爱字了得。
我知道,喜欢玻璃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但肯定得算我一个。
最初认识它,不知道是在我的什么年龄,也不知道是摆在哪家的书桌上,是的,我只记得是在一个很简陋的、甚至是有点寒酸的书桌上,它通透之中的若有似无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直到后来,我认识并使用过了很多的器物,还是觉得它是所有器具里最富浪漫气质的。通透,把它的天真、率直毫不掩饰地呈现给你;幻彩,用它的丰富和百转柔肠软化着你;经久,是它不老的容颜让你对它的痴迷总是这般的年轻和如此地跳跃。在这种对玻璃的跳跃的迷恋当中,我也一直不肯把它当成是平常器具,因为它那若有似无当中,深藏着某种机缘。
常常地面对玻璃发呆,就成了我的一种消遣。我渐渐地发现,玻璃的性格也很令人着迷。作为器具,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都可以,酸、甜、苦、辣它都一样恭恭敬敬地承接着,它也从不对自己的主人挑剔、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它从不挑剔自己“包装”的内容是什么,只是尽自己的通透、经久之本分,安静地、安然地,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有时我甚至对它有些不悦——那安静好像是一种另外的傲慢。
直到那天,我做了一个梦。
好像又是一次考试,在一个硕大的玻璃房子里,老师给我们两个命题,可以任选一个。其一:“鸽子只相信蓝天”;其二:“小熊只相信食物”。哇,这次的命题还真有点创意!像看到了美味的食物一样。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先“咬”谁一口……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淌着,奇怪的是,我分明是在急匆匆地写着,可是雪白的纸上却一丝划痕都没有。难道我笔下的白纸是玻璃做的吗?
随着交卷铃声的骤响,我的两篇没有划痕的作文纸变成了两个通透的玻璃房,一大一小摆在讲台上。小的只能叫做玻璃罐,一只灰色的小熊把头伸进去取食物,自己的头无法退出来,挣扎了一会后,它似乎并不知道绝望,索性把罐子里的食物舔了个干干净净;大的那个,可以叫做中型玻璃房,里面有十几只红嘴鸽子,一个劲地扑棱着翅膀往外飞。刚开始,它们把翅膀最大限度地展开,用力地扑在玻璃上,甚至把自己的肚子也一并用力地贴在玻璃上。可是,当它们发现这样的努力还不奏效时,它们变得焦躁起来——把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狠命地“摔”在玻璃壁上……鲜血,像大写意时的点染一样,渐渐地把这块玻璃燃烧成了绝美的琉璃壁画。
这样的梦惊醒之后,我还在想标准答案。
答案就在玻璃中。
在我国的南方某地,有一个三口之家。男的在外打工,家里剩下年轻的母亲和他们5岁的儿子。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女主人有些寂寞,于是渐渐地被隔壁的麻将声所吸引。那天,她带着儿子去串门,隔壁的女人热情相约并答应帮忙看孩子。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女人沉浸在麻将世界里,直到散局要领孩子回家时,才发现孩子已经死了——头朝下,死在装有半缸水的玻璃鱼缸里,而他身边的鱼儿仍全然不知地欢快地游荡着。想必这孩子把鱼缸当成了小溪,他只想与鱼儿嬉戏,却不知那是一条回不来的“小溪”。
我突然意识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能认知玻璃、与玻璃共生的生命太少了,除了发明它的人类(必须是有自主意识的、自我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以外。几乎所有的生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看,玻璃的发明简直就是一场阴谋。
最初,玻璃的出现就是为了作器皿之用。但是,不管它在盛放什么,液体还是固体,都是在起到一个“限制”的作用,在限制中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而后,玻璃又被引用到建筑领域,经过特殊处理后,它可以代替屋顶、墙壁、楼梯……至此,玻璃的作用在人们不经意之间却产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但可以限制一些没有生命的物质,还可以限制很多有生命的物质。是的,小熊只相信食物。鸽子只相信蓝天!
我们又在相信什么?!
我们在代代相传着一些经验,经验在很多需要我们做出判断的时候都是“真理”;我们还相信一些规则,是大量的规则在帮着我们在生活中取舍;我们更愿意把这些经验和规则当成自己的“法律”……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蓝天下层层叠叠的玻璃房,大房之下有小房,小房里头还有更小的,而大大小小的玻璃房里“关着”的全是人类自己。
是玻璃让生命产生了痛苦。鸽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触摸不到蓝天,它只会怪自己不够努力;小熊不知道自己眼前的美味是“最后的晚餐”,因为它不知道食物可以伪装成陷阱;人类不知道自己的心智外从出生之日起,就积累起了看不见的玻璃墙,哦,原来所有的困惑和情感上的痛苦都源于玻璃和玻璃里面的东西!
至此,玻璃从限制无生命的物质,到限制有生命的物质,再到限制生命本身的思想感情,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在这个世界的最高表现形式。一个简简单单的玻璃,一种天真、浪漫的物件,一个通透的毫不设防的物质形式,就这样通过残忍的低语,在告诉我们关于挣扎、关于困惑、关于痛苦。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喜欢旅行,那是一种穿越的快感。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不管天有多高、地有多远,那总是可以丈量的距离。于是,我们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借用各种交通工具去丈量,每迈出一步,体会的都是一份完整的自由,更具有诱惑力的是,在路上的时候,往往是距离困惑、痛苦最远的时候,距离自由、轻松最近的时候。自由,你知道那是玻璃以外的东西吗?
而玻璃是制造距离的最佳选择。我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玻璃的两边,
“扑棱”着一对眼泪汪汪的男女,可能是恋人吧;玻璃的两边,站着永远也握不到对方手的男人,可能是政敌吧;玻璃的两边画着同样的风景,可对方都以为只有自己是惟一的……
玻璃,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哲学命题。
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玻璃都是无法伸展的,它仅以“罐”的形式出现。被它罩住的东西因此平添了些许想象、许多色彩。后来,如何让玻璃平展开来,折磨着、长时间地折磨着玻璃匠们。也许,他是被上帝选中的,在一个世代以玻璃为生的家族里,在经过了不能再忍受的苦思之痛后,那个男孩似乎轻而易举地就用自己的工具把祖辈们又恨又爱的、被烧红了的、软软的玻璃(半液体半凝固状)像舞蹈似的舒展开来。以至于在旁边观看的他的老祖父十分不解:为什么几千年树起的那堵“墙”是在这个小伙子手里推倒的?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原来它的“解”一直就绕行在我的身边……实话说。这个老祖父同样也没意识到平板玻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它最初的诞生。有了平板玻璃,人们不但改写了建筑史以及和电子产品等有关的一切领域,还使得人们对“窗户”的想象摆脱了“盲窗”的现实,才有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能看得出望得进的“窗户”。是啊,有的时候,玻璃的意义就在于它能成为“窗”——透过它,我们有了再一次认知这个世界的机会。
回过神来,玻璃仍旧那样亭亭玉立地、安然地、心满意足地站在那里,所不同的是,玻璃上多了很多看不见的“窗”。
玻璃上本该有窗的。我还是喜欢玻璃,只要玻璃上有“窗”。
从这以后,因为窗子,我更加喜欢上了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