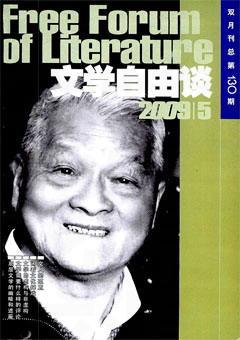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
李建军
由于外在的原因,我最近重读了几篇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其中一篇,就是魏巍的通讯特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这篇作品我上中学的时候,不知读过多少遍,也不知在作文中多少次模仿过那种气贯长虹的排比句式,但是,今天重读,却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感受。令我尤其好奇的是,这样一篇看去普通的报道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拂去岁月之尘,找到久被封埋的答案,似乎并不很难。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3500字左右的“新闻特写”性质的文章。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
这篇文章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都望着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魏巍,热烈鼓掌),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在接下来的书面讲话里,周恩来赞扬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
从此,《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便家喻户晓,流传中外。
它顺理成章地被选人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在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无数中学生口诵心惟的必读文章;1951年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先后印刷22次,发行达数十万册。也许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新闻稿,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会获得如此隆盛的殊荣。
那么,一篇短短的通讯报道为什么引起高层的重视?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赞誉呢?
从艺术形式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其实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语言是平实的,既没有非常个性化的修辞技巧,也没有灵活多姿的叙述方式。无论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是收入同名散文集中的其他16篇文章,最常用到的表现手段无非是设问、排比、议论和抒情。尤其是设问,乃是《谁是最可爱的人》用得最多的修辞手段,在不足四千字的篇幅里,竟然用了12次;不仅用之于作者的叙述语言中,也用之于人物的话语中。这种充满抒情性的设问修辞,既有助于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有助于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同时,也有利于强化作者抒情的感染力和议论的说服力。从叙述方式来看,魏巍的特写呈现出这样一些模式化的特点,那就是,首先用设问或其他方式显示“观点”,然后用一个个由“故事”构成的事实来证明它,最后,再用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方式来强化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
《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文本,首先是因为它在内容上显示出很强的时代性,极大地满足了自己时代的现实需求。按照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文学价值观,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决定于它的社会价值,决定于它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丁玲在《读魏巍的朝鲜通讯》(发表于《文艺报》1951年5月25日第四卷第3期)中,高度评价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冬天和春天》,针对“有人以为虽然写得好,不过只能说是通讯,算不得文学作品”的质疑,丁玲的回答是:“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他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是文学,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文学价值的大小,完全决定于作品的内容,尤看它是否表现了当下的“伟大事业”。魏巍的通讯特写无疑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新生的人”,他的“出色”之处就在于他对于“最可爱的人”这一话语的创造性的构筑和表达。“最”是一个表示高级形态的副词,“可爱”是一个表达内心由衷的喜悦的形容词,而且用来指涉孩子和女性等秀美的人或事物,魏巍将这两个词合成为一个短语,表达对孑L武有力的军人的情感,无疑有着别具新意的“陌生化”效果,无疑有助于人们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产生强烈的感情。所以,吉悌才在《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发表于1960年第8期《解放军文艺》)中说:“最可爱的人”,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光辉的形象化。通过魏巍同志的文章,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战斗精神、英雄精神更为发扬光大了。“支援最可爱的人,学习最可爱的人,作一个最可爱的人!”成为我们全民的口号。“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的那个历史时期里,几乎成为我们全民的道德标准。在我们志愿军里,最严厉的批评,无过于“你称得起一个最可爱的人吗!”同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最严厉的批评,恐怕也无过于“你对得起最可爱的人吗!”
真正表现了、发扬了时代精神的作品,它的威力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的影响才会如此的深刻。
是的,正是因为“表现了、发扬了时代精神”,正是因为满足了进行社会动员、激发斗志以及牺牲精神的需要,所以,“它的威力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的影响才会如此的深刻”。
强烈的抒情性无疑也是魏巍的“新闻特写”写作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作品获得好评的一个原因。他的抒情不仅在内容上显示出极强的时代性——对英雄的赞美、对领袖的崇拜、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乐观、对幸福的感恩,而且,在形式上也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特点——这是一种被强化的抒情方式,属于直接的、不加掩抑、甚至略显夸张的宣抒: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魏巍作品的被强化到极端的宣传性和鼓动性,无疑满足了战争动员和激发斗志的时代需求。他因此被当作“革命的鼓动家”。吉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怀着赞赏的心情肯定了这一点:“曾经有些人怕当不成伟大的艺术家,不甘做坚决为革命服务的‘煽动家。很显然,魏巍同志不是这样的人。魏巍同志是一个为革命服务的鼓动家,或者说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鼓动宣传员。……当魏巍同志觉得通讯特写这种形式是更快当、更直接、更能说明问题、更能和广大读者及时见面,因此也更能发挥鼓动作用的时候,魏巍同志毅然抓起了这个武器。”他还准确地概括
了魏巍的“新闻特写”的基本特点:“魏巍同志的抗美援朝散文是政论、特写和抒情诗的完美的结合。而把这三者合而为一的是奔腾澎湃的战斗热情。魏巍同志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所为的,都是有目的的,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的;当他认为要说道理时,他就毫不迟疑地把道理摆出来;当他认为要鼓动一下时,他就大声呼唤;讲着讲着,忍不住激动起来,想倾吐一下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感情倾泻于笔下。”可以说,正是这种将极度的自豪与无限的感恩之情融为一体的抒情和“政论”性质的“鼓动”,极大地满足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需要,从而使它成为无数读者和青年学生学习的范本。但是,一种写作方式的优点,有可能也正是它的缺点。魏巍的“通讯特写”美学上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一览无余,淡乎寡味,经不住从容往复的含茹吐弃。
从战争叙事的角度看,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真正的特点在于他对战争的酷烈场面的接近自然主义的真实性。由于复杂的原因,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战争文学叙事常常回避对死亡和牺牲场面的过于细致的呈现,往往显示出一种避实就虚的浪漫主义特点。然而,做为一个新闻记者,魏巍的笔下的战争描写,却显示出了记者的在场感以及对真实性的本能忠诚:敌人为了逃命,用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个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聚歼了敌人。
许多年之后,作者的那些议论和抒情的话语,会因为时过境迁而被人们淡忘,但是,这些梦魇一样的场景,你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忘却,就仿佛扎入记忆深处的长长的芒刺。从表现战争的惨烈性这一角度看,《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这些细节,令人想起了《静静的顿河》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尽管相似的细节表现着不同的情感态度,但是,就描写的真实效果来看,却是一样令人震撼的。
1957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俄译本。C·马尔科娃在序言中写道:“魏巍的这些特写作品现在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在这些作品中,他真诚地赞美、歌颂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的每一篇特写,都浸透着难以遏制地相信普通人、相信人民的光明未来的信念。这些特写作品,现在仍未失去其魅力。”然而,进入新世纪,魏巍的这篇作品,却被新编的中学语文教材拿了出来。令人意外的是,这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和太大的响动,没有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和争论的话题,直到他2008年逝世之后,才在网上有了一点声音微弱的争论——有的说《谁是最可爱的人》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标志着时代生活的进步,有的则说应该重新将它编进教材。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应和的人,似乎都不很多。
五六十年前,埃德蒙-威尔逊在谈及文学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时候,曾经用过“长效文学”和“短效文学”两个概念。我不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底属于长效文学,还是短效文学,但它的确是一篇与时代生活的“相关性”很强的作品——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正是因为它满足了时代对文学的这种“相关性”要求。
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尤其在反映战争、灾难等严重的社会事件的时候,文学常常会仅仅因为“相关性”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和阐释语境的转换,或者,换句话说,当直接的“相关性”被间接的“历史性”取代的时候,对这种作品进行解读和评价的难度就会增加,甚至会有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和评价,除非这些作品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感和普遍的情感内容,否则,它就很难感动后来时代的人们或不同社会的读者群。
那么,《谁是最可爱的人》具有经得住时间之水洗磨的“长效性”吗?未来的读者阅读它的时候,还会像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那样感动吗?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时间自己能够回答。
时间是文学最难跨越的障碍,是它也许拼尽全力仍然很难战胜的敌人。
然而,不管怎样,我希望,那些属于过去的作品,也能属于现在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