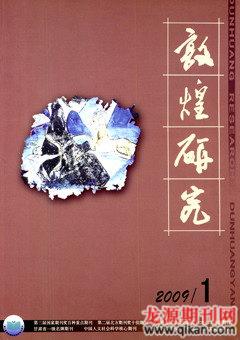关中北朝造像碑龛楣道教图像考释
张 方 郑 文
内容摘要:通过对关中地区道教与佛道混合造像碑上的一些典型石刻图像进行考释和解读,可以发现当时佛道信徒在建造造像碑时就把早期的神仙传说题材作为其进行创作的思想源泉,在造像碑上刻画大量表现传统宗教中的长生和成仙思想的图像。这对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整体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该地区造像碑从一开始就与我国传统宗教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特征。
关键词:关中;造像碑;石刻图像;宗教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26-07
在我国,早期的道教造像艺术资料发现甚少,因此,关中地区现存的大量表现道教图像的造像碑在早期道教艺术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中地区是道教早期活跃的地区之一,目前在“渭北地区发现的北朝至隋代道教、佛道混合造像碑的数量就有五十余通,占目前全国已知同类资料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对关中地区这批涉及道教图像的造像碑进行研究,对于厘清我国早期道教艺术的线索会有所裨益。

初始的道教并不注重形象的塑造。据唐释法琳的《辩证论》卷6之自注说:“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卢盛经,本五天尊形象。按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云:‘道无形质,盖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到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传人,佛教的造型艺术逐渐发达起来,佛教徒崇尚造像礼佛,极力推崇观瞻佛像。在此影响下,道教徒们为了争取信徒,也模仿佛教开始打造道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作形象,故假号天尊,乃左右二真人,量之道堂,以冯衣食。宋陆静修亦为此形。”释玄嶷《甄正论》亦云:“近自吴蜀分疆,宋齐承统,别立天尊,以为教主。”关中地区道教造像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始打造的。
关中地区除了一些道教造像碑外,还有大量的佛道混合造像碑,这在南北朝佛道斗争激烈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佛教在初传我国的时候多是借用我国早期宗教艺术形式,佛像等同于仙人。而在当时民间信仰中人们并不能区分佛与神仙的区别,所以把佛和仙人一起祭祀,这种早期民间信仰中将佛视同诸神来拜祀的现象即使到了佛教造像发达的南北朝时期仍在关中地区有所遗留。据宋敏求《长安志》卷5载:“后秦姚兴集沙门五千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做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闻,皆以为稀奇。这里仙人佛像具有,说明当时佛教徒把佛像和中国早期宗教中的神仙一起拜祭。而当时在关中兴盛的道教同样吸收了这种佛即神仙的早期宗教思想。《魏书。释老志》引寇谦之的《录图真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说明当时道教徒同样把佛看作道教中的一个神仙,由此看来在关中地区出现佛教徒和道教徒出资共建的混合造像碑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说道教模仿佛教造像,并且与佛教徒共同出资建造造像碑,但是道教徒在一开始造像时,就力图与佛教造像区别,使其独立于佛教造像艺术而自成体系。《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云:“科曰:凡造像皆依经具其仪相……衣冠华座,并须如法。天尊上帔以九色离罗或五彩云霞,山水杂锦,黄裳,金冠、玉冠。”“不得用纯紫、丹青、碧绿等,”“左右二真皆贡献或持经执简,把诸香华,悉须恭肃,不得放诞手足,衣服偏斜。天尊平坐,指捻太无,手中皆不执如意尘拂,但空而已。科曰:凡天尊、道君、老君左右,皆有真人,玉童、玉女侍香侍经。”“如不依规定,或稍有不恭,鬼神罚人,既非僭滥,祸或无乎。”所以道教并不是简单一味地模仿佛教的造像,而是有一个严格的造像制作规程。从关中地区的这批道教造像碑来看,造像龛形、衣着、碑面图案等都与佛教造像碑有明显的区别,这些都是道教徒为了区别于佛教而刻意雕镌的,比如道教造像碑中的龛形一般为屋形龛,座为床座,用以区别于佛教的尖拱龛和倒梯形方座。这种趋势在佛道混合造像碑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临潼博物馆所藏的师录生佛道混合造像碑,其碑阳为佛教造像,在佛龛的周围造像者饰以千佛图像。千佛是佛教石窟中常见的佛教题材,《法苑珠林》卷8《千佛篇》云:“初千佛者。华光佛为首,下至毗舍浮佛,于庄严劫得成为佛,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贤劫中次第成佛。后千佛者,日光如来为首,下至须弥相佛,于星宿劫中当得成佛。”而在其碑阴的道龛周围则饰以群龙和象征日月的三足乌和蟾蜍,群龙和日月都是我国传统宗教思想中仙界的象征。《十洲记》载:“方丈洲在东海中心,西南东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专是群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之处。”《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龙门,日月所人。”由此可见,教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更是大量地吸收了流传于民间的传统宗教艺术中的神仙美术题材,试图用传统的民族艺术来区别于佛教,显示其为华夏的正统宗教,也是当时道教欲与佛教一争高下的手段之一。
道教在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早期宗教的思想和艺术,早期神仙传说是道教传说的直接来源,长生成仙说又成为整个道教的核心教义,因此,道教徒在建造造像碑时就把早期的神仙传说题材作为其进行创作的思想源泉,关中地区的这批造像碑中就出现了大量表现传统宗教中的长生和成仙思想的图像。这样一来造像碑上的图像从思想和雕刻技法上都和汉代的画像石形成了一种承继的关系。
汉代所形成的不死和升仙思想,了魏晋以降随着道教的发展而更加兴盛,大量神仙志怪小说的涌现更为这一时期的宗教艺术提供了鲜活的题材,如《十洲记》、《列仙传》、《穆天子传》等,这些小说或为道家收为经典,或本身就为道士所作,后来收录到《道藏》之中。关中地区的道教图像有很多正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神仙志怪小说,表现了当时道教徒的长生和成仙的愿望。笔者从收集整理的数十通造像碑中选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吴洪标兄弟造像碑,并对其碑额的道教图像进行考释,用以说明此问题。

吴洪标兄弟造像碑,1934年出土于耀县雷家崖,现藏于药王山博物馆,上小下大呈梯形,尺寸为150×66×25厘米,两面均为道教图像。此碑在李淞《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和罗宏才博士论文《造像碑源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均有著录。此碑阳面碑额上图像丰富而且精美,颇有汉画像石的遗风,具有典型意义。此图像还未有人进行过考释。
此碑阳面龛楣为二龙相交,道教造像碑中非常常见。龙本来就是我国传统宗教艺术中升仙的象征,但是它与佛教艺术的渊源同样很深,此处涉及问题较为复杂,另作它述,首先,我们来看图案中的三个圆轮,图1中①居图案中央、二交龙之上,②与③在二交龙两边。
图1中②与③图像易解。②图像清晰,圆轮
中有蟾蜍与兔。兔与蟾蜍在西汉图像传统中一般与月亮有关。《淮南子,精神训》曰:“月中有踆乌,日中有蟾蜍。”《后汉书·天文志》注引《灵宪》云:“姬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另外兔是西王母长生不死药的捣制者,蟾蜍在传统观念中能够死而复生,二者也体现出了长生不死的观念。因此,②的圆轮代表月亮。图③圆轮内图像漫漶不清,传统宗教艺术中的日月图像多为对称。关中地区造像碑碑额刻有左月轮、右日轮的图像也不在少数,如锜双胡道教造像碑、师录生佛道造像碑、锜麻仁道教造像碑等。因此,图③的圆轮应是表现太阳。
①为内外有三层图案的大圆轮,在其他造像碑图像中未见类似的图像。要解释此图像,我们先注意双龙与日月图案。《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龙门,日月所人。”同书亦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妪天门,日月所人。”再结合出土的一些画像石和铜牌所表现的西王母端坐在天门之中,两边伴有日月或龙的图案的图像,我们可以认为,在造像碑中人们把传统的天门图案与佛教中的佛龛艺术相融合,龛楣上双龙和日月图像说明造像者用道龛象征着天门,只不过天门中端坐的不再是西王母,而是道教的老君、天尊等。这样一来,图①就弄清楚了,在南北朝时成书的《神异经,西北荒经》对天门曾有这样一段描写:“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金阙银盘高五十丈,二阙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人两阙中,名曰天门。”《诗纬含神雾》亦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也。因此,图①即为《神异经》所说的“明月珠”,此碑中将其雕刻为三层用来表示其径为三丈。而此珠在二龙之上,正如《诗纬含神雾》描述的“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也”,此图案亦有可能就是后来民俗中常出现的“二龙戏珠”的雏形。
图④和图⑤是“明月珠”两边对称的一对飞仙形象。佛教造像碑中飞天的形象比比皆是。此处的二飞仙的形象比较独特,决不类于其他造像碑中的飞天的形象。此处两位仙人衣饰豪华,衣袖裙摆都似鸟羽编织而成。《拾遗记,颛顼》载:“溟海之北,有勃韆之国。人皆衣羽毛,无翼而飞,日中无影,寿千岁。食以黑河水藻,饮以阴山桂脂。凭风而翔,乘波而至。中国气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此处所刻的应为长寿的勃韃国民。会飞的仙人形象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这与人们渴望不死的观念有关。《楚辞·远游》曾云:“仍羽人于丹上兮,留不死之旧乡。”,此碑之所以雕刻衣羽毛的仙人,应是道教徒为了区别佛教的飞天而刻意打造的。无论如何,在当时人的观念中,飞天与羽人都是释道融合的精神产物,并无明显的分野,都只作为人们升仙的象征而已。
图⑥至(12)是众鸟的形象,7只鸟的形态各异,图⑥、⑧、⑨、⑩的鸟皆衔一棵草,鸟衔草的图案同样也出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田良宽道教造像碑的碑阳龛楣中(图2)。据《海内十洲记》载:“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两岸,七万里,上有不死神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四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如乌状,衔此草覆死人面,当时起坐而自活也。有司奏闻,始皇遣使者,赍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其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人海寻祖洲,遂不返。”碑中图案的鸟所衔之草即此不死神草。仙鸟衔物的图案在山东汉代画像石中曾出现过,西王母两侧青鸟衔食的图案。据《山海经·海内北经》云:“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但鸟衔仙草的图案在此前的艺术图像中似未曾见过,而记载“不死神草”的《十洲记》、《神异经》成书年代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鸟衔仙草的图案应该出现并流行于这一时期。后来这种图案逐渐成为我国民俗中常见的一种祥瑞图案,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如北齐徐显秀墓墓门门额上方的凤鸟衔草的图案,莫高窟晚唐第16、196窟中心背屏上也画有双凤衔环形卷草图,都应渊源于此。
观察众鸟的图像应为雄鸡、鹳、鹊等。雄鸡的图像在造像碑中有很多,如耀县药王山碑林所藏之魏文朗造像碑的碑阴龛楣上就出现过两雄鸡(图3)。在古代的俗信观念中,雄鸡是具有降妖除害、驱鬼避凶的神力灵禽。《风俗通义,礼典》云:“鸡主以御死避恶。”魏晋时有“门户用鸡”之俗,人们把鸡刻画于门户之上《北齐书·魏收传》引南朝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正旦画鸡于门。”《拾遗记》还道出其风俗来源于一种叫“重明鸟”的神禽:“尧在位七十年,有掋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又眼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贻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其遗像也。”由此可见,碑上刻雄鸡之形亦是当时民俗之反映。图工中⑩为鹳鸟、雄鸡形象的组合。这种图像在陕西宜君县西魏福地石窟中也曾出现过,李淞先生认为其与关中地区农村的文化习俗有关。他说:“中国古字有声同皆相假借的普遍现象,这一点在关中至陕北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汉代画像石中‘鹿代表‘禄,这种习俗至今尚存,这几个动物图像皆是以谐音的意义出现的:大鸡即‘大吉、鹳雀即‘官爵。”宜君与耀县地理位置所去不远,民俗相近,此碑中的鸡鸟的图案应也与民俗有关,而且这也正符合吴洪标家族为中下层官吏的背景。另外,众鸟图案的出现同样是一种表现仙境的象征。在我国传统的宗教艺术中,仙境的图像总是与众多的飞鸟相联系着①。
图工中⑩至⑩是鹿和豹,前人所述均称此图为“虎逐鹿”。但图⑩所表现的兽,身体矫健瘦长,与虎的体形并不相应,反而与豹相类,应是一种与豹相似的神兽。《述异记》载:“炎州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万里。上有风生兽,似豹,青色,大如狸。张网取之,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兽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砍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铁锤锻其头数十下乃死;而张口向风,须臾复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脑,和菊花服之,尽十斤,得寿五百年。”在葛洪的《抱朴子·仙药》中也提及此兽,不但是不死的神兽,还是长寿仙药,而鹿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瑞兽,其图像无论是在佛教艺术还是道教艺术中都随处可见。在这里之所以出现鹿的图像,笔者认为其有三层含义;一是鹿乃长寿之兽。《抱朴子·玉策》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述异记》亦云:“余干县有白鹿,土人传千年矣,晋武帝遣捕得,有铜牌在角后,书云:‘汉元鼎二年临江所献白鹿。”其次,鹿乃升仙之物,有乐府
诗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鹿还被道教认为是“三矫”之一。这里所指的“三矫”,一日龙矫,二日虎矫,三日鹿矫。道教的三矫主要是作为上天入地的乘骑工具。第三,鹿音同于“禄”,取其谐音用于代表俸禄。
图1跑得中⑥在图案左上方,两人相向而立,四手相握。此图像不见于其他造像碑,在早期的宗教艺术中是一种很少见的图像。联系图⑥—⑩中的众鸟衔草的图像,此处图像应是古代神话中所提及的“蒙双民”。《博物志》卷2云:“昔者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在此处刻“蒙双民”用来作为不死神草药效的范例,反映了造碑者希望长生不死的愿望,最上部的图(18)残缺,但能看出是一人骑马。此处出现骑马像绝非造像碑中一般的骑马供养人像,也应该是仙界之物。《神异经·西北荒经》载:“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人遇其乘车,抓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物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此像可能就是仙界中能作仙药的骑马小人。
最后,图1⑩为一屋,屋内一物似鸡状,不甚清楚,因不能详察其形,此处仅作猜测之说,《神异经,东荒经》云:“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关中地区自古以来也有石鸡传说,《艺文类聚》卷91引《辛氏三秦记》曰:“陈苍山在太白之西,上有石鸡与山鸡。赵时差使烧山,山鸡飞去,石鸡不去,晨鸣山头,声闻三十里,或云是玉鸡。”此图中屋内的图像可能为传说中司晨之石鸡。

通过以上对吴洪标碑碑额等图像进行的考释来看,图像之间虽没有明显的关联,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图像想要表达的思想是统一的,而且是清楚的。造碑者通过刻画这些传说中仙境里的长寿之物和不死仙药,来表达希望能长生不死的愿望,正如其发愿文所说的“因缘眷属,崇山福德,舍身寿身,值仙闻法”。长生不死的观念是道教的核心思想之一,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道教的养生术、炼丹术、医药学作为其追求长生不死的手段都很发达,那些道士们服饵炼丹,都希望能得到不死仙药,此碑中所表现的长生不死的观念正是当时道教艺术所经常表现的主题之一。
关中地区造像碑的道教图像中除了表现“长生不死”的主题之外,“升仙”的主题同样表现得十分强烈。道教追求不死升仙,当时人们不但希望能够在人间长生不死,更希望自己能够直接升临仙界做神仙,正如辛延智造像碑的发愿文所说的“重利群生,教于仙药,精成则白日升天”。这种“升仙”的思想表现在艺术图像上就是对一些仙山、天宫等仙境图像的刻画。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北魏熙平二年(517)造像碑,碑阳龛楣上就被雕刻成天宫的形象,李淞先生对其这样描述:“龛楣为屋顶形,左右各一根高大的立柱,以示天宫。屋檐上正中有一仙人骑瑞羊,羊口出瑞气。左右角则又各有一瑞兽,龛外侧又有一小屋,内悬盘与钟。”对于“仙人骑瑞羊”,李淞先生却并未作出解释,而考诸当时传说中的神仙,骑羊者非葛由莫属。《搜神记》卷1有云:“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人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后世亦有诗赞曰:“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此处“仙人骑瑞羊”指的就是蜀地仙人葛由,造碑者希望传说中引领人们进入仙界的仙人葛由也能够引领自己升入仙界,此处葛由的像刻于天宫之上并不意味着其凌驾于天宫之上,由于造像碑图像的平面表现形式,应是指葛由骑羊到达天宫门口的意思。而在关中地区出现蜀地流传的神仙形象,也恰恰反映了关陇地区的道教信徒源于汉中的历史背景。除了天宫图像之外,有的造像碑还刻画仙山纹和仙草纹来装饰造像碑(图4)。仙山形象在早期的宗教艺术中非常多,道教素有灵山崇拜,昆仑、蓬莱、方丈、瀛洲等都是道教徒所向往的神山,在他们想象中这些洞天福地布满奇花异草。
关中地区造像碑中的道教图像反映的主要是道教“不死成仙”的思想主题,而且图像众多,布局精美,富有浪漫主义气息。但是纵览这一时期的道教造像碑的图像,我们会发现这些内容丰富、画面精美的图像都是出现在公元500年之后的,之前的碑,画面质朴,雕刻也较为简单,仅有老君、侍者和供养人像。而此后,道教造像碑的图像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大量奇禽异兽、双龙、日月传统宗教艺术的图像加入,构图也较之以前精美许多。关中地区造像碑上道教图像风格之所以会发生突然的转变,笔者认为与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道教思想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的。
魏晋之际,以终南山为中心的楼观道派在关中地区日益活跃,楼观道强调“返本归真”,以《老子》为根本经典,主张以性命清修为主。至北魏时,受到寇谦之改建天师道的影响,成为较成熟的道派,其教团组织在统治阶级及民间都有较大的影响,而崇奉大道、神化老子本来就是天师道区别于其他各种原始巫教的主要特征,陆静修《道门科略》说:“天师道‘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天师道的这一传统在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后仍然保留,北朝新天师道及后来的楼观道派都将太上老君奉为教主。而且,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反对滥传服食仙方,强调要以斋功为养生求仙之本,重视奉守道诫、斋醮礼拜等宗教实践活动。所以,早期的造像碑图像,除了供奉老君和侍者的像之外,并未见其他传说中的神仙怪兽、仙药仙草,姚伯多造像碑中发愿文:“当今世道教纷,群惑兹甚,假道乱真,群聚为媚,大道之(?)要清虚,唯真素为洁,练身克修,大道之本。”可见当时关中地区的道教徒唯奉老子之大道,以斋功练形为养生之本,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早期的道教造像碑造型朴实,返璞归真,唯奉老君,并无其他图像。
到了北魏后期,关中地区楼观派道教的发展,在教义上颇受南方上清派的影响,江南道士所奉持的三洞经戒法篆,主要通过当时隐居在华山的一些道士之手传至楼观,华山乃是北朝道教重镇,楼观道士陈宝炽、侯楷等所修持的三洞经戒法篆,即得自华山道士陆景。而南方的道教上清派与天师道不同,一方面崇奉许多古代传说修道成仙的神仙真人,同时又创造了很多神仙。上清派的重要传人陶弘景网罗众神、排定位次,撰写《真灵位业图》,对道教神仙信仰体系进行了构建,把传说中的神仙世界全部吸纳进来。同时,上清派重视炼形、服饵炼丹等神仙方术,注意医药学,陶弘景还撰写过《本草集注》,上清派的教法北魏晚期在关中流行起来,从关中地区的造像碑上来看应在公元500年前后,北魏正始二年(505)冯神育造像碑即出现了“三洞法师”的称呼,这正是受上清派的影响。由于上清派吸收了很多早期的神仙世界的传说,受其教义的影响,在造像碑中才出现了大量的仙人异兽、奇花异草的神仙世界,图像风格趋于华美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正是由于南方上清派道教对关中地区的影响,才引起了造像碑上道教图像的风格转变。
关中地区的道教和佛道混合造像碑,整体数量并不多,但是对这一地区造像碑的整体风格的影响却很大,不同于其他地区造像碑域外风格那么明显。关中地区造像碑从一开始就与我国传统宗教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特征。李静杰在《佛教造像碑的分期与分区》一文中总结关中地区造像碑的风格特点时说:“碑时常在主龛两侧刻二圆轮,内刻金乌、蟾蜍以象征日月。圆拱龛龛楣饰二蟠龙的做法基本见于这一地区,蟠龙之上饰二飞鸟更为独特。线刻或减地平雕乘骑、骑马供养人和牛车的形式最早出现并流行于这一地区。”这些风格特征的形成与这一地区道教艺术的流行是分不开的,道教艺术与我国传统艺术紧密联系并将此影响扩展到整个地区的造像碑艺术中,这也是这一地区造像碑风格独特的重要原因之一。
附注:本文得到业师吕建福先生和周伟洲先生的指正,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