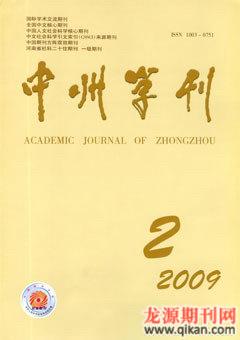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胡玉洁
摘要: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方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215-03
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极为灵动的曼妙气质。无论是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还是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体现了毕飞字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特性。
一、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方式
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正面强攻式的紧张状态。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叙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曼丽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逻辑思维中,迅速传达作品内在的审美意旨。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
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马家父子》等作品的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的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深远的思索,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例如,《怀念妹妹小青》看似在着力于叙述妹妹小青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是主人公那充满悲剧性的几个重大人生转折,却明确地凸现出历史深处的残酷、悲壮和劫难。而这种历史的不幸正是毕飞宇的审美目的,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少女妹妹只不过是作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命符号。《哺乳期的女人》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这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作家自始至终都不点破这种朦胧境界,而是以一种心灵叙事的方式,缓缓地打开男孩的内心,又以少妇特有的温情,缓缓地收拢一切。《男人还剩下什么》似乎在讲叙一个有关婚姻解体的故事。但是婚姻解体之后,前妻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复仇欲望,它直指人性深处,呈现出某种非理性的可怕的癫狂状态。《地球上的王家庄》是一篇极为精美的短篇。它生动地展示了人与世界、苦难与诗意的巧妙对接。8岁的“我”由一册《世界地图》开始,便常常衍生出各种有关“世界大小”的想象。于是,他便从现实中的王家庄出发,在一种无法遏止的狂想中,赶着一大群鸭子,沿着乌金荡顺流而下,试图探求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真相。与此同时,被“文革”剥夺了教鞭的父亲,则在沉默的体力劳作中不断地保持着对天空的遐想——那是一种灵魂在暗夜中的飞翔,是生命挣脱苦难命运和悲剧现实的奇特方式,是在没有诗意的生存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反抗行为,而这种被常人视为“精神病”的行为,恰恰与少年“我”的梦想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振。因此,“我”的冒险行为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对父亲自由灵魂的一次盲动的实践。
长篇小说《平原》无疑是毕飞宇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以1976年作为历史的横断面,全面展示了以端方为首的乡村青年寻找自己的人生,并由此在狭小的王家庄里演绎了一场场有关人性与历史、理想与现实、尊严与地位相抗争的惨烈悲剧。其中既有狂欢性的民间生活气息,又承袭了意识形态的蒙昧化情境。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爱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却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它既遵循了整体性的历史常识,又对常识中的某些幽暗区域进行了必要的扩张。这种对轻与重的精妙处理,使毕飞宇成功地逃离了“意义”对话语的强制性压迫,从而让叙事获得了举重若轻、灵性曼舞的艺术效果。
这种效果的获得,还取决于毕飞宇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无论冲突何等剧烈,主题何等尖锐,一旦话语进入人物的内心,便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节奏。如《五月的九日和十日》中,面对妻子的前夫突然光临,情感危机似乎一触即发,但作家却让人物彼此间不断抵牾,可就是引而不发。《玉米》中的少女玉米,无论是面对父亲的情人还是命运的巨变,都保持着一种内心特有的对抗方式,既不剧烈爆发,但也决不屈服。作者的叙事,始终沿着这种临界状态缓缓推进。《水晶烟缸》、《青衣》等作品也都是如此。《唱西皮二簧的一朵》中的一朵成功地利用了一个纯情男子的力量实现了自己近乎疯狂的目的,却被另一个情场老手不露声色地颠覆了。这种叙事策略,使得毕飞宇的小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节奏,所有的波澜都潜藏在内部。
二、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视角
1、变化和流动的视角
毕飞宇的小说常常采取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来表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这种变化和流动的叙事视角主要体现在: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运用;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叙述自我”视角与“经验自我”视角的交替变化;第三人称叙事作品中的视角偏离和流动。在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控制中,凸显出毕飞宇明晰的视角意识和毕飞宇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叙述人称置换的艺术技巧带来叙事态度、叙事情感的变化,造成了文本阅读的亲切感,又使意味深长的语言包含了内在的叙述张力。
毕飞宇小说中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与人们常常谈到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是不同的。它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平均后的变体。在小说叙事效果上,这种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可以在表层的富有“距离感”、“客观性”的第三人称视角叙事中增加具有“亲切感”、“主观牲”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从而丰富文本的内涵、增强小说叙事的表现力。下面以《玉米》中王连方被开除以后玉米一家人的表现为例略作分析。小说首先从施桂芳写起,施桂芳“从头到尾对王连方的事都没有说过什么。施桂芳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不停地打嗝”。这就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出发,客观地、富有距离感地道出了施桂芳的无奈。接下来“作为一个女人,施桂芳这一回丢了两层的脸面”的描述却自然微妙地让读者感受到这里仿佛有一个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面对施桂芳“她”不由自主地发出内心的感慨:“作为一个女人,施桂芳(你)这一回丢了两层的脸面(呀)!”文本的叙事视角在这里就由第三人称叙事视
角不知不觉地转化为毕飞宇小说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这种转化使得作者与读者双方经由对“施桂芳”的怜悯同情而达成了一份默契,开始了一种情感的沟通和交流。接着叙述者再回到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继续写施桂芳,“她睡了好几天,起床之后人都散了”,“这一回的散和刚刚出了月子的那种散到底不同……只不过吃力得很,勉强得很”。此时的叙事视角就又由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变化为“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了。在这种转化中,叙述者不仅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施桂芳崩溃的精神状态,帮助读者清晰而准确地把握小说人物的内涵,而且逐渐拉近了读者、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读者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一个隐藏的“我”正逐渐靠近“她”,“我”和“她”的相对距离渐渐缩小,“我”禁不住流露出对施桂芳“她”的感情倾向和评价。
除了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之外,毕飞宇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叙述自我”视角与“经验自我”视角呈变化、流动状态。“叙述自我”视角是“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它是“叙述者从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的视角,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常规视角”。“经验自我”视角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它“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这种模式一般能让读者直接接触人物的想法”。这两种叙事视角在文本中的变化、流动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和认识,形成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的对比态势,从而使得文本富有一种层次的叙事美感。除了上述两种叙事策略外,毕飞宇小说还常常采用视角的偏离和流动,特别是聚焦人物视角向旁观人物视角转移的视角策略。在毕飞宇小说中,叙述者在整体通观视角的统辖下,采取了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控制艺术。这些巧妙的视角策略不但丰富了毕飞宇的小说世界,也拓宽了读者看世界的眼光。
2、儿童视角与创伤记忆
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
在毕飞宇采用儿童视角的10篇小说中,读者都能从里面读出两个字:伤痛。特别是作者选取的儿童视角,从一个个孩童眼中看到的和心中感受到的伤痛更有一份揪心和动人的力量,更增添了文本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意蕴。《上海往事》从一个14岁男孩臭蛋的视角里凸现了小金宝(一个渴望爱情的风尘女子)的绝望与伤痛。《哺乳期的女人》中,7岁男孩旺旺流下的泪水映照出的却是一颗纯洁却无限伤痛的心灵。而在《那个男孩是我》、《怀念妹妹小青》、《写字》、《枸杞子》、《武松打虎》、《白夜》、《蛐蛐,蛐蛐》和《地球上的王家庄》这些小说中,叙述者从儿童视角切入,回溯了“文革”时期的一份份创伤记忆。它们共同揭示了“文革”中的野蛮、愚昧、残忍对一个个生命、一颗颗心灵的无尽戕害和肆意践踏,让原本天真纯真的儿童世界遭遇到无法理解也不能承受的疼痛与伤害。这份创伤记忆带给人们的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尽思索和深刻反省。《那个男孩是我》中,飘拂在“我”(一个生病的孩子)心里的栀子花香和悠扬哀怨的琴声在表姐痛快淋漓的欢笑声“他们完蛋啦,彻底完蛋啦!那个老太婆原来是个反革命”中悲惨地消解了。《怀念妹妹小青》中妹妹小青在“文革”时期无中生有的村庄械斗中丧生,“我”在恐怖至极的颤栗中留下深深的伤痛。《写字》里7岁儿童“我”的童年生活就全部结束在“永远是狐狸的逃逸姿势”的伤痛感觉中。
三、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结构
1、欧·亨利式结构形态
欧·亨利式的结构主要取决于故事结尾的出奇制胜,所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种“欧,亨利式的结尾”,并不只是强调一种故事表面的合理性突变,而是要凸现“突变”之中的丰厚内涵。毕飞宇的小说《平原》中,三丫在经受了妈妈的宗教感化之后,忽然有了“进入极乐世界”的强烈愿望,但是那个革命时代不承认这种宗教感化,它只认同发生事实的政治内蕴。因此,三丫命运的最后突转,看起来只是一种叙事层面上的意外,但在意料之外却又分明把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交织在一起,更为长篇小说的张力平添了无穷的内涵。
2、辛格式游离结构形态
辛格式的游离结构形态主要强调人物之间的游离和情节细微之处的盘旋,通过对叙事节奏强有力的控制,让冲突始终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并在往返与盘旋之中凸现人物内在的精神本质。在这种游离式的叙述法则中,鲜活地展现了人物内心深处异常隐秘的精神状态,凸现出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蕴。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看似漫不经心地写了一对都市边缘男女的情感际遇——偶然的相遇、做爱,然后彼此交流,似恋爱又不是恋爱,最后友好地分道扬镳。他们温暖着自己也温暖着对方,甚至有点相濡以沫的真诚,但他们却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那个沉重的“爱”字。是他们不想相爱?不,是不敢。世俗的欲望、生存的压力、不测的命运、无望的未来……这一切都不允许他们正常地相爱。他们以独特的生存方式呈现了都市普通人群在爱与欲之间的分裂,也表达了他们对这个物质时代近乎绝望的抗争。
3、卡尔维诺式寓言结构形态
卡尔维诺式寓言结构形态主要是通过一些异乎寻常的细节,使叙事脱离纯粹的写实层面,进入充分想象的空间。这种形态既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使叙事话语在剥离写实之后获得了诗性的气质,呈现出飞翔的状态,同时。以一些小小的人物或事件,将思考延伸到某些重大的命题之中。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派意味的创作形态。它融灵性、凝重、隐喻于一体,在一种广袤的想象地带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回味空间,同时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们的影子。姜广平认为,《蛐蛐,蛐蛐》这个短篇是毕飞宇“全部作品中提供阅读的可能性最多的也是最深邃的小说”,“蛐蛐”作为一个媒介象征着“文革”中的中国社会状态,体现出了汉语的表意功能。又如,2002年《上海文学》推出《地球上的王家庄》时,在“编者的话”中认为,这是“一篇带有寓言意味的小说,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封闭的厌恶以及对世界的向往”。而梁弓则认为,小说表达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即不要去做我们无法完成的事。柳润香指出,这篇小说通过对一个横断面的剖析,不仅展示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世界的人的内隐的对立,而且表现出对在这种对立中所建立的秩序和标准的质疑。
总之,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叙述者通过对叙事视角的有效控制和选择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个丰富的艺术世界,也在叙事视角与叙事效果间形成平衡协调、水乳交融的态势,展示了令人咀嚼和回味的悲天悯人的大家风范。其独具匠心的结构安排,体现了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揭示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责任编辑: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