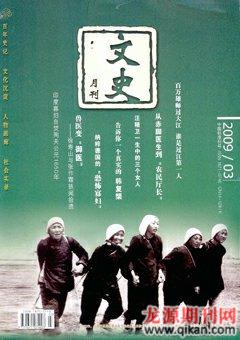历经沧桑话通讯
杨宇宁
我生长在距神池县城20多里的大山深处,那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上世纪50年代初,乡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相互传递口信,人称捎话。这怕是有人类以来传递信息最原始的方式。记得我入小学那年,进城办事的乡人捎回话来:“明天老师进村,请村里做好准备”。听说老师要来,自己可以上学了,真是高兴极了。我离村到县城上高小也是乡人捎的口信,这种以口语传递信息的方式,虽然原始,但它增多了乡人的往来,也增进了乡人的情感。
50年代中期,我家收到邮递员送来的第一封信,是解放前走西口到内蒙古的二伯父写来的。这封信从写到收共走了两个多月,父亲从信中得知离散多年的骨肉同胞还活在人世间,就是这封信才使我与口外的同族兄弟姐妹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上初中、高中及至上大学都是邮递员把通知书送到村里的,邮递员给村里送来福音,村人是很欢迎他们的,以致成为村人家里的座上宾。
我接到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正是中秋时节,我把邮递员张好杰请回家中,拿月饼和肉包子招待。那时的信件有平信和挂号信之分,挂号信丢失的可能性小,一般都要送到本人手里,我从初中到大学的通知书都是挂了号的信。那时除了信件传递信息外,还有电报,但价钱高,乡人没有什么太急的事,一般是不采用的。我二伯父病危,通知我父亲时,就是采取电报的方式,这是我家至今收到的唯一一封电报。
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栽电杆,架电线,由县城到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再到村里通了有线电话。这种电话有个摇把,手摇几下,公社机房接机,再按你的要求中转,有时一接就通,方便了村人;有时一个电话一天半天也接不通。尽管费时,它毕竟给乡人带来了方便,成为小山村具有现代气息的标志。
当时在电话线上再接一根铁丝安上了喇叭,这种喇叭装在一木匣子里,挂在墙上,人称“洋戏匣子”。那时公社开会什么的一般是通过这种匣子来通知各村的干部。
夏日夜里,村人聚集其下,听着匣子里播出的神池道情那种惬意的神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后来我家也安了这种匣子,因此,我家也就成为乡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
记得我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劳作,夜里匣子里传来让我到公社学区报到,参加民办教师培训的通知,从此,我就“参加了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些大村子装上了高音喇叭,这家伙真的声音很高,毗邻我村的朔县上圪佬村的高音喇叭响起,我村也可听到。每当村人谈论起高音喇叭时,村人总认为那家伙在我们那样的小村用处不大。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办公室用的是拨号电话。这种电话面上有个圆盘,盘上有十个圆孔,十个孔相对应的是从0到9十个数,按号拨数,拨一个放开,圆盘复原后再拨。要拨个七、八位的数,没一分半分钟是不行的。
尽管费时,但要比手摇式电话先进多了,然跨省、跨县仍需中转交换。我当时在忻县地委宣传部工作,记得通知各县参加“真理标准”讨论会,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将所辖的14个县通知完。当时部里的那伙年轻人不怕写材料,就怕揽上打电话的差事。
上世纪80代末,办公桌上的电话换成了数字电话,这种电话不摇不拨,而是按,省却了中转交换,功能很多,可以随心所欲地直拨,这种电话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后来,我家里也安了这样的电话,有个什么事,按按即可。我就是从这种电话在家里第一时间得到女儿被太谷交校录取的信息。这种电话好是好,但需老守着它,如离开它,接打无人,也就暴露出它不能移动的弊端来。
后来,为了方便,随身携带了BP机,亦称传呼机。这家伙会随时得到有人呼叫自己的信息,当得到呼叫信息后,立即就近找部电话回过去,双方及时交流,迅速地把事儿办了。一年,家父急病,妻子很着急,打传呼告我,我又用传呼手段呼叫在市医院工作的朋友,使老父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这种工具弥补了固定电话不能移的不足,然而也存在不能及时找到电话的尴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人将传呼机弃之不用,换之而来的是大哥大,这东西既可随身携带,又可直接通话,可价钱上万元,我当时那几个小钱是买不起的,但我确实沾过它的光。我和朋友外出,车子被搁浅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路,眼看就要夜宿荒野,挨饿受冻,心中不禁犯起了惆怅。谁知朋友从包中掏出大哥大,向另一朋友求援,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连夜修好车,安全回家,从这以后,我由衷地感谢那个大家伙。
时间推移到21世纪,我的传呼机也下了岗,女儿用她参加工作的第一笔钱为我买了部小巧的手机,这个小玩艺儿真怪,既可接打通话,又可收发短信;既可设置闹钟,又可记事照相……手机的使用极大地便捷了我的生活。随后妻子配备了小灵通,有个什么事,随时可与妻子通话,如今妻子也换成了手机,有事互发个短信即可。
几年后,家中添置了台电脑,妻子又上了什么宽带,电脑这东西作用太大了,它帮我及时了解国内外的信息,帮我查阅重要资料,可以说它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好伙伴。侄女高考成功的第一消息就是从电脑上得知的,我向全国媒体提供的文稿,也是由电脑发出的,我写作、和朋友交换意见,谈吐心声有时也是通过电脑进行的。电脑真的帮了我不少忙,我打心里感谢它。
50年的时光,50年的沧桑,真正使我成为了“千里眼,顺风耳”。
(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