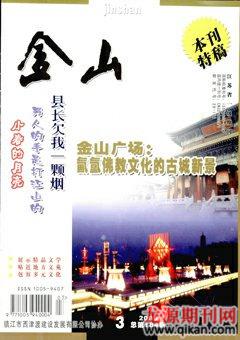没有敲门声的夜晚
吕志勇
李厅长办公室的门铃安装在边框上,不熟悉的人不容易发现的。
因此,敲他办公室门的,总是陌生人。
最近省里的高速公路开始招标,他忙得很。敲门声此起彼伏,有时急如战鼓,有时悄若蚊嗡,有时零落琐碎,有时又热情张扬……但他一一作答:公开公平公正,谁都有机会。
尽管解释得如此详细认真,敲门声还是不断。毕竟,他是总指挥长。谁都以为他可以左右形势的。
没人的时候,李厅长盯着门就发呆。前几任,都进去了。
他和秘书说,把好一扇门不容易啊。他指指门,又指了指办公桌。秘书笑,李厅长的门,静音的。他也笑。
还好,一下班,可以到公园里当个票友;可以散漫地牵着老伴的手,到处走走;可以推着苗儿四处看看。
几十个亿的工程啊!他心里老是沉甸甸的。路旁的草坪里,荒草也在狠狠地吸收营养疯长。他蹲下去,薅了几把荒草。
要不是苗儿腿脚不好,老伴也不会信佛的。作为父亲,他欣慰的是,苗儿好在还快乐,心里没有阴影。可,以后呢?自己总要老的呀。
晚上,不息的敲门声扰乱他的思绪。他告诉吴妈,生人一律不开门。
一天,两天,三天……敲门声少了。
晚上,他反而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就问吴妈:“去看看,是不是又敲门了?”吴妈说,没有吧。我怎么没有听到呢?
“生人千万别开。”熟人也没有,吴妈遗憾地摊摊手。
没有敲门声正好睡个安生觉。可,睡眠,像汹涌的洪水奔袭过来,冲击着李厅长,很长时间才能入睡。
有时候正吃饭哩,他忽然说:“吴妈,看看谁敲门。”吴妈只好望望他,望望苗儿,望望他老伴,然后去门边看看,遗憾地摊摊手。
这天,他到监狱里看了看前任厅长,原先的老伙计,憔悴焦虑声泪俱下,感染得他也唏嘘了好久好久,擦了很久的汗——监狱里好像连风也封闭了。
这天,正在吃饭,吴妈忽然说:“又敲门!真不让人安生。”李厅长惊讶,我怎么没有听见?难道耳背了?!
转天,吴妈又说:“又是谁?敲门真不让人安生。”他没听见。想,真的耳背了。
吴妈总是听到敲门声。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一上班就让司机陪着上了几次医院,反复检查,耳朵没有一点问题。但他还是不放心,怕老伴知道,家里有个残疾的女儿,已经够拖累她了。
老伴诵经的声音从里屋传来:多行善,不作恶,全家人人都平安……
招标最后的结果终于定下了,李厅长抽着烟端着茶找秘书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晚上正在看书,吴妈又说:“又敲门!真不让人安生。”李厅长忽然说:“开门,迎客!”神情坦然镇定,指向门的手指像将军的宝剑,寒气凛然。
吴妈的颜色蜡黄,哆哆嗦嗦起来,他催促地看着吴妈。门开了,空荡荡了无一人。他惊讶地看着吴妈。内心里一阵寒栗:防不胜防啊。
他问吴妈,说:“你当保姆多少年了,难道不知道我的脾气?还有人敢收买你?”
吴妈尴尬地站在客厅里,不停地在围裙上摩挲着手掌。
老伴从里屋走出来,笑着说:“老李呀,是我收买的。你说说,这关键时刻,不演场戏让你有点牵挂和担心,我一个人能劝住你嘛!”
无敲门声的夜晚,李厅长梦中又回到了农村老家的柳树下,又闻见了大学宿舍里同学的脚汗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