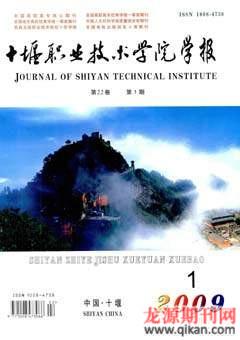“十七年”农村小说书写中的“历史疏离”态度研究
[摘 要]“十七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时代,表现出了相当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对于这一时代而言,它与过去的关系不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而是一种彻底决裂的关系。“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呈现出的历史态度无疑是对时代氛围的反映,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并不能与传统完全分道扬镳。在这里,我将抽取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一问题:一是农民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土地)无疑是最能反映农民本源的东西;二是乡村传统道德模式的变化,基于个体的道德标准到基于集体的道德标准的转化过程使我们有可能窥见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十七年;农村小说;历史疏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09)01-0069-05
[收稿日期]2008-11-25
[作者简介]吴玉玉(1982-),女,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引言
在“十七年”时期,历史之于人们往往不是所珍爱的对象,反而是急于疏远和摆脱的对象。由孝到忠的传统观念转变,实际上表现出的正是对历史的一种挣脱。历史在此遭致的疏离,相当于对个人情感的某种遏抑,其实是在为集体主义观念的输入创造便利的条件。“古代农业社会是建立在道地的传统主义上的,在这种社会中,只有那些长期延续的事物才最有存在的理由。”[1]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唯物史观强调的是“螺旋式上升”,“螺旋”意味着旧之阻力存在的现实状态;“上升”则意味着新事物到来的必然性——无论是“十七年”农村小说中所透露出的农民与自然关系的嬗变,还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乡村道德体系以及标准的转化,都体现出了这种前进方向单一却矛盾而复杂的态势,可以这样说:“革命是一段资源丰富、头绪复杂的历史,而革命却不赞成那种过于复杂的历史叙事。”[2]激进的历史观所带来的是一种除旧布新的态势,上一代的观念无论曾经怎样辉煌,在面对新的技术或思想之时,就不免露出可笑之处了。从家庭内部的主宰来看,也早已不复是当初的老一辈了。在这里,经验被一定程度地扭曲,它代表的时间印记被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所代替。
二、农民与土地——从依靠到征服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将目光集中于乡村的落后和愚昧上,将乡村作为谴责的对象加以描绘。乡村背后的巨大保守势力成为渗透一切的因素,人在乡村中处于被包裹的地位。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涌现出了两种不同风格的乡土小说:一种是以沈从文、废名的创作为代表的充满浪漫气息的乡土小说;另一种则是隶属于左翼作家群创作风格范畴内的现实意味较浓的乡土小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一方面,从前者那里来看,人与自然之间表现出了一种和谐的态势。双方互为对方生存的要素,自然被人化的同时,人也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举例来说,《边城》中个体的生死爱欲与自然风物是同一化的,“虎耳草”(翠翠爱情萌芽的标志)等意象的出现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从后者那里来看,乡村的气质逐渐由静谧向激烈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主、客体位置开始发生转移。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大多数的作品都有着矛盾的阐释基调:景物描写所蕴含的主体感情是正面的;同时,自然作为人类的改造对象被客体化,承受着放逐自我的命运。这种阐释基调可以被视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农村小说无疑承袭了左翼作家群乡土小说的某些风格,却又对其有所延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直接导向了“十七年”农村小说主体风格的形成。随着社会条件、时代氛围的变迁,“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乡村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集体规划和派定的劳动取代了个体劳动,个体农民不再固定地在一块土地上劳动,于是他们与土地之间由熟悉而产生的感情因素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外,占据主导地位的由自然的力量变为了人的力量,即集体的力量。集体代替自然成为了新的依靠,个体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批评的语气,并将最终获得改造和归队。客体化的结果使自然变得软弱无力,自然被完全忽视,只能作为期待占有的对象。集体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服从性和纪律性。追问的权利被剥夺,个人所做的一切在于结果的达成,原因则成为了秘而不宣的被集体隐匿之物。所有个人的行为都导向一个相同的结果,于是他们的单独作用力并未受到重视。在结果的显现之下,原因的忽略成为了纪律和服从的保证。集体以其绝对的精神感召力消弭了差别,相同的信仰必然指向相同的追求——这一推论成为了写作之中的隐含线索。
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20世纪30~40年代乡土小说→“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品中农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们由悲哀的、充满伤痛的个体转变为朝气蓬勃的一群,继而又裂变为了充满战天斗地意识的一群。“十七年”农村小说无疑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调,这“既与中国人一向缺少根深蒂固的悲剧观有关,也与当时的现实情状有关:中国终于结束了被他人蹂躏的耻辱,也结束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内战而带来的混乱。它空前地向人们显示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3]精神状态的千篇一律构成了这一时期农村小说集体形态的内在指标。在面对困难时,犹疑和彷徨几乎是非法的,因为集体早已被笼罩在昂扬的氛围中。
王汶石的《严重的时刻》反映了大跃进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干旱、冰雹等天灾所引发的沮丧情绪,作者暗指了它的危险性。“严重的时刻”不仅指物质层面的损失,更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涣散,这意味着集体赖以形成的精神根基有着动摇的危险。在这时,陆蛟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各方面,从各个角落,把晦气冲开,把畏惧心理打掉,把悲观情绪扫出去”[4]283,之后的生产任务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一大二公,力大无穷”[4]287和“人定胜天,公社胜天”[4]290信念的支撑下,人们的乐观是没有边界的——因为责任被平均化了。喜气洋洋的结尾反映的仍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在浩然的《泉水清清》中,刘炳志寻找水源的行为一方面以人力破坏了自然的神秘性,一方面又被作者赋予了一种政治性,这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被纳入到了政治的范畴中:“喊声滚动在这个神秘的山洞里,开天辟地以来,这里第一次响起人类的声音,这第一声,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喊出来的!”[5]
在沙汀的《你追我赶》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甚至超越了主、客体之间的界线,而一跃成为了敌、我双方的斗争关系:
“……龙唯灵……用洪亮的嗓音不断同干部们谈着下一段的工作计划,满口兵家术语:‘据点、‘战线、‘集中火力等等。他没有打过仗,但他懂得,他们是在同大自然作斗争。
自从大跃进以来,实际所有农村干部,几乎都是这样谈庄稼生产的。”[6]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年”农村小说中人类能够成功征服的自然领域是无所不在的,它不仅包含自然的物质层面含义,还包含有自然的抽象层面含义——“时间”便是一个很重要的考察维度。农业的合作化进程本身就是重视速度的产物,这将导致精神对现实的驾驭,因为前者的生发更具备一种摆脱羁绊的特征。在快速变动所带来的震荡中,个体的精神始终处于躁动之中,这必将导致一向以保守为特征的农村除了激奋之外还体味到一种不安的情愫,秦兆阳在他的《在田野上,前进!》中将创造性简单地归结为与时间的竞赛、与不可能的斗争:“要争取时间,争取快。争取——这个字眼太好了!我们今天的一切不都是争取得来的吗?……一个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办法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不可能就会变成了可能。这就叫争取,这就叫创造性,这是最了不起的东西!”[7]这实际上是将创造的主体与所依靠的客观条件完全割裂开来。保守是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速度感的丧失,阻碍了未来的来临。首先,时间成为了束缚人的、与人相对立的事物。在集体所制造的伟大人类的构图中,时间由一种本有之物变为了一种有待于生产之物,这也就是说,它不再是被给予的,而是由使用者自行产出的。通过提高速度、缩减睡眠确实能够使人在单位时间的劳绩增多,但这只不过是将生命时间提前预支——短暂的亢奋之后即将有深深的疲惫到来。由于作品中对前一阶段进行了过量的描写,同时却又对后一阶段只字不提,所以文本表现的是一种断裂的现实。其次,由不可能到可能之间的关键被简化了,人不再试图向自然表达自我的心情,而是开始片面地理解自然。人们在“劳动万能”的心态下不再视收获为一种礼物,而是将它看作斗争的成果。
“一件物质客体,一旦服务于一种用途,或从属于一处背景,就被裹上了一层形式的外衣,对我们掩藏起了它的赤裸形骸。”[8]在“十七年”的农村小说中,土地的自然属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掩盖了。一方面,作者表达了对于土地的喜爱之情,作品中人物的活动范围和全部生命价值都存在于土地的基础上,以此为评价标准的人物性质显现于文中。这种评价虽然依从于农民传统的实用理性原则,却又被置于政治的框架中(农业合作社)。另一方面,土地不仅仅是被赞美和倚靠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了可征服的对象,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土地之所以获得赞美是因为它拥有可以被改造的特征,即,它的人工性是它存在的最大价值。在此,人的原则代替了自然的原则,农民在某种力量的支持下可以创造出自然的原则,这本质上是一种控制论的思想,它来源于机器工业文明所占据的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在小说中虽然并未获得被直接书写的机会,却以另一种方式渗入乡村之中,使乡村变成了混合气质的独特景观。耕作于土地之上的机械(拖拉机)不仅不会破坏土地,反而会发掘出它新的生命,它们之间的层次等级应该说是比较明晰的了。对于土地的态度反映了个体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变,由个体联合所组织起来的集体生产单位的确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不可能再对自然持以往的敬畏态度,置身于集体中的个体会希望借助他人的力量去追逐悬念色彩浓厚的未来。
三、历史新景观的形成——农民精神状态和道德模式的转变
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笔下,“集体”的形成纵然与地理位置有关,但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更重要的判断标准在于生产资料占有程度所决定的阶级划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思想一致性。农民由土改时革命的主力到后来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人民公社运动的革命对象,他们所经历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状态的嬗变,更是精神世界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将社会主义变成为农民自身的内在要求”[9]。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对农民由外→内的植入过程中,它也开始由一种外界的规定转变为了被追求的对象。农民新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品质的浮现成为了他们与自我过往告别的依据之一,而这也恰恰是国家所倡导的“翻天覆地”式的农村改变格局的图景折射表现。文学作品开始描画一种新的历史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新”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而出现,却又往往被融合入“除旧”的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对峙是明确的,却又不能被截然分裂开来。
梁漱溟认为,“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道德问题。”[10]在传统的乡村道德体系中,富人承载着一定的道德期待,社会主义时代条件下这一道德体系被彻底颠覆了。在浩然的《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被作者描绘成了“魔鬼”一类的人物:“……马小辫……把自己打扮成‘慈悲圣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个地道的吃人魔王!”[11]这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利用和置换——“魔鬼”的虚幻性被一种实有性所代替,但它的邪恶和黑暗却是恒定的。另外,在此种意寓下,集体得以使“人”、“鬼”之分贯穿于其内部的评定标准中,同时也使调和这一举动变得没有意义了,永恒的矛盾必须以斗争来解决。这是将阶级与人性挂钩的一种巧妙的写作策略。同时无可否认的是,它也是一个时代对于”人”的普遍认知方式,不可能不在作家的心里投影。于是,在写作行为的内、外两重环境中,反面人物拥有了他们的固定命运,这与传统小说的“大团圆”结尾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更加重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教化功能。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既保留着乡土小说的地理风物特征,又从中分离出来,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政治的宣传工具。
道德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中被因果倒置了。本来应该是由道德去修补制度之弊,在这里制度却反过来成为了净化道德的过滤器,使好的、善的自然而然归并入集体;不好的、恶的被澄出来,接受众人的审视并选择改正或自我毁灭两条道路之一。然而,实际一点说,“人民公社的政治理想与农民缘于自身利益而生发的经济动机,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12]247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作家们笔下的正面人物形象往往会显得比较虚幻和刻意,并不具备人道主义的价值。浩然的《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杀死了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这一事件有助于使萧长春的集体主义情怀更加祛除私人性的情感,达到一种纯粹的境界。但他高大却虚伪的冷静使我们无法更进一步体味他在道德上的正面意义。
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中间人物身上。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中间人物为描写重心的小说叙事结构往往同人物的转变过程并行不悖,隶属于“改造故事”[13]的模式范畴之内,“暴露缺点→被教育→成为社会主义一员”的故事发展线索是极为普遍的。但差异并不是不会产生,它的位置往往在教育以及教育结果的阐释环节表现出来。有的作家会基于现实的考虑而避免直接给出具体结果,相反地,有的作家却会加强自己作品中教育手段的表现力度,从而使小说的结构趋向完整。总的来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历史断裂发生在文本之外,他们在文本中以较恒定的形象出现,于是我们的考察就必须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下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中间人物的被教育过程使他们的历史断裂发生在文本内部,这使文本呈现出了一种新旧交错的内在丰富形态。
西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些道德进化过程的不完善事例。《赖大嫂》中的赖大嫂的思想表现方式在前、后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姿态。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赖大嫂自私的心理活动被作者用直接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后半部分赖大嫂的转变却并没有获得直接的心理上的表露机会,仅仅通过一些间接的描写来预示人物的一种变化。但这取决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利益的一致层面,而非相悖层面,甚至可以说,集体对个体有一些妥协和迁就,于是赖大嫂的思想转变就不具备一种彻底性和稳固性。
陈残云的《前程》中,水满叔在集体的压力下,“自觉地觉得越来越不顺手,像有一股什么力量束缚着他,他想不通,却开始感到疲劳与孤单。”[14]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是大多数农民走向集体的原因之一,自我的责任承担与思考被集体以一种轻松的许诺卸下,个体开始放下一切现实的打算,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这也正是标题“前程”的寓意。将人性简单化→将人的转变过程快速化→将人的转变结果乐观化三个步骤的衔接是大多数“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叙事结构,在衔接之间担任触媒角色的往往都是党的“干部”或“工作员”。寄希望于由上而下的启蒙实际上反映了现实的苍白和无力,这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准则的作家创作行为内部的一种悖论。谷峪的《拖拉机》中,以老梗为代表的守旧、固执、自私的旧式农民形象是被改造的主要对象。他对于拖拉机的不信任反映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与机械工业文化之间的隔阂。在文中,老梗一度处于被孤立的地位,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使他与众人有了距离,他挣扎于一种自尊的矛盾之中。当他人与自己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自我就很容易动摇,并开始试图想象被关注的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向集体靠拢的心理。一旦认知自我的角度完全从他人的目光出发,距离也就消逝了,个体融入集体的过程便完成了。老梗由不信任拖拉机到让儿子小环去学开拖拉机,其中的转变是巨大的,尽管作者将其中的原因归于老梗的悔悟,但文末老梗的一句话才真正说明了缘由:“……我知道了,现在不信新事,才是顶受罪的人。”[15]“受罪”指向了一种集体给予的心理压力。集体施加的压力包括孤立状态带来的精神上的空虚,这往往会导致个人对自我立场的放弃。这不仅反映了个性在集体所塑造的生活环境中无以为继的现状,也反映了一种个人的彷徨心态。
马烽的《三年早知道》中,赵满囤是典型的个体农民,自私心理很重。从入社的动机、入社后的表现来看,他是很“公私分明”。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因此他的转变就不仅具有宣传意义,更具有预言的作用。由“人入社了心没入”到“人、心皆入社”,表明了集体要求深入个体内心、洞悉一切思想的意图。赵满囤改变后宛如另一位赵大叔,这说明集体对于个体的塑造有模式化、同一化的一面——这也正是这个短篇颇受好评的原因,正如王世德所说:“赵满囤的变化也说明了新的品德的养成是两种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的结果……他是整个向前行进的集体中的一个。”[16]将农村描画为道德乌托邦的企图使马烽的小说有着相对较强的教化色彩。书中普通农民的思想境界之高令人不禁有些半信半疑,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意义被无限扩大了,“农民的劳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净化,还是为了物质利益?”[12]137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农业集体化的秘密所在。在个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对应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它随时都与一个更庞大的群体挂钩——个人所创造出来的一切都不再属于自己所有,而是须得经过一个上交→再分配的过程。道德感召就在这里起到了强迫命令之外的润滑剂功效。
私有制的产生是由历史决定的,历史的惯性从一定意义上支持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以政治的规划来改变私有制的现实存在状态无疑反映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也不再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成了某种政治-道德的理想,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全面发展个性潜能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亦即‘政治觉悟高的圣贤。”[21]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阶段,对于个体的道德要求主要是从两方面提出的:其一是个体需要服从统一的号召;其二是个体要对集体作出奉献。“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对这两方面的处理亦是理想化的——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原因,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农村长期以来个体经营的现实与集体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之间必将产生历史惯性与现实状态层面的一系列矛盾。“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对此的表现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意味,然而他们那种普遍的对于小说叙事结构的完整性企图却使他们倾向于制造光明的结局,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意图制造现实在文学领域上的对应形式,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作者对于集体的乌托邦式的认知方式——个体内心与行动之间的和谐充满了集体内部的和谐。尽管仍有矛盾,但完全可以在道德的层面上加以克服,这是符合乡土中国的处事法则的,也使这种理想得以与现实更好地融合,产生出一种奇异的美感。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中写道:“在差序格局(指中国的社会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22]由此视之,作家们在小说中所透露出的对于传统人伦美德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尊老”的传统道德观之间结合的结果便是双方的共同妥协——激进的不顾一切的革命态度变为温情脉脉的劝说,顽固的守旧的保守立场也变为容易改造的柔软性质。集体的几乎无不成功的改造事例使“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线颇为晦暗不明的世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的历史条件下摒弃旧有社会基于年龄、物质因素而建立的“等级”后所制造出来的“平等”现实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被打倒的阶级使人与人之间的天平朝相反的方向倾斜,而不是平衡。土改→互助合作对于农民最大的诱惑在于个人利益的获得,从经济的层面来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是无法弥合的。于是政治的介入就显得尤为关键。在政治的支持下,个人权力与上级的关系变得愈加密不可分,服从和施压使大多数农民失去了话语权,令“平等”更加形同虚设。政治所赋予的权力意识代替了财富所赋予的优越心态,但结果却大同小异。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他们理想中的平等。于是在“平均化”的笼罩下,怨恨心理产生了。“四清”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是由上面发起的,但与农村中压抑着的一种破坏情绪是分不开的。革命带来的是权力的改弦更张,是循环的变易。“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更迭反映了秩序的不合法性,也说明了一切的道理只是相对而言,由立→破,再由破→立,循环的规律似乎在嘲笑着进化史观。[参考文献]
[1]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85.
[2]程光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05.
[3]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30.
[4]王汶石.风雪之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5]浩 然.彩霞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130.
[6]沙 汀.沙汀选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82-183.
[7]秦兆阳.在田野上,前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82-383.
[8]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1.
[9]李 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61.
[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88.
[11]浩 然.艳阳天: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706.
[12]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郭冰茹.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M].长沙:岳麓书社,2007:69.
[14]陈残云.陈残云自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341.
[15]谷 峪.新事新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23.
[16]马烽作品评论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67.
[2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87.
[2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28.
On Historical Concept of the Novels about Chinese Country World from 1949 to 1966
WU Yu-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The 17 years from 1949 to 1966 were a new beginning in history, which witnessed radical evolution in ideology. As a result, that period was not cherished but was discarded. The historical concept in the novels about Chinese country world from 1949 to 1966 was a kind of admixture of tradition and reality. Two aspects will explain this question: one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untrymen and nature, because nature (land) can reflect the countrymen's fountainhead; the other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ity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the 17 years from 1949 to 1966; novels about Chinese country world; historical Alie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