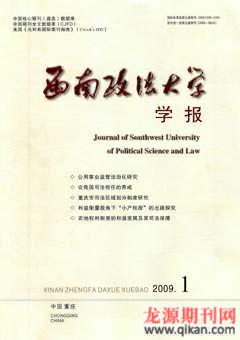美国环境规制与成本—收益分析
周 卫
摘要:基于对20世纪1970年代环境规制的高社会经济成本的反思,成本—收益分析在美国环境规制领域愈来愈受到重视。关注美国环境行政规制中的成本考量,有助于我们正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反思本国环境行政实践中的某些盲目和失误,可以避免因为不恰当的规制方式带来更加严重的环境损害后果。
关键词:成本—收益分析;环境行政;环境规制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一、美国环境规制的反思与成本—收益分析的兴起
自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颁布以来,美国控制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行政法规大量增加,公众环境权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过,这一划时代的“权利革命”虽然迎合了公众保护环境、控制污染的呼声,却没有考虑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在1970年以来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有毒物质控制法》等成文法所确认的严格环境标准下,企业即便添加新设备或停止生产,也难以实现法规所要求的“零污染排放”或“零风险目标”[1]。
环境规制的高成本问题很快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重视,尼克松总统因而在1971年实行生活质量评议计划,要求环保局制定法规必须听取其他有关机关的评论,并把评论的意见和法规草案送管理和预算局审查。之后,美国各任总统开始加强对法规实施的成本控制:从福特总统1974年的11827号令到卡特总统1978年的12044号命令,及至里根总统1981年的12291号令和1985年的12498号令,这种控制达到非常高的程度。根据12291号令,任何重大管理行动都要执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保证政府任何决策措施所产生的收益都要大于它所引起的费用[2]。该命令的发布使以前局限于部门和行业的成本—收益分析扩展到政府部门的决策,对非市场物品的价值评估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尤其集中在对环境影响的价值评估上。美国国家环保局因此制定了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手册,并且开始大量资助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3]。1993年克林顿总统以12866号及12875号令取代了上述里根总统的两个命令,强调规制措施只有通过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后才能被认可,并规定所有重大的规制行动都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小布什总统执政1年以后,2002年签发了13258号令,要求行政机关继续执行克林顿的12866号行政命令。
从里根总统到小布什总统时代,美国政府对成本—收益规制方法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政府应当尽量对自己试图解决的问题的规模进行量化,通过分析权衡规制措施的成本和收益,选择合适的规制工具,实现既有效又便宜的规制[4]。虽然这种共识并不限于环保领域的规制,但环保规制尽在其中。
二、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规制中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成本—收益分析的主张源自20世纪晚期美国总统加强对行政和规制监督的努力。由于时值美国规制泛滥,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规制过分和规制不足的问题同时并存,因此,谁来监管规制者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难题。里根总统的12291号令将行政法规的成本—收益审核权集中在管理预算局中的信息管理事务局(OBM),无疑有助于总统加强对规制部门的监督;当然,也有助于总统集中更多的行政权力。这种努力在克林顿总统的12866号令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不过,具体到环境规制领域,成本—收益分析体现出来的是对此前政府环境规制低效问题的反思,其作用表现为通过对环境规制效益的综合评估,促进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典型的例子如在成本—收益的衡量下,1996年《食品质量保护法》废除了早先著名的关于食品添加剂的零风险标准“迪兰尼条款”,代之以较低但更为可行的“合理的无伤害确定性”安全标准;同年修正的《安全饮用水法》则授权环保局在规制带来的收益不抵成本时有权对有关措施进行调整。对新近的一些重大环境规制法规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2000-2015年之间,美国在酸雨控制、冰箱节能标准、新的地表水处理方法、新型高速公路重型汽车排放标准、多氯化联二苯处理及微尘标准方面的规制,收益将超过成本,因而可能是有效的;然而,在为城市固体垃圾填埋地提供保险计划、纸浆及纸污染物指导方针、臭氧标准方面的规制收益则可能为0或负数,有待改善。这些衡量和比较,有助于引起政府对严重的环境问题的重视,促使规制部门采用更低的成本完成法定的环境规制目标[4]29-33。在孙斯坦等美国学者看来,成本—收益分析在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质量的立法和规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衡量市场效率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实证分析的市场基础,又有规范分析的价值取向,既可以解释现有政策的效率程度,又可以预测未来政策的走势[1]39。
三、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规制中引起的争议及其发展
(一)主要的质疑
尽管有关环境行政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要求在多个美国总统令中得到延续,但其实施过程中引发的质疑仍然相当多。这些质疑多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存在货币化难题。人们很难确定环境成本的量化标准,也无法确定更清洁的空气、更清洁的水、更安静的环境收益为几何。这通常是个变量,而且不同收入、地位的人群对洁净环境的偏好不同,赋值也就会产生差异。这对于环境执法的统一性要求无疑是一个障碍。
第二,对分配的忽略。成本—收益分析即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环境行政行为是否产生收益,是否值得实施,但无法确定成本和收益究竟由哪些人群分担,由此将引发对公平的怀疑。
第三,科学确定性的质疑。环境规制的目的多是为了消除或减少环境风险,但环境风险本身就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行政机关的判断往往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上,有时还会被媒体的言论牵引视线,这将导致对环境行政执法依据的怀疑。
第四,理论和实际不一致,当下和未来难结合。如一些环境规制的收益的实际情况和最初的预计相去甚远。一些研究表明,由于管制导致了降低污染控制成本的新技术产生,或者管制未能实现目标[5],不少污染控制管制措施的实际运行成本低于预计。
上述这些质疑都可能导致环境行政执法的正当性危机。此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作为政府决策工具使用,其本身还存在信息不足、操作费用高昂、技术面争议大、受政治过程干扰多、衡量价值单一等多种障碍[6],无怪乎1997年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公开的第一份规制成本—收益评估报告即引起巨大争议。
(二)对质疑的学理回应
经济学界对于上述质疑的回应,可以在1995年《环境、卫生和安全规制的效益费用分析——原则的陈述》这一由11位经济学家共同商议的报告中得见。该报告在充分考虑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环境、卫生和安全规制中应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意义、指导原则和改进意见。该报告指出,成本—收益分析对于环境、卫生和安全规制法规的制定极具意义,它有助于阐明公共政策决定的内在的权衡并使这种权衡更具透明性,也有助于政府机构建立规制的优先次序。该报告并没有盲目夸大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在环境、卫生和安全规制法规的制定中的作用,而是主张对该方法的应用有所限制,如限制在“重大规制决策”中应用,即规制的年经济费用逾期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此外,应从技术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解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不足,如分析重点的确定,成本和收益底线的确定,对替代方案的考虑,透明度和外部审查的约束,成本和收益数据依据和折现率幅度的限制等[7]。
法学界以波斯纳父子和孙斯坦为代表,也为成本—收益分析工具积极辩护。孙斯坦认为前述许多批评并不足以构成放弃成本—收益分析的理由。他指出,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处理量化问题时应当比较警觉;对于处理评价很难量化的变量,应当采取变通的方法;分配目标可以在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纳入考虑的范围;即使充分利用成本—收益分析不太可能,政府还是可以通过确定一系列的已知成本、已知效益以及事实上不确定的东西,朝充分利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向迈进。成本—收益分析为协助规范性选择的作出提供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分析工具,迫使人们更加集中、准确地考虑政策的潜在后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都不应当放弃[8]。
(三)实践中的发展
理论上的争议并没有导致环境行政执法实践中对成本—收益衡量方式的否定;相反,这是对它的完善。这表现在:
第一,对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变通。由于成本—收益分析存在货币化难题等不可克服的缺陷,美国环境行政执法还会借助“成本—效用分析”、“考虑成本因素”、“影响评价”等成本—收益衡量方式的变通方法。
其中,成本—效用分析是判断执行某一任务最有效方法的准则,无论采用何种决策规则,所选择的方法都应是最有效的,即实现项目目标的费用最省的方法[9]。当环境行政裁量中遇到某些效益无法进行定量分析时,或者环境目标已经由政府确认时(该目标未必具有经济学理由),成本—收益分析是主要的衡量方法。它能够寻找花费最小的方法来完成事先决定的政策目标。当选择了其他的政策而不是成本最小的政策的时候,成本—收益分析还可估计此时所需的额外的成本。不过,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无法解释实现决定的政策目标是否有效率[10]。 考虑成本因素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相比较,其共同的地方在于:都要求裁量者考虑行政行为的正面和负面效应,考虑行政活动的成本;其区别则在于:是否在制定规制政策中能将消费者的决定引入市场交易中[11]。考虑成本因素往往建立在直觉、经验、历史和习惯之上,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经济,但是也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主观专断。影响评价则是对政府干预的后果进行评估。
和考虑成本因素或成本—收益分析相比,影响评价不要求将结果货币化,也无须最优化结果。影响评价考虑的因素十分广泛。环境影响评价就是一种影响评价方式。但是,环境行政执法的影响评价并不限于环境影响评价,还广泛包括对项目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制度、人群分布等多方面影响的评价。
第二,通过制定法的规定实现成本—收益分析程序的法定化。最初,美国仅在个别法案中做出了成本—收益分析的规定。如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在第7章812款明确规定环保局应对法案自1970到1990年之间所发生的成本—收益进行综合分析,范围包括以往年度间的对比分析和对未来的预测。1995年以后,美国当局对于在规制中引入成本—收益程序表现出更大的热情,通过了为数不少的要求比较成本和收益的法案,如《联邦杀虫剂、除菌剂及灭鼠剂法》、《有毒物质管理法》、《饮用水安全法》等法律的修订案,同时对一些无效率、无效果的规章公之于众,如1997年美国环保局发布的关于臭氧层和微粒的“周边空气质量标准”。国会甚至考虑颁布一些能要求所有机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超级法案”,如1996年《非资助委任事务改革法》即从程序上要求政府对所有规制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不过,该法不具强制效力)。此外,管制对小企业、小实体的不利影响也备受关注,1996年国会颁布《小企业管制实施公平法》,规定法院有权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遵守了管制机动法,首次为小企业提供了强制性的救济程序;要求环保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召集小企业辩护审查团以确保从受影响的小实体中获得有关其繁重负担的真实性信息。
四、法院的态度:保持就事论事
也许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变化有关,美国法院对于环境规制的成本考量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如1980年“铅工业协会有限公司诉环保局”一案中,环保局在确定安全限度时并没有考虑可行性和成本问题,甚至连危害的证据也不清楚。法院认为,《清洁空气法》第109节禁止环保局在确定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时考虑成本;可行性和代价问题无关,环保局在确定安全限度上行为正当。在1987年“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诉美国环保局”一案中,环保局拒绝为氯乙烯设置一种“零排放”限制,尽管它承认这是能彻底避免接触这种明显的非界限性致癌物的惟一办法。地区法院巡回法庭驳回了这种解释,认为环保局应当根据《清洁空气法》第112节的规定把健康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12]。
然而,1991年在“防腐安装公司诉美国环保局”一案中,上诉法院对于成本考量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该案中,环保局试图对石棉进行规制。尽管环保局在规制前进行了成本—收益衡量,但法院认为环保局没有根据《有毒物质管理法》第6(a)条的规定,对所有可能的(包括最小负担和最大负担的)石棉规制替代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错误的,因而认定环保局的成本—收益衡量方法不合格而否决了环保局对石棉的禁止[11]679,681。1998年在“密西根州诉环保局”一案,法院对于成本考量的支持态度更为明朗。该案涉及到对于《清洁空气法》的条款的理解。根据法律规定,各州实施清洁控制规制的州执行计划,必须禁止本州内任何污染源或者其他形式的排放活动排放污染物,如果其排放量将会显著造成其他州不能达标,或者不能保持国家周边空气质量的一级或者二级标准。对于“显著影响”这一法律用语的理解,环保组织提出法律在根本上禁止成本考虑;法院则认为,显著性不应当“只用一种尺度来衡量”,即“健康”的尺度,在很多情况下,除非立法机关明确作出了相反的规定,否则,应当认为包含“成本的考量”[4]249,250。
2001年在著名的“美国卡车协会”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法院同意下级法院对于《清洁空气法》第109节禁止环保局在确定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时考虑成本的解释,但就判决结果来看,还是通过肯定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和风险衡量的必要,灵活地弥补了制定法中排斥成本考虑的规定。布雷耶大法官在其个人意见书中称:“管制者应当考虑管制的所有不利后果,尤其是那些明显可能产生严重的或不成比例的公共损害的不利后果。因此,我相信,在其他问题上也是一样,我们本该从法规沉默或含糊的语言中读到的是允许,而不是禁止(对成本的考虑)”[13]。在布雷耶看来,涉及到不确定性强的环境标准设定,国会本来就有意授予环保局以裁量权,而环保局在裁量过程中进行成本—收益衡量或风险衡量在所难免,相反,环保局丝毫不考虑各种影响的权衡,任意选择并不见得就符合国会立法的目的。
这些案例表明,美国法院对于环境行政过程中的成本考量的态度,多半的时候遵循“就事论事”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14],很难冠以一般性评价。正如卡多佐所云:“我们看到,决定是否忠实于先例以及是否忠实于有先例支持的原则并不能使我们在这条路上前进多远。原则不是一个,而是复杂的一束。说我们应当保持前后一致,这的确很好,但问题是与什么保持前后一致?应当与规则的起源保持一致,还是同发展的进程和趋势保持前后一致?或者是应当同逻辑、哲学或通过分析我们自己的和外国的制度所揭示的法理学的基本概念保持前后一致?所有这些忠实都是可能的。”[15]
五、评价与启示
环境规制成本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倍受关注,为历任总统所重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此前环境规制的高社会经济成本的一种反思。有研究显示,美国1973—1985年间,环境控制使得GDP的增长率下降了0.19个百分点[7]153。尽管该项数据没有包括环境控制带来的健康收益,但是它也足以引起美国官方和民间对环境控制的成本合理性问题的敏感和警惕。
正是环境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从1975-1995年,美国在控制污染方面的花费超过了1万亿美元,如果采用一些替代方案,只要花不足其1/4的成本就可取得同样的成效[8]436。尽管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估环境管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粗糙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但成本考量作为行政执法的基础,可以避免产生不成比例、不合理的代价,并且让人反思环境行政中命令控制模式的僵化和低效问题和提高政策措施的激励性。美国学者艾瑞克.A.波斯纳因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成本—收益分析的规制制度是美国自《宪法》颁布以来对《宪法》的一次重大修正,也是自1946年《行政程序法》实施以来对《行政程序法》的一次根本改革[1]68。
关注美国环境行政规制中的成本考量,有助于我们反思我国环境行政实践中的某些盲目和失误。从20世纪90年代先声夺人的“零点行动”到近年接连的“环保风暴”,一方面,没有人否认这些暴风骤雨般的行动的巨大意义:这些运动引发的环境规制在建设必要的治污工程、控制局部区域水污染的恶化趋势、促进环境法的实施和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都产生了显著的成效;另一方面,应当承认的是,这些管制措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淮河、太湖等国家重点污染防治流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规制成本巨大而环境风险仍然此伏彼起;环保部门的管制重点常常不恰当地被公众牵引到了像圆明园防渗工程这样的小问题上,对环境保护中的经济因素和科学因素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其结果很可能令环保行动“妖魔化”,环境法的实施遭遇更多的障碍。
国内有学者认为美国在环境风险的控制上表现出“以保护健康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16],美国人自己却很有保留地声称,“即使环境保护的利益因司法可实施权利的状况而得到增进,它仍旧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保护,并且其公共成本将与提供保护的程度成正比例增长”,并因而慨叹“环境保护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17]。美国的环境法律实践表明,关注环境规制的成本,将规制成本与收益相权衡,对于正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避免因为不恰当的规制方式带来更加严重的环境损害后果,恰恰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席涛.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成本-收益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9.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574-575.
[3]曾贤刚.环境影响经济评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4-5.
[4]凯斯•R•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6-7.
[5]RobertV•Rercival,etc.EnvironmentalRegulation:Law,Science,andPolicy,4th.AspenPublishers,2003:137.
[6]张四明.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决策上的应用与限制[J].行政暨政策学报,2000,3):45-74.
[7]阿罗,等.环境、卫生和安全规制的效益费用分析——原则的陈述[J].投资项目评价与经营决策信息资料,2005,(1):7-10.
[8]凯斯•R•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M].金朝武,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9-171.
[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项目和政策的经济评价指南[M].施涵,陈松,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25.
[10]汤姆•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第5版[M].严旭阳,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8.
[11]RobertH.Abrams,etc.EnvironmentalLawandPolicy-Nature,Law,andSociety,3rd,AspenPublishers,2004:678.
[12]罗杰•W•芬德利,丹尼尔•A•法伯.环境法概要[M].杨广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6-107.
[13]Whitmanv.AmericanTruckingAssociations,531U.S.457(2001).
[14]凯斯•R•桑斯坦.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
[15]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8-39.
[16]唐双娥.环境法风险防范原则研究——法律与科学的对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0.
[17]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0.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U.S. and Cost Benefit Analysis
ZHOU Wei
(Law Schoo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high socio economic cos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ince 1970s,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Cost Benefit Analysis(CBA)i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a of U.S.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BA in th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of U.S can help us face the complex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view what has been overlooked and what mistak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and avoid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by inappropriate regulations.
Key Words:Cost Benefit Analysis;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