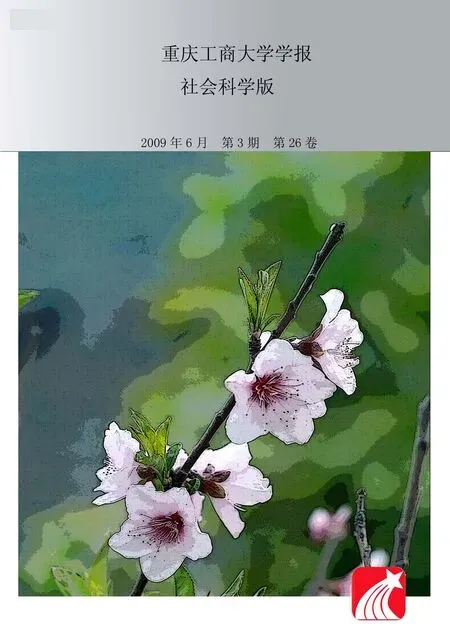守望家园:从文化复归到诗歌复兴
——文化诗学视阈里的当代大凉山诗歌*
贾剑秋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当市场经济迫使高雅文学边缘化后,写诗者比读诗者多,诗歌流派层出不穷,但除了有几次争夺话语权的嘴仗外,众声喧哗并没给枯寂诗坛带来春色,“诗人死了”、“诗歌死了”似乎成为当代诗歌的宿命。诗歌被迫潜隐“地下”民间,被当代文学研究挤出学术场,以致文坛时有“新诗精神重建”[1]、“诗歌复兴”[2]的焦灼和渴望。而地处边地的大凉山诗群,坚持他们的诗歌信仰,在颓圮的诗歌园地虔诚耕耘,试图以回归文化的姿态于死地而后生。尽管作为边缘群体他们被主流话语漠视,其创作也偏离了泛文化时代大众狂欢的轨道,但是,民族文化赋予他们诗歌美学的强悍生命力和多元色彩,让荒凉的诗坛响起幽谷足音——或许它昭示着诗歌复兴的信号。
大凉山诗歌出自一个有鲜明民族地域文化色彩和诗歌流派色彩的创作群体——大凉山诗群,主要由新时期以后登上诗坛,籍出大凉山地区的中青年彝族诗人组成,有的成果早熟,更多诗人的风采显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目前已成一个成果丰卓的庞大诗群。其诗歌集体性地显示出民族文化的底蕴和美学色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涵、担负的人类道义、张扬的诗歌精神与理想、体现的诗歌品格与价值,与那些要“卸掉诗歌众多的承载、担负、所指、教益,让她变成完全凭直感的、有弹性的、随意的、轻盈的东西”[3]的大白话诗或“口语诗”、“废话诗”、“下半身写作”、“裸诗”之类有着天壤之别。既彰显出诗歌灵魂的精神诉求,又展示着诗艺创新的风姿;既有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审视,又焕发着文化新质带来的生命活力。在文化诗学的视阈中,这些诗具有真正社会审美文化意义上的优秀诗歌的必要素质——深刻的精神内蕴、丰富的人文维度、突出的民族品质、健康的诗情抒发和鲜明的诗艺追求。不可否认,大凉山诗歌正以文化复归的努力为诗歌生命招魂,因此而催生了其诗歌卓异的文化诗学品质。如此品质的诗歌理应为当代诗坛瞩目。
诗歌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审美文化现象。它来自人类天性中对真、善、美的需求与同理期待,体现着人类的人文关怀精神和诗意的追求,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人类在文明创造中追求“诗意的栖居”,“诗意”指向人类的精神家园,要求诗歌创造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人类缺失深度精神文化就无法实现“诗意的栖居”。所以,诗歌理应承载丰富的文化元素,蕴涵感动、熏陶、引导、鼓励人类向上、向善、向真的品质,并借助艺术手段实现其精神文化价值。朦胧诗以后众多诗人或自命为诗人的人写的诗、印的诗集之多恐怕前所未有,“废话诗”、“口语诗”、“下半身写作”、“裸诗”以及煞费苦心追新求异而致晦涩、怪异的先锋诗之类尘嚣甚上,不仅未能救赎诗歌,反致诗歌生命衰竭,何也?盖因诗歌精神价值的消减——缺失诗性品格、缺少体现诗歌价值的文化精神,无法感动、鼓励、熏陶、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去实现人类精神世界的升华,无法让我们“诗意的栖居”。而大凉山诗歌则不然,其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来自于独特优秀的诗学品格。
一、深厚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精神构成的卓异、崇高的诗性品质
人文关怀是诗性构成的主体,是人类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意识的集合。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基础与终极价值,也是诗歌终极关怀的基本内容。“终极关怀所指向的全都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如人的自我认识(我是谁?我从那里来,又到那里去)问题,人的处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及人的根本困境等等问题。”[4]终极关怀在哲学层面上体现着人类发展的形而上思考,是人类精神提升的通道,它使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不断净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走向崇高、广博。现实关怀则在社会学层面上体现着文化的濡染、教化作用,它使人类趋美、趋善,使人类品性进步、完美。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共同构建起文学的品质与价值,成为文学精神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文学就是苍白的、孱弱的。大凉山诗歌正是在开拓诗歌灵魂的意义上坚守他们的诗歌理想,将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精神贯注其间。诗中积蕴着诗人对生命终极的叩问,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我写诗,是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死亡”,“我写诗,是因为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我写诗,是因为人类居住在这个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大地上,人类面对万物和自身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其本质和规律”。[5]于是,吉狄马加在厚重的沉思中看到一个族群生存处境的悲壮与孤独“我看见一个孩子站在山冈上/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充满了忧伤”;倮伍拉且透视着“白云拉不走它/太阳带不走它/它永远盘旋”(《盘旋的鹰》)的一个民族坚韧的魂魄,发现人类生生不息的真谛;发星将乡土家园和精神家园同化在一片澄明空灵的世界:“少女/水果 鲜嫩的手指/这些使人心跳的字眼重新回到自然之地/接受沐浴 接受光线的柔和/接受诗意的表白与牵引”(《梦幻》),精神守候的坚定与自然巡礼的欢跃同时流淌于诗人笔端“我的那些诗句 那些从彝女红扑的脸颊间/扑来的山花梦忆/在一条条山道上站立成静穆的林子/我忽然明白/在有新鲜空气不断袭扰的山谷/心灵的月光总是皎洁”(发星《从我笔尖走过的彝人》)。如果说他们的终极关怀在于对生命意识的开掘与生存处境的关注,更多文化思索的沉重,那么,其现实关怀则建立在对人类现代处境的解析与未来命运的关注上,更多情感意绪的沉痛。阿库乌雾以学者的理性和诗人的感性解剖大工业社会人类的生存危机,探索民族文化的命运:在“日历簿上开满月季花”的繁荣盛景遮蔽下,文化患了“贫血症”,“工业以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的方式 充当着/畸形或非畸形的城市催生素”(《倒影》);牧莎·斯加有感于人类精神失缺而手足无措的现实,吟唱起痛失人类之善的哀歌:“眼睁睁地望着/仁善的雨露/从我们中间/消失。……英雄与美丽的光环/总是镀满挽歌泪花”(《毕摩子额莫的命运》)。这类人文关怀意识是他们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反叛了当今一切浅薄、庸俗、丑恶、反文化、伪文化的诗学旨趣,无疑给诗坛扬起了人类精神的理性旗帜。
二、多元、深度的精神文化维度所形成的诗歌丰厚意蕴
诗歌不同于“顺口溜”或“流水账”,在于它具有丰富深厚的精神文化蕴涵。诗人以高度集中与概括的艺术手法将人类创造文化的体验、情感、行为浓缩,提炼并形象化,形成人类精神产物。其集中与概括的终极是反映人类的深度精神文化,体现诗歌所承载的精神价值的构成。优秀诗歌高度集中与概括了人类文化创造的最高精神成果,最能体现文化升华到文明的精神积累,体现人类生存、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古往今来,众多杰出诗人追求的诗歌理想莫不是将这种精神积累和意义不断延伸、不断丰富。诗歌生命只有建立在深刻的精神文化向度上才会永驻不衰,多元化的精神文化向度才能带来诗歌园地的斑斓多彩。而构成诗歌的深度精神文化,“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入”,“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6]。不同优秀文化的不断交融、深入、演化,升华为人类性的精神文化,成为人类社会由蒙昧进入文明,由鄙陋走向先进的精神动力。
大凉山诗群正是积极努力地推进诗歌内涵的精神文化维度,在关注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实,在诗性精神的提升与文化精神层的深度开掘上不遗余力。他们以连绵不绝的文化景象,文化创造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类生存思考的智慧,不断延续、丰富人类文化的精神积累与文化进步的意义。其诗意在多维文化空间显得无比饱满、绚烂。他们以深沉的眼光巡检民族文化历程,透视丰富的民族文化深层积淀:民族历史、道德价值、信仰崇拜、语言范式、族源亲情、地域风物等等都呈现于诗作,过去的创造,现在的审视带着精神世界的穿透力给人以震撼、感动。当我们被粗鄙的伪文化包围,任意撕扯宰割历经千百年精神洗礼的文化镜像时,大凉山诗歌让我们在震撼与感动中看到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径,看到了民族文化生成的根脉:“一个喜欢弓箭的汉子/不再迷恋狩猎的王国/跟着太阳寻找光明/跟着火焰寻找温暖”(马德清《属于彝人的道路》);“额头上写满历险的日记……/头颅上有远古洪荒时期群山的幻影/他褐色的胸脯是充满了野性和爱情的平原”(吉狄马加《最后的召唤》);“在巴国的许多山顶上学习历法/推算天文/交流神经/把华夏祖先羌戎的血脉在汉字的最初构想中留下印痕”(发星《思念巴国》)。他们在回视历史中寻找文化之根生长的家园、民族灵魂形成的渊源:神话、史诗、毕摩、英雄、经书、咒语、耕作、狩猎、火塘、族亲……这些文化积累构架了民族精神的基础,传递着保持民族文化鲜活生命的基因信号——在不断迁徙中经历艰辛和磨难的坚韧勇敢;在险恶环境下顽强生存的粗犷、强悍;在狩猎与耕作中创造文化的辉煌;在世代延续的传统中守望亲情、守望民族魂魄的执著。在他们诗歌张扬的精神旗帜上,写着许多富有人类性、永久性的文化价值符号——热爱自然、热爱美和生活;崇敬英雄阿格鲁支和睿智、英勇的祖先;赞赏勇猛、强悍、善良、勤劳、宽厚、仁爱;珍视生命、重视友情;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物质与精神的虔诚、感恩。这些人类的精神财富铺架起文化从蒙昧进化到文明的台阶,表达出人类普适性的真、善、美意识,是深度精神文化的集中与概括。而且他们的诗歌表达的文化符号频频闪烁着民族文化变迁后的新质——阿库乌雾忧患于现代文化的嬗变,“割据嶙峋的山脉是你们立体的耻辱/屠杀牛羊 屠杀草木/写成丘壑起伏的故事/于是 你们失去天堂/同时失去地狱”(《岁月》),他将艾略特的“荒原”意识嫁接到边缘民族的思想里,昭示着一个民族对人类未来承担的道义和对人类文化走向的思索;吉狄兆林从家乡的自然万物获得人类之爱的博大真谛,同时将博爱植入自然万象,以致“我深深地相信/空气稀薄的高地上这些石头/是一些有情有意的家伙/我甚至相信它们都有一双单眼皮的固执的小眼睛(像我一样)/最适合用来表达爱”(《人间的幸福——一些石头》)。他们对家园、自然的书写浇注了深度的精神旨意,使得单纯的诗句凝固了丰厚的意绪。大凉山诗群还以现代理性精神直面社会的发展,在时代大背景下贯穿起对文化终极的思考,其现代性的发散思维素质超越了传统文化的视界和规囿。阿苏越尔欣喜于“彝语、汉语和英语/在从马洪觉村回来的路上集体生长”其开放的胸怀与视野提示了民族文化走向现代社会的积极取向;诗人渴盼民族文化开放与更新的杂交优势“春天 迎接剪刀/创口中有嫁接的喜悦,这/是初步认识/良种从中脱颖而出。”(胡应鹏《对现代嫁接的一种新认识》),知道走不出大凉山就“永远不如一条河有远大的前程”(龚茂君《凉山彝人》),这种开放意识是现代社会彝族诗人文化进取姿态的华丽亮相,是民族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提升的写照。他们的诗歌有如此丰厚美丽的文化内蕴,才构成其诗学品质的深厚博大,崇高庄严。
三、民族文化浇灌的饱满、真实、强烈的诗情
“诗者,吟咏情性也”,[7]诗歌之美构成的重要元素是诗歌抒发的情感,以情感人是实现诗歌价值的重要手段,“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8]即使最直白浅显的口语化诗歌,如“床前明月光”之类也能给人特定的情绪感染。当下人们得出“诗歌死了”、“诗人死了”的诗值判断,大多缘于不满当今诗歌写情现状——真情缺失、个体情感褊狭难与读者共鸣,先锋手段拙涩导致情感抒写隐晦不畅等等,这一切致使诗歌难免缺乏感动、感染、感召人的活泼的生命力。徐志摩曾说自己的诗是从性灵里逃出来、血液里流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大凉山诗歌亦如此,是真实、强烈的性情之歌、生命之歌,其诗性往往是在激荡的诗情中实现。
大凉山诗歌的诗情摇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魂魄里,蓄满了民族性的文化生命——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传统、民族地域风物……其诗情或散发着史诗般宏大悠远的气息,或带着民族神话原型的生命体认,或是自己民族性格的沉重书写,或为历史传统的深情寻觅,或有地域万象的热烈赞美,或交织着对家园、族亲的缕缕衷情。倮伍拉且情思缭绕在祖先《湖兰色的森林》,在那片文化之林中,诗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马惹拉哈伤感于民族《最后的山脉》所面临的文化裂变,痛苦地看到“一片死亡的废墟上”,“平原”最终取代了“最后高傲的山脉”;阿库乌雾在《巫唱》和《咒语》中苦苦地寻找那枚民族灵魂《最后的火种》,渴望在文化困境中获得生命的突围;马德清把文化冲突的幽思用忧郁和悲壮编织起一道《凉山风景线》,“向天下人诉说/一个古老部落的消失/一个古老民族的希望”;发星将“泪水掬进深深的悲恸”,用《苍凉的歌谣》与死者作灵与灵的对话;倮伍沐嘎听见“从远方的门缝深处传来”《回家》的招魂声,在感动和忧伤里失魂落魄,“茫然失措”;阿苏越尔、马惹拉哈、阿黑约夫们则沉醉在他们生活的高山峻岭轻盈飘洒的“雪”中,倾诉着“从此灵息相闻,彼此祝福”的默默深情(《听人说古红木地又下了场大雪》),骄傲于“我们是雪的后代/我们如冬之冰凌遍体明洁”(《第一场红雪》),怀想那“心情随日月星辰的融合而融合”的“雪”如何“把真实的感情/深深地烙在大山的凝重之中”(《雪人》),显然诗情已将“雪”化为民族品格的缩影,化为诗人个体情感的方舟。岩羊的孤独、土地的忧郁、乡土的依恋、友情的深厚……总之,民族历史、故土家园、神灵传说、族源亲情、自然万物都是他们诗意环绕的轴心、诗情喷发的山口、意象采撷的园地。在民族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情感是深刻的、强烈的;在民族心理性格催生下的情感是沉郁的、庄严的;在民族文化生态里酝酿的情感是醇美的、酽浓的。他们抒发的情感演绎着彝人独特的民族气质——忧郁、深沉、内向、强悍、善良、炽热,借助诗情,诗人传递着自己对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的追想和肯定。情感内蕴的民族性不断发酵、张大,延展成一种博大深广的人类性情感,唤起人们对人性真理的认同和人类情感的共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正是这个道理。
四、多元文化交汇酿制的醇酽、悠长的诗味
“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9]诗味是优秀诗人艺术追求的目标,是诗歌艺术魅力的具体表现,品鉴诗歌“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0]显然,大凉山诗歌的艺术灵魂是极富诗味的。在大凉山乡村集会处笔者曾目睹人们如痴如醉地与诗人同吟大凉山诗歌;阿库乌雾在高校大礼堂、在乡村的集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时引来众人的同声回应;高校众多学子仿习大凉山诗歌,将其列入毕业论文研究课题……大凉山诗歌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让人们沉迷在那醇酽、悠长的诗味里。其诗歌艺术融合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美学元素,调动起纷繁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为诗歌魅力酿制出各种意味、情味、韵味、风味 ……他们或者继承民族诗歌传统,以克智、尔比尔吉似的短促精练的诗句书写生活哲理,描绘地域景象,类似“鼻子里的鼻子/嘴巴里的嘴巴/梳理空气和水/不需要鳃/不需要翅膀”(倮伍拉且《灵》)这样精短的诗句,其中的深蕴哪能轻易悟透;或者开发民族诗歌智慧,用想象、比喻、夸张、象征抒发性情、歌唱人性,即使醉倒于酒,而酒的含意“是一片广阔的土地”,被醉倒的是荞麦地里的歌谣和女人“那非常可爱的身影”(霁虹《为一杯酒歌唱》);巴莫曲布嫫踏歌而咏民族《图案的原始》纹意,起伏婉转的旋律“仿佛一条河流”,载着民族的历史、灵魂、生命;石万聪唱着古老的《〈女儿〉之歌》为“出嫁”的大凉山“阿姐”送行,悠扬的歌声画出一个“恒久的意境”;吉狄马加给诗歌插上现代主义翅膀,像艾青那样唱着“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土地》);阿库乌雾的诗嵌入传统与现代、母语与汉语、乡土与世界、理性与情怀,借助西学质素激活沉潜于记忆的文化基因,融现代诗艺创新民族文化符号的诗意美,韵味无穷;吉木狼格则用简洁明快的汉语口语在“非非主义”诗歌阵营探询文化归宿,隐喻的铺排下有“是”与“非”、传统与现实的思考,有毕摩的智慧、老庄的玄思,意味深长。品味大凉山诗歌,会让人陶醉在一种由中外文化、古今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交汇形成的诗歌氛围,感受到由悠远、庄重、淳朴、深沉、忧郁、清新、明快、炽热、粗犷、豪放、幽默等多种审美效应组成的醇厚、悠长的诗味。
综上所述,大凉山诗群将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自己的诗歌信仰和创作目标,以文化复归的姿态开辟诗歌复兴之路。他们把民族文化、人类意识作为诗歌灵魂,用卓异的诗性、丰富的诗意、强烈的诗情以及醇厚的诗味构筑起诗歌独特的、优异的诗学品质,为寂寞的诗坛奏响了诗歌复兴的笛音。
[参考文献]
[1] 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11).
[2] 何言宏.诗歌正在悄然复兴?[N].文汇读书周报.2007-11-9.
[3] 赵丽华.有关我的诗歌[EB/OL].http://blog.sina.com.cn.zhaolihua.
[4] 胡山林.文学艺术与终极关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 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吉狄马加诗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
[6] 童庆炳.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M].东方丛刊,2006(1).
[7]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8]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6.
[9] 贺拉斯.诗艺.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0] 钟嵘,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