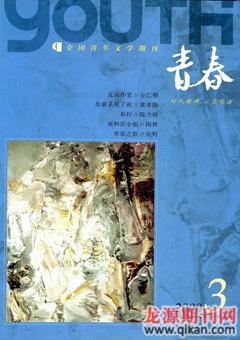书页里的盐
川 美
公元前七到六世纪,正是我们的《诗经》奇葩次第绽放的古老年代,在古希腊小亚细亚海边的勒斯波思岛(Lesbos)上居住着一位奇女子,名曰萨福。萨福整日怀抱竖琴,聚集一群山林仙女般的女伴们以歌诗唱和。她创作阿芙洛狄忒颂歌,教少女们吟唱,也教她们弹琴、崇拜仪式以及白昼与夜晚的庆典之舞。她创作了更多的抒情诗,赞美史诗中的英雄,赞美爱情、友情和自然万物。今人也许很难想象萨福与她的女弟子们居住怎样的屋舍,但她的诗歌分明告诉我们,勒斯波思岛是怎样的人间仙境:
此处甘棠荫里,
冷泉潺湲
四下里蔷薇覆盖,
白银光沙沙颤抖的枝叶
泻落酣眠;
此处亦有草地,马群游息,
春花开遍,蜜风
轻轻吹拂……
(田晓菲/译)
美丽的岛屿,浪漫的生活,构成萨福神话般的神秘世界。因此,她有理由高傲地宣称:“自会有人记得我——/我说——/即使在/另一个时代”。
她说这话时,也许更像一位预言家。在她死后历时约两千七百多年的时光里,后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她的追索。
萨福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转换的时代,她的诗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琴歌唱出来的,是依靠口头记诵而流传下来的。至少到公元前五世纪末,亦即在她身后百年,她的诗歌才得以被收集和书写下来,记录在芦纸卷子上。据载,公元前三世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萨福诗歌曾被学者们按照格律编成九卷,仅其中一卷就有1320行,但流传至今的,除了一二首相对完整外,其余的只是大约二百篇残简断章。
恰似风信子开花在山野里,牧人的脚
不断践踏,把紫色的小花儿踩入了泥…… (飞白/译)
在这首哀婉少女失去处子之身的诗里,那被踏碎的风信子,岂不也暗示了她那诗歌的命运?
空白的诗行和诗行里空白的词句,成为后代诗人、学者们不尽玄思的谜。一些好事的诗人(诸如伯恩斯通),像精细的考古学家修补破碎残缺的出土陶罐一样,修补过萨福的残诗。尽管那修补过的诗歌不再是“萨福的”,但仍不失其精致与美妙,甚至借萨福的名义成为传世之作。而关于萨福的身世,又将修补得怎样呢?倘若连这也不再是“萨福的”了,在天的萨福之灵可怎样看待她留在地上的萨福之影呢?
我们估且来端详这修补过的萨福图像吧。让我们说,这奇女子是一位出身于古希腊勒思波斯岛的名门闺秀,十七岁始做诗,与阿尔凯乌斯唱和。她曾因家庭成员参与政治活动受株连,流寓西西里岛,数年后回乡。她的兄弟中,一个叫莱瑞克斯,曾在弥特利城议事厅的公宴上负责执爵倒酒;另一个叫卡拉克索思,曾航海去埃及经商,迷恋上一个叫多瑞哈的女子,并为她花去大量钱财,也有人说他曾花巨金为名妓“蔷薇颊”赎身。她有一个女儿,叫克莱伊丝,与她母亲同名,她爱着这个宝贝女儿,“拿整个吕底亚也不换”。她有超凡的才艺,为柏拉图称道:“漫不经心的人称缪斯只有九个,须知勒斯波思的萨福是第十位文艺女神。” 她有美丽娇好的容貌,与她同时代的诗人阿尔凯乌斯有诗赞美:“堇色头发,纯净的,/笑容好似蜂蜜的萨福啊”!她有许多女伴,她用诗歌表达她的爱慕和歌颂,厌弃与嘲笑,也因此而获得经久不息的坏名声:她的名字和她所居住的勒斯波思岛成为“女同性恋”的专有术语。她有一位苦苦追求而不得的异性恋人,名叫法翁,是一位英俊的渔夫,正是因了对他无望的爱,萨福最终从卢卡斯悬崖投海自杀。她一生诗歌无数,却几乎全部散失风中,尽管如此,米雷格(约公元前100年)仍坚定地褒奖她留下的诗篇:“虽然不多,但朵朵都是蔷薇”。
由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田晓菲博士编译的《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是一本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萨福专著,遗憾的是,里面所收萨福诗歌皆译自英译本,而不是最初的希腊文,这种转来转去的译本,让人不能不担心会大量丢失本来的萨福。因此,我不能肯定,这是一部让人满意的萨福诗歌译著。但是,她是一部比较“全面的”萨福,尤其是第三辑里收录的自古希腊郎古斯(公元前三世纪)的田园爱情小说《达弗尼斯和克洛伊》(节选)、古罗马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的《萨福致法翁》,直到本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单得勒(1953——)的《咏地下铁》,这些“多出来的”萨福将作为额外的补偿,让我们仿佛听到在萨福身后世世代代的萨福迷们一路追随的脚步声。
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
田晓菲 /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迷人的海
眼下,我第二遍读完了约翰·班维尔的《海》。在我少得可怜的一周假期中,居然把两天的阅读时间花费在这上面。昨天和前天。
我洗干净手,然后开始打开这部小说。当我在一堆破碎的情节中摸索,感觉是在对付一个不太简单的拼图游戏。我最初能做的只是读懂每一小片形状不规则,描绘着各种不完整图案的纸片。不得不惊叹,那些图案呈现出的细节异乎寻常的清晰迷人,就像呈现在液晶显示屏上一样。而且,场景和氛围也是异乎寻常的真实,直逼五官。你似乎可以伸出手指,感觉一下那里面人物的肌肤,比如你不妨摸摸上校那对像皮革一样支棱着、仿佛风干又熏制过的耳朵,或者摸摸他的被岁月侵蚀的打着皱,褐色,像牛皮纸一样闪亮的手背。你也可以站在奶牛工戴戈南家的小院,看看院子里的母鸡怎样“迈着谨慎的碎步蹒跚在白垩与橄榄青色的鸡粪中间”。或者,听听睡在沙滩上的格雷斯太太温柔的鼾声,班维尔把它形容成“柔软的小引擎,不断启动又不断失败”——我的意思是说,班维尔的语言简直棒极了。这不单得益于他对事物的准确把握,更得益于他高操的调遣词语的能力。词语几乎信手拈来,却全都选择、安置得如此妥帖,“非它莫属”。这就是语言大师的魅力!
当把所有的情节碎片烂熟于心,现在,我敢说,我可以很顺利地拼出一张完整的图画了——主人公马科斯的心灵地图。
艺术史学家马科斯一直跟相爱的妻子安娜过着相对怡然恬淡的生活。然而,就在他们刚刚步入老年的时候,安娜不幸患上绝症,他陪伴她度过痛苦煎熬的一年,直到安娜在一个黎明来临前离世。此后他陷
无边的孤独、回忆和对人生的迷惑之中,渴望摆脱冷酷的现实和更加冷酷的未来,渴望“在子宫般温暖安全的地方挖个洞,躲避外面无关紧要的注视和粗粝空气的伤害”。他终于找到了这理想的也是唯一的庇护所,他童年生活的海滨度假村巴厘来斯。那是他过去的过去,那里有他苦涩的童年生活,有他青涩的朦胧爱情,有欢乐的泡沫,也有一辈子无法抹去的忧伤。一场偶然的梦把他牵到那里——香杉墅——他小时候暗恋过的格雷斯太太和小情人一样的玩伴克罗伊住过的房子。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日子,而萦绕在心中的痛苦和困惑,从来没停止过对他的折磨,在一次酩酊大醉之后,他被迫重新回到他和安娜生活过的房子。
现在,我打量着这张拼图上两个重要的象征性的地方。
大海——马科斯没有交待它的名字。其实,所有的海都是一体。海,是那样一种象征,苍茫,辽阔,起伏不定,像时间一样永恒。海是一切事物的背景和见证,生与死的背景和见证。
香杉墅——格雷斯一家居住的海滨度假别墅,它曾经是富贵的象征。在童年马科斯眼里,夏日的海滨,世界的结构是那样的稳定而难以攀登的金字塔,“顶端是少数拥有度假别墅的家庭,然后是那些能住得起旅馆的——沙滩旅馆比高尔夫旅馆更好——然后是租房子的,然后是我们。”五十年前,穷小子马科斯梦想从陡峭的社会台阶的底层爬到格雷斯一家看起来的那样,他用孩子的方式成功走进这座神秘的房子,成为格雷斯家双胞胎的朋友。直到大海吞没了双胞胎姐弟。直到男主人格雷斯死于血管瘤,女主人格雷斯太太死于车祸。命运整个毁了这个曾经快乐无忧的家庭。五十年后,香杉墅犹在,却成了另一种象征:流动的剧场。物是,人非。因为,“这儿毕竟只是寓所,无数生者往来如织,早已将逝者的痕迹消磨殆尽。”岁月完全抹去了格雷斯一家生活过的蛛丝马迹。
拼图之上飘浮着马科斯的纷繁的思绪,它们像羽毛一样轻盈,同时有着金铂一样的分量。他说——
“我们都是些盛满了悲哀的小船,航行在压抑的静谧中,穿行过秋日的黑暗。”
“我们带着死者的记忆直到我们自己也死去,我们承担了一段携带者的角色,然后我们的携带者也将离开人世,依次循环至无穷世代。……真的,我们中的什么会存留下来,褪色的照片,一绺头发,几截指纹,我们最后咽气的房间中的一粒原子,所有这些都不再是我们的——现在或者过去的我们——而只是死亡
的尘埃。”
“也许整个生命不过就是在为离去做的一场准备。”
“当现实,这愚蠢的自满的现实,控制住这些我自以为记得的事情,将它们打回原形。一些宝贵的东西被毁坏了,从我的指尖流走。然而,最终,我轻易地放弃了它。……真实的往昔,并没有我们假装的那么重要。”
而这些真理般的语言明显指向两个字:虚无。
最后我要说,小说叙述的核心故事——安娜的死和双胞胎的死,两条主线交织在一起,像来自大海中的两股暗流,只是前者是可期待的,就像一个破折号,而后者如突如其来,更像一个惊叹号。
《海》
约翰·班维尔 (爱尔兰)/著王睿 夏洛/译
作者简介:
川美,辽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梦船》、诗集《我的玫瑰庄园》;出版译著《清新的田野》、《鸟与诗人》、《山间夏日》。散文、诗歌作品曾收入《中国散文年选》、《中国诗歌精选》等多种选本。2004年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