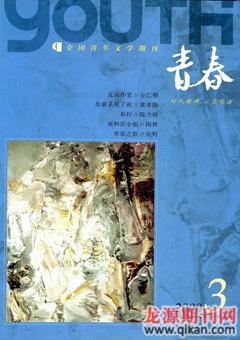阅读随笔
习 习
阅读随笔
那幅画是我在某个深夜看到的,打开一本书,刚好看见了它。画面叫我很紧张,我于是仔细琢磨起了画的全局,想了解它令我紧张的缘由。窗外的黑一下子涌了进来。我睡了,梦境里四处奔逃,为无形的事物所追赶。依然是在深夜,但梦里有亮白的光,四处的黑影诡谲地匍匐下来……这时,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金属声,我猛然惊醒,那声音还在耳旁响着颤颤的余音。
我终于明白过来,那金属声是从书中那幅画里发出来的。
那幅画被称为《一条街上的神秘与忧郁》,不知是不是画家契里柯的亲自命名——意大利男人的忧郁是由来已久的。但我不喜欢过于累赘的称谓,界定越多,随之散发掉的东西越多。
天亮后,我又仔细端详起了那幅画。在一片晨曦中,画面一下子变得很小、离我很远。但注目片刻后,我又走进了画面。这是最令我紧张的画。我曾被凡高的《星夜》和《麦田上的鸦群》所压迫,那是因为画面本身战栗着、遍布了死亡的气息。但这幅画很安静。仿佛是另一只眼从高处的俯视,两座相向而立的高大建筑,呈现冷硬的几何线条。一面建筑被光亮照得惨白,整齐排列的黑色门窗像两排深深的咽喉;另一面建筑藏在浓重的阴影里,如临深渊。两面建筑之间半明半暗的街头,飞奔出一个滚铁环的女孩。女孩飞奔,对面街面上铺着一个静静的人影,堵截在女孩要奔去的方向。是一个阴谋或者宿命?那光亮想必是阳光,即便是刺眼的阳光,晒在街上,也是冷冷的烫。
我梦中的声音就是那个飞奔的铁环发出的,尖锐的声音滚在地面上,刺破纸张。女孩对面的那个人形就是梦中我要逃逸的事物。我是梦中人,另一个我在俯瞰我的梦境,那只俯瞰的眼睛是冷冷静静的,但梦中的我万般焦虑、无处逃逸。
——《一条街上的神秘与忧郁》,“神秘”、“忧郁”,与我的“紧张”而言,缺乏的仅仅是密度吗?
菊花将开,袅娜的花瓣是向内的,即使它怒放,纷繁的花瓣依然紧张地扣向内部。
我在读他的书时,他的文字便给我这样的感受。语言细密,刻刀雕过一般精致,恰如菊花的花瓣那样一丝不苟。而且它朝向内心,繁复、层层叠叠地抱成团。他把一个个柔软伸展到了异乎倔强的纤细。读不到敞亮之处,于是我不停地呷着热茶,似乎要借着茶的热气要将内里凝结的东西散发出来。
看完了他写的整整一本书,我觉得他的每篇文字都像一瓣内向的菊花,细致而美,但也很相像。他把一本书开成了一朵紧促的菊花,我想,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是一朵可以摘到手心里仔细把玩的菊花。还有一种迥异于它的文字,它若沧海流云,漫漶于俯仰之间,甚至在你凝神的一瞬,它依然动荡着,它一直在你的把握之外,会长时间地令你心旌摇荡。
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在街上散步,碰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中学同学。他说,去我家喝茶吧,刚从南方带来的新茶。那是我第一次喝那么新鲜的茶,我忘了什么茶,生长自哪里。我喝出了茶里一股淡淡的豆香。后来,但凡喝出茶中的那股豆香,便知那是新采摘的茶。可我所谓的茶里的豆香,在后来的十几年中,从未在任何跟前得到共识。这是个小小的无奈,有时很难相信,你眼里一个明明白白的真相,却无法叫他人看到。人世间的很多阻隔大抵也是这样造成的吧,有些事情就该是永远独有。
但就在前几天,很偶然的,我在一个朋友的文字里看到了他说龙井茶的一段话,他说,新鲜的龙井里有豆的香气。我有点激动,很想马上告诉他,不只龙井,在贵州、在四川、在杭州,我在很多品种的鲜茶里都喝出了豆香。豆香是淡淡的,若隐若现,并不滋扰不同风格的茶味。
我忽然很想与他交流一下另一种物质的气味,但忽然又打住了。先前,我曾问过一个人,你知道它有什么气味吗?他踟躇许久,说,无味。我说:它有生麦子的气味,他很不相信,他说,男人身体里的这种东西怎会有植物的气味?
世间尚有许多事无法与人交流,何况就它的气味呢?
可我确信无疑,小时候,我们成群结伙地在潜伏在河滩边,没人时,偷摘月光地里的麦子。麦粒还青青嫩嫩的,咬开来,里面是乳白的浆液……
它的气味虽然清淡,但的确有青嫩的麦子即要成熟时的气味。
我珍藏着他的声音,不愿示众。怕它被和声污染。公开过于热爱的东西,我一直心存担忧。我把他的声音放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只我一人独享。我独享着自己的怪癖,像喜欢观望一个个苍老男人的背影一样。
他的歌声有着独一无二的低沉,低到几乎在诉说,在很简单的旋律中,他自顾自地诉说。我和他,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彼此无需任何回应。低沉的声音从身心深处缓缓发出,像是在往昔中抽丝拉茧。静悄的深夜,没有灯光。这个老男子的歌声慢慢地升起来,不急不躁、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好几次,我在他的歌声里眼底潮湿。我知道,我迷恋的是他歌声里长长的时间。
其实我不懂他的语言,但我能看得见他的表情、他述说时安静的姿势。有时候,我会跌落在他声音的某处,他的诉说已走得很远,但我还停在那里……其实,除了知道他叫雷纳德﹒科恩之外,我对他的其它一无所知。
喜欢朋友马丁的这句话:诵经声托出的城市——他把我们这个边远的城市说得很有意味。
我和马丁未曾谋面,我们相识在文字里。马丁孱弱、敏感,我常从他的文字里嗅出忧伤。马丁从我们的城市迁徙到首都后,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怀想我们的城市。一天,我终于在他的一段文字中辨识到了我们的城市,他说,这个城市是诵经声托出的城市。这是拉开时空后才有的缈远的记忆,马丁帮我在远处瞭望。
我们的城市,黄河穿城而过,亘古至今,黄河与这里的人们时代相处,马丁自然会说到它。他说了一件与黄河有关的事:有一个人不知道怎样向女生表达,突然跳进了冰凉的河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同一事件的见证者。那一年深秋,在河畔,我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河水中一动不动,人群在桥栏外越积越多,我拨通了110电话,搜救的船只很快到了,冻僵的他被拉上船只时,我才看到了河畔一个与他相关的姑娘,她坐在草丛里,冷静地考验着她的小伙子的忠诚。
我们的城市随黄河蜿蜒成一条细瘦的带子。黄河以北以南,矗立着南山北山。马丁曾居住在城市边沿的河畔,河对面的北山上烧着干涸的火红。
马丁还说到了我们城市的混乱和人群跌落在南北两山之间的无形的焦躁和狭隘,他又忧伤了。不过,他说,这是个诵经声托出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散落着好些清真寺,高高的清真寺穹顶,顶着一弯新月,每天天欲亮时,诵经声从这里传出。悠远的声音在尘世的高空传散。空气潮湿的清晨,声音更加清澈。它飘进我恍惚的睡梦里,这一天就要被干净地托出来了。
我相信马丁是不善言辞的,和我一样。如果我们不期而遇,我们一定会很局促,也许我们会说几句无关彼此言不由衷的话。但我始终会记着他的这句话:诵经声托出的城市。干净的诵经声跟随我穿梭于大街小巷。人们在林立的高楼间仓惶、奔碌。但因为日日都有澄净的声音在高处响起,我的每一天的开始就仿佛沉静了许多。
很少收到邮局寄来的信件了。但朋友孙江固执地坚持着这种传达消息的方式。他不会发手机短信,电脑里也不设置邮箱。他还坚持在他那发黄了的信纸上用毛笔写字。六、七年前,他就告我,单位淘汰了若干年前的一批信笺。他如获至宝,将它们全部带回家里。他一直用那些信笺写信。暗黄的信笺因为愈加毛糙而显得温暖,墨汁洇开,每一道笔划里都有奇异的柔软。
在去内蒙额济纳旗的途中,我在他酒泉的家中小坐,他用的镇纸是两块粗糙的硬木,木纹扭结,里面有坚硬的树瘤。这些都和他气味相投。
刚收到他一封信,他把信写在几页杂志上。纸的背面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几篇短文。他读了,觉得好,就顺手撕下寄了过来。我读了那组文字,也挺喜欢。我细细阅读阿特伍德时,手里触摸着他的墨迹。这些文字他也读过,他还在这些文字背面用毛笔做了记号。
我常说他是在酒泉泡老了的酒鬼,他虽然常常酒眼惺忪,但事事洞悉。翻过他的信,我名字背面,阿特伍德说:“我走进那片废弃的果园,因为我不想跟你说什么,甚至也不想看到你,我想做些有用而且能做得不错的琐事……”阿特伍德这些翻译过来的文字读起来不错。我对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心存疑虑,就是担忧我看到的并不是作者所写的。
孙江称呼我从来都随心所欲,他叫我勺勺或者刁刁。这次他在信上叫我勺妹子,他喝了酒偶尔会来个电话,辟头就唤我勺妹子。这次他是不会醉着的,他的毛笔字看上去有点儿优雅,大约有了阿特伍德的文字在一边,所以他的信看上去少了很多酒后的放诞。
《枕草子》就在枕边,喜欢“枕草子”三个字。枕草子有枕边书的意思,既是枕边书,就可以宽了衣解了带,在床前的一团灯光里躺着去读。但我还是喜欢按了自己的意思理解,“枕草子”里断不可少了那“草”字,那字没了,就少了植物的颜色和香气。
清少纳言这名字也好。可清女的文章太娇嫩,像早春浅粉的杏花,与这四个字的气味很是不投。清女的文字确能催人入眠:“蚂蚁很讨厌,不过它身子很轻,竟能在水面上平安地跑来跑去,十分有趣。”她天真娇嗔的样子活灵活现,真的就像绘卷里的她,烂漫、纯真,但那云鬓散落的慵懒里多了几份大女人的味道,不过这该是后宫女子独有的模样吧。
清女的文字配了绘卷,相得益彰、二者愈是清纯香艳。大都是工笔画,精致的笔触里揉进了满满的爱欲。《七月里,风劲吹》依然有她一贯的悠闲:“七月里,风劲吹。大雨哗哗下的日子,大抵天气很凉,早已忘记用扇子的事。这时,将带有汗水味的薄衣拉过来,蒙在头上,睡个午觉,很是舒畅。”版画家海老名正夫为此文配过一幅木版画,精雕细刻:华丽的榻上,貌美的清女扶颊遐思,黑发堆在肩头,透明的衫子里有两粒粉色的乳晕。我无端地想,日本女子矜持,但人性里有很明亮自由的一面。后来又查了些资料,原来清女的文字配过许多这样气味的绘卷。大约近一千年前的画面了,叫人遐想。
作者简介:
习习,甘肃兰州人。著有大量散文、小说。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天涯》、《青年文学》、《散文》、《散文海外版》、《美文》、《山花》、《红豆》等,在《青春》发表散文多篇,并有多篇散文入选各类选本。著有散文集《浮现》(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讲述:她们》等。《浮现》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一等奖。现在兰州某杂志做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