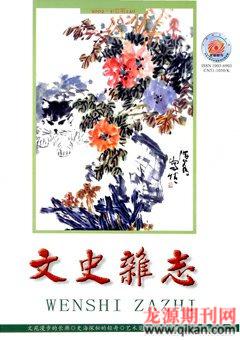孙中山毕生爱读书
朱小农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一位著名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之所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是与他始终不断地吸收新知识分不开的。孙中山的毕生爱好就是读书。黄昌穀在《孙中山先生之生活》中引孙中山自述说:“我一生除革命外,惟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孙中山自香港西医书院完成学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无论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还是政务繁忙的从政时期,都未曾忘记读书;尤其是在革命受挫之际,读书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书便会跟不上时代,变成一个落伍者。
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许多国民党元老,对孙中山勤恳读书,手不释卷,以学习为乐的爱好都有极深刻的认识。吴稚晖在《总理行谊》中说:“中山先生治事,一有暇晷,就手不释卷。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两三箱书跟了他走”;“中山先生每天除工作饮食睡眠外,皆手不释卷”。黄昌穀在《孙中山先生之生活》中说:“国父一生的生活,无论是在做事,或者是休息,每次除了饮食做事之外,总是手不释卷。”
孙中山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7岁进私塾,曾接触过四书五经。他在13岁时远赴檀香山,接受了5年的西式教育;后来又在香港、广州两地求学。1883年,他进香港拔萃书院,第二年转入中央书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就是在这段时期,他在课余时间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不仅节约生活费用,买了一套大部头“二十四史”,而且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他读了以后感到英文译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释更容易明白,于是借来经常研读。后来他于1916年7月15日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与传统的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1]
在孙中山的知识结构里,传统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专业是西医。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度过了求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他的阅读非常广泛,常常在夜里起床点灯读书,《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孙中山的心灵。到晚年,孙中山在他的演讲中还不时地提及达尔文,如1923年12月21日在广州岭南大学,他在号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时,就列举了达尔文的例子:“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便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的道理。现在扩充这个道理,不但是一切动物变化的道理包括在内,就是社会、政治、教育、伦理等种种哲理,都不能逃出他的范围之外。所以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2]
那个时候,孙中山已在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清政府了;可是,他仍然对各方面的书籍和学问都有兴趣。对农学,孙中山就有浓厚的兴趣,曾读过《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些古代的农书,也读过西方农业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农政机构、农业政策、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学科都有涉及。他在1891年前后所撰写的《农功》,引古叙今,引外议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农业思想。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倡言革命时,还曾创立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农学会”。他不仅是将其作为革命的掩护,而且亦在思考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改良。他发起“农学会”,也是希望搜罗翻译各国农桑新书,开风气之先;设立学堂,培养造就农技师;用科学方法检验各地的土质物产,著成专书,引导农民耕植等等。
孙中山一生为革命而奔走。革命与读书,看起来是两回事,实际上犹如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为孙中山先后接受正规教育达20年之久,并且在大学毕业后一面行医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一面不断地积极自修,广涉各种社会科学,况且又长年流亡海外,周游世界;而所知愈深,见闻愈广,革命救国之心亦就益切。
孙中山从20岁起就立志革命,后来虽曾试图以缓进方式改革政治,如“上李鸿章书”等;但自甲午战败后,即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从此放弃行医,专注于领导革命。“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既已立志献身革命,就必须潜心读书,从书中寻找真理,作为支持革命的原动力。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为一个国家的医生,医生没有知识,怎能为国家治病!
孙中山为革命在海外漂泊16年,虽居无定所,却往往携带很多书籍。孙科在《国父生平最爱读之习惯》一文中曾这样回忆说:“总理在革命的时候,常常作全球旅行。在旅途的时候,随身的物件很少,可是携带着很多最新出版的书籍。”吴稚晖在《总理行谊》中说:孙中山“带有箱子四五支,都是书。还有一部局刻的《资治通鉴》”。黄光学著《国父革命逸史》中记载了孙中山自己说过的话:“我数十年来,因为革命,没有固定的住所,每本书读毕,便送与友人。究竟读过多少书,不能尽记;不过,在革命失败时,每年书费至少四五千元;若奔走革命时,只二三千元而已。”孙中山不时从各地购书阅读,并将各种名著寄给儿子孙科,或者转送他人。他把自己的读书爱好,尽情地分享与家属和友人。
孙中山曾多次流亡到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那里的华侨是他的重要支持力量。其中他往来最多的是新加坡。据很早参加同盟会、担任新加坡分会副会长的华侨张永福回忆,孙中山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凡事都极乐观,喜欢读书,读书时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读后一定放回原处。孙中山喜欢买书,尤其是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和中国古籍。他不喜欢小说杂著、美术图画、音乐诗歌这类书。他对中国地图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对于各国陆军组织法及有关书籍、海军海舰图等,价钱虽高,也一定要买下来,熟读到差不多可以背诵。他的书籍分类摆放整齐,毫不混乱。
孙中山到过日本多次。在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夫人宫崎槌子印象中,孙中山一有空暇就是看书。有一次,他在宫崎家住了10天,几乎把他们家的全部藏书都看了一遍,临行时还用柳条箱子装了满满一箱带走。宫崎夫人回忆说,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常去东京和宫崎滔天见面,每次到他们家,有空就从随身带的皮箱中拿出书来读。读的书当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内容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哲学的。他还因为读书得罪过人。一次,他正在他们家走廊上看书,宫崎的乡亲胜木夫妇听说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主动与他攀谈;而看书正入神的孙中山只是随便答应了几声,眼睛并没有离开书。胜木误以为他傲慢不理人,用当地方言大声说:“这像什么话!听说孙文是个豪杰,怎么这样简慢人?”
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流亡期间,把时间也主要用于读书上。康德黎回忆说,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也买了很多书。吴稚晖在所撰《总理行谊》一书中,曾生动地描写过孙中山在伦敦读书的趣事:
有一年,中山先生在伦敦,有一友人叫曹亚伯见他很窘,设法凑集了四十个英镑送给他。过了几天,再去见他,忽见架上增添了不少新书。英国出版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籍和各种社会学、经济学等书,他统统买来了。那位曹先生见了很不高兴,以为四十英镑是送给他做生活费的,现在统统买书,花完以后,如何吃饭呢?但是,中山先生可不管这些。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一书介绍,清廷驻英使馆雇用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孙中山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至少有68次。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时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这一时期,对孙中山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是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这种单一税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便再度流亡日本。8月9日,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不久,当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全部装的是书。[3]孙中山抵达东京的第一天,把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就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的丸善株式会社是一家外文书店,是孙中山经常购书的地方。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购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1914年年初,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的书大为关注,2月28日这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罗素等人的著作。在他故居的藏书中还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915年5月,孙中山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他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在《总理学记》中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库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 。[4 ]邵元冲说他曾因孙中山各种书都嗜读不倦而请教孙中山究竟“以何者专攻”,孙中山回答说:“我无所谓专攻,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学问,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我皆用以为研究的资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因为需要大量参考书,他于是广泛搜集。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他在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订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孙文学说》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几十种。为了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光是经济方面的就有240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他在完成《民族主义》一稿后的序文里说:
《民族主义》一册已经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册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册,于思想之线索、研究之门径亦大略规划就绪,俟有余暇,便可执笔直书,无待思索。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可痛恨![5]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认为“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黄季陆在《国父的读书生活》中说:他于1923年秋自加拿大返国时,得到两本新书,一是罗吉尔、威芬贝合著的《战后欧洲新宪法》,一是罗吉尔、麦克汉合著的《近代政治问题》。他在旅途中读完了这两本书,甚为得意。当他到广州见到孙中山后,谈及最近出版的新书,就提到了这两本。不料孙中山立即就从书柜里取出了《近代政治问题》。黄季陆一翻,只见上面用红蓝笔注记画有许多横线、问号及不少的圈、叉等。
正是因为孙中山爱读书,又善思考,所以他学贯中西,正如沈清松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中所说:“国父的伟大,在于他能吸收欧美的优长,发扬中华文化之神髓。中华文化一向重视由个人的善性出发,扩而广之,及于群体,甚至有世界大同、天地合一的胸襟。”孙中山博古通今,融会各家之所长,创造性地提出了“孙文学说”,的确是在读书方面的成功典范。
孙中山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书,也就是与宋庆龄结婚以后所买的书,据统计,共计1932种,5230册,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体育、天文、地理、人物传记等,还有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这些书,在他于1925年3月11日的临终之际,作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一代伟人与书的因缘趣闻,当然也就未能因他的去世而划上句号。
注释:
[1]孙中山:《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据《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第171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3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4]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914年6月19日《孙文动静》,乙秘第1169号,《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88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省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