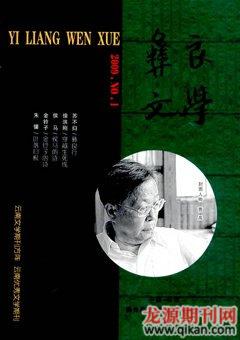彝良行
苏不归 1982年11月生于重庆,六载英伦学成归国,在英国期间做过文案翻译,制片助理,摄影助理,业余演员等工作。
★上篇
我是从这样的诗句中走进来的:“这里是世界最孤独的地方/阳光被绝壁折断/落下老鹰的羽毛和黄昏的血/愤怒的大河踏一路波涛/经过这里也收敛狂乱的步子/被风吹成任意弯曲的歌谣……当我日夜喧嚣的爱情没有归宿/火焰开始悬空蔓延/我的痛苦是一片树叶/在随波逐流中无法飞翔……黄金的门户也锁不住我的想像/星星正失足于绝壁/月亮也驶进我的怀里/但我在天亮之前向远方敞开的/只是冷冷的风景……”
当我被羽绒紧紧围裹的身体出现在今冬通往诗中的某一条山路时,我经不住蜿蜒走展的折腾,半梦半醒之间,上面一段声音的主人担忧并关切地为我打开了车窗,可身体孱弱的我把头往外一伸,在一片雾茫茫的风中仍然无法一吐为快,头脑眩晕双手僵硬,因为有着自以为是的侠肝义胆与豪情海量的我前夜喝得比车窗外铁色与白色凝成的乌蒙高原还高。
拜会诗人陈衍强是我蓄谋已久的事。当时我在英国伦敦,一边打工一边企图单凭思考去解决我想要远大的前程。出于对诗文的天生爱好,我白天上班晚上上网,在天花乱坠的博客里不知怎么就坠进一个所谓“散打诗人”的陷阱,这个陷阱释放出能让人开怀大笑的化学气体,不久我便在轮番的攻势下宣告中毒,在《喝酒记》尾巴上的三句话后面笑出两行叫眼泪的东西。当时奥地利的朋友兼房东艾瑞克经常发现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对着电脑傻笑,他怀疑我神经有问题,当我逐字逐句把陈衍强的诗翻译给他听了之后,他马上下楼,说要给我再买两瓶啤酒。这个拿着一杆烟,形象不羁又长得谁都不像的诗人制造大量的炸药,致使我的白天嗅他的硝烟,夜晚探访他的工厂,他不讨厌我,有时来串我门,我既高兴又充满了诗兴,也开始明目张胆地做起了化学实验。我做成的第一根爆竹是《石头城非梦》——题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这首被《彝良文学》选刊的诗歌成为我坚持写作的最好奖赏。陈衍强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其实是《彝良文学》手工艺厂的厂长,他简单地告诉我他要用我的诗歌,他知道我不会不从,因此他没有讲一个多余的字。写作激情被进一步激发的我继续埋首创作,在《伦敦撒威尔巷的西装》中我不要脸地提出了自己对《英雄美人》一书的渴望,他从十月的首都回来,途经重庆时,把写有他亲笔签名的诗集赠给了我。彼此诗歌每一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更新,促使我们之间的交流如同地球两端两个人平静的呼吸,那么平常,那么毫无羁绊,那么随意。而只有我决意去彝良的心中之火在熊熊燃烧,它不仅是英雄的热土,美女的圣地,陈衍强笔下的诗行,更重要的,它是快乐的源泉,精神的城堡,它跟我前世有着一段不可分割与解释的缘分。
2008年的冬至日清晨,我像一只麻雀跳出抵达云南昭通站的火车。正在昭通开知名作家座谈会的陈衍强带着不能亲自接待我的歉意,用手机和短信给我发来冬天里的一把烤火炉般的问候与关切,并经他昨夜的安排,让他的朋友李克强接我,杨云彪带我去逛逛,直到他把会坐完。李克强的兄长却成为这次我彝良之行第一个用方言当面交流的云南人,刚刚巨幅下降的气温和急剧回暖的人情,使我在缓慢行驶的车上一边打量着昭通的脸,一边听老李摆谈昭通的过去。热情的他把我交给十分钟之后的民警杨云彪,我们便分道扬镳了。明处的我被暗处过来的杨哥首先发现,我坐在停着的车上一回头就看见他迎面而来的真诚的笑脸。一番嘘寒问暖,杨哥带着我走进他的家,亲自削了一个昭通特产的大苹果,然后又一个更大的广柑,堵住我的嘴巴,让我甜在心头。我很快和这位出生大寨子乡的散文作家兼人民公安混为一谈,从他家堂屋正中作家雷平阳的题字到对古诗词的偏爱,其间另一位他的朋友也特地赶来,作家朱镛以他擅长的小说手法叩开了房门,与我们谈天说地把茶言欢。从杨云彪的家中到昭通的大街上再到古色古香的打铁巷,借着杨哥驾驶的小面包车,我们游览了这座凤凰山脚下城市的主要街道,享用了昭通小吃稀豆粉,在英雄罗炳辉的塑像下合影,在昭通群艺馆门前和毛主席塑像挥别,在时不时有马拉车经过的街上倾诉着彼此的心事……当我们走到一条叫爱民路的街上时,我被哥俩燃烧的热情拐进一间餐馆的二楼雅间,说好要请我共进午餐。盛情之下,其实难负,我被他们的真诚和无微不至感动,面对两位在文学造诣上不知超出我好几倍的兄弟,我们开始一边大口吃菜一边更大口地喝高度白酒,反复碰杯,我整整一大玻璃杯下去之后,杨哥接到电话:陈衍强马上到了。我随朱哥到楼下等,脸上已经红潮涌动。
陈衍强从我迎面的左边,不知是从哪一个车下来的,一看见他的时候他迈着急速的步子同时伸出了诗人温暖的右手,我迎上前去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就是一个遇见了久违的兄弟式的拥抱!然后我们上楼,雅间里的热火迅速被烧得更加猛烈了!已经用过午餐的衍强也不再喝酒,因为他风火轮一般飞快的语速已经足够摩擦起一股一股的静电,激情的谈话使我们忘我并心甘情愿沉醉其间。他在念着原本打算在文学座谈会上念出的书面发言的同时,我的夜光杯不知不觉中又被倾注满了,一敬衍强再敬兄弟,酒被桌子下火炉的火越燎越烫,逐渐我就忘了我喝的是高度的白酒……酒酣耳热之际,两位兄弟先前交口称赞的作家吕翼来了,镇雄的诗人尹马来了,场面霎时好不热闹!他们举起酒杯碰向只顾着兴奋的我,我也举起酒杯给予他们重重地还击……
发酵的我被悬空架进宾馆不知是哪个时辰的事,模糊中有谁喂了我糖水我也记不清了,我躺在沙发上喊冷,一直在我身旁照顾我的杨哥把他的外衣脱下来盖在我的身上,因为偌大的宾馆里找不出一床铺盖,我就这样一动不动把白天睡成了晚上。他们断定我还活着是晚上他们在一张大饭桌上吃饭的事,陈衍强的一首诗闯入了我的梦中,他在念着:尽管她/上过《时代周刊》封面……不知是哪里飚出的一股力量,我从沙发上顺势弹起来,大声说出他的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打死我都不相信!”笑声从几秒钟惊愕的停顿后哄堂响起,我被诗意地拉回饭桌和满座的知名作家们相提并论,虽然一粒饭也吃不下,但也能咬着盒装牛奶的吸管听他们摆龙门阵,我欣喜至少我还留了一口气和衍强到彝良去,今天我们在昭通文友的挽留和安排下就在此地度过,相聚的时间总是愉快而短暂的。我们与吕翼,杨云彪,朱镛等兄弟简短而深情地作别,我和陈衍强在他诗里出现的昭通会馆一觉梦到天亮,在天公不当美人的清晨小雨中,我随衍强一路到了昭通开往彝良的汽车站,吃了早点,坐上中巴。一路上的消费衍强都不许我掏钱,我只好乖乖坐下,忍气吞声,还有我的头昏仍在隐隐作祟,昨夜不知吐了多少次,盘蟒形的公路又将我生拉活扯,我的表现引起坐在旁边不远处衍强的高度重视和严重担心,我到达曾经离我万里之外的彝良后的第一站会是彝良县城医院吗?
★中篇
当汽车柳暗花明地驶近彝良县城,我渐渐睁开了我一直不敢睁开的眼睛。我们的车在两旁险峻山势的逼迫下,穿梭于一条快捷的大道,沙石在脚底下抱头飞窜,一条去县城赶集或赴约的河流在右边发出竖琴般好听的声音。“这就是洛泽河。”衍强为我洗清了心中的疑问,我心底的浪潮不断在拍打着,那些鬼斧神工的连绵大山,我呼吸得再紧张和缓慢,也跟不上它们哪怕是一秒钟的节奏。这不就是我心中神往的那一片土地吗?在这样神圣的时刻,值得纪念的时刻,我却带着宿醉,呼吸急促得不敢将雄伟挺拔的江山在眼底一路尽收!我只好在一半清醒一半醉之中靠想象来勾勒我眼前浮现的一个快门接着一个快门的丽景……阳光在寒冷的空气中透过山的脊梁,也打不断从贵州威宁草海私奔到彝良县城的洛泽河的忘情歌唱,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被陈衍强的诗歌润泽而更加盛放……来到这里和我的想象没有任何区别,谁也不会在心情愉悦和亢奋之时去关心具体存在的事物,我只感到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诗章,哪怕我不力求急于在那一时刻的表达,经过的房屋越来越多,商店的密集显示着汽车已经驱入县城,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撬开蚌壳一般的山,我们在山里的街道重新放下自己的脚步,衍强带路,我随他之后,不必交代我是不用去医院的了。
一个婉约的女子在街的对面向衍强打着招呼,如果说这县城的每一个美女都把陈衍强当作英雄熟识,我也不会觉得丝毫奇怪,但奇怪的是这个女子好像也在对着我问好。走近一看,原来她就是常常在衍强诗歌和影像里抛头露面的潘群,我们握手,并一边走一边向她诉苦:好不容易到了彝良,结果是以一个病号的方式挂进来的。她说:“没事,年轻人一会儿就好了。”我的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三步两步就到了潘群为我预订好的宾馆房间,卸下包袱,这是一间大房间,窗外就是奔腾不息的洛泽河和岿然矗立的连绵群山。潘群和衍强交谈了两句就先离开了,衍强说要带我一起出去吃饭,吃了饭再回来休息,并且说带我去他家坐坐,我说要得。我用圆规一样的双腿丈量着彝良县城这方寸的土地,过了一条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街,一个左转弯再一个左转弯,就转进了陈衍强家的二楼。上到二楼对直就是他家的门,我随他进了屋,他媳妇也在家,听到我们回来了,就快步走出来,把暖火炉升着,把当地的桔子放到我的面前,让我吃。我在衍强的博客里见到过他的媳妇,可面对面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她比电脑里或一张纸上更加眉清目秀。暖火炉放出的红色爬上墙,将整个堂屋烘得暖洋洋的,衍强和我在沙发上坐着,把手伸出来烤火,我向他倾吐着我的心事和对人生的困惑……一小会儿之后,我们就起身离开了,他带我一起去吃了羊肉米线,很爽。接着他领我到他办公的那间屋子,通过县委大院,绕道一棵深根彝良县城城中心据称700岁的大叶榕树,更上五层楼,最后和关着门的保密局办公室擦肩而过,就到了《彝良文学》的总部。整洁而不大的办公室墙上挂满气喘吁吁的文件袋和一张清新靓丽且放大的“中国作家走彝良”采风活动的合影照,透过办公室的窗便是彝良的群山,置有电脑的正对着山的办公桌上放着衍强今秋十月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和三位美女的合影。离开办公室后我和衍强走到离宾馆不远的岔路口分别,我回笼睡觉,等待衍强傍晚接我出去吃饭。
我被门敲醒的时候还在床上,笼好衣裤一开门,衍强已经到了。一出门还没站稳,一个高挑的美女就立在不远处望着洛泽河飘逝的方向,我不假思索,就用一声问好把代唐仙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来。代唐仙和潘群都一样,既是衍强的同事,又是衍强散打诗里的常客,无法见外。我们穿过一些巷子过了一座桥,就到了衍强预订好吃饭的餐馆。在餐馆里的沙发上我们坐下来等待,因为从和代唐仙与潘群的交谈中,我知道今晚还有更多的客人。没有等候多时,一抹大红就从我眼前悠然掠过,再一看她的眼睛,让我想起了陈衍强写的“你的每一双眼睛,都可以把我活埋成故乡”的诗句,我立刻用我的声音试图把这片飘逸的红停住:“罗姐。”衍强给我介绍她是县文产办的罗月萍,我说我早就知道了。而荷花妙手李珊梅的亲临,就更加烘托出了彝良产美女这个主题的真理。晚餐之前,又有一位豪爽的客人走进门来,衍强介绍,他是苟占东律师。一席丰盛而热气腾天的晚餐,我喜欢的辣味,加上红牛兑的泡酒,畅谈说笑,举杯问盏,三下五除二我就魂魄不知归所,英雄埋单,美女如云,不亦喝乎,不亦悦乎……晚餐尾声,姐妹们给我的碗里盛满天麻,我知道,这是彝良响彻世界的土特产,远方的客人来了就摇身变为最为厚重的礼遇……这次我没有被架着出去。
我们一行说着笑着在衍强的率领下转战卡拉OK,李珊梅送给我的《草原夜色美》让彝良的夜空披上了银辉,衍强中气十足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并不是他唯一的拿手好戏,唱得最悲壮的还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我们在音乐声之下纵情起舞,欢笑声穿插醉过的音符,最响亮的歌曲献给最闪亮的朋友,波浪在勾兑过的啤酒杯中起伏。衍强与我一起劲歌着“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我们在《七月火把节》里把气氛烧到了高潮,手牵着手唱成一个舞动的圈,衍强开启手中的打火机充当火把冲进包围圈,笑声的浪头瞬时把歌声扑灭下去……难忘的今宵我睡得很好。
而《美丽的彝良》和《彝良,我英雄的故乡》这两首歌时时闪现我的梦中,“小草坝回荡着林海的交响,白水江弹奏着飞歌的旋律,姑娘小伙对歌采月,轻柔的月光引领心灵,从古歌的故事里大步走来……”我在洛泽河奔流的声音中醒来。我打开蒙蒙亮的窗帘,河对岸的山上蒸腾着雾气,山间零零落落的树木在放哨,沿岸的房屋里不知还装着多少人的美梦或鼾声。我开始第一次想到我应该近距离地观察彝良,这座曾经在诗歌故事里闪亮的小城,只有在清晨这个时候,我呼吸它的同时,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我抬头望山,那山,就如同一只盘踞的鹰,羽翼已然锋芒,那是一只伺机捕获猎物的鹰,广阔的天地下,这是不是一种城市发展和腾飞的昭示?我浮在想象的天空又身在其中,彝良县城恍然如同一枝打开的睡莲,街道就是花芯,花瓣一瓣一瓣展开,而每绽放一瓣,天上的阳光便照射进来,滋润着城市里的生命,花瓣在正午时分已经怒放,叠成了一脉一脉的山川,静静守候着城市里的人们,看他们下班,放学和休闲,直到月亮也打探不到的夜晚。
我在由洛泽河伴奏的宾馆的大窗里,居然一口气写出我心中彝良的美:“小而灵,深而静,靓而达,动而脱,尊而峙,俊而倔,和而贵,朴而谐……虽为县城,但重山绿野遍布。虽非世外桃源,但胜却人间神域仙境无数。”我无暇看书,在这样的早晨,我更愿意从书本的字里行间里飞出来,在这个诗意的天空里放情地翱翔。“现在来县委会门口,我们等你出去吃饭”,我收到衍强的手机短信,便一拍腿出门了。
午餐安排在县城一间餐馆的二楼,衍强说,是罗月萍招待我。我原以为昨天的分别后,和她只能在牛年马月再相见,没想到昨天的那帮朋友,今天又可以坐在一起。这顿全民投票取消饮酒项目的午餐既丰盛,可口,又简便,席间的风趣和诙谐就是我们最好的下饭菜。衍强说要带我去看罗炳辉将军纪念馆,2点多开门,我说好。然后和几个姐妹又到大叶榕树旁边大楼里的办公室里谈天,上网。代唐仙带我去罗炳辉纪念馆的时候,衍强已在里头等我,我和唐仙经过一座必经之桥的时候,她对我说,这是情人桥,虽然彝良桥比路多,但三江汇合绕双双情侣的桥就是脚下这座桥。走过没有情人的情人桥,爬坡上坎,就看见罗炳辉将军在高处骑着马等我了。走进纪念馆大门,衍强也在那里,迎接我的是底楼墙壁上雄遒苍劲、气贯山河的一幅幅书法作品,譬如对联“将军创伟业,英雄显豪气”,位于底楼正中毛主席1946年写给罗炳辉将军的亲笔信的复制扩印版增添了纪念馆的恢宏与庄重。和衍强到二楼的各个展厅透过塑像,照片,报章,遗物复件等目睹和经历了罗炳辉将军光荣、悲情与壮烈的一生。参观完纪念馆后,我们折返办公室,烤火,聊天,上网,直到晚餐时间。
晚餐在人民广场旁边不远处的一家餐馆进行,又是我爱吃的热火朝天的火锅。令我惊喜的是,这次衍强的家人也来了,他媳妇和他儿子,进来后坐在他旁边。红牛兑的泡酒充当着节目的主角,衍强打趣说待我不周之处多包涵,弄得我说啥都不是,就与他碰杯喝酒,并向他和在场的所有美女发出比火锅还热烈的邀请,请他们到重庆来,到时候我就翻身客人做主人。我放情地喝着,无所顾忌地高声说着,笑着,我们拿出相机,把今后肯定会怀念的一幕一幕咔嚓下来。
那一夜,有太多事难以忘怀。
★下篇
彝良的冬至清晨7点钟的天和人的眼睛还是一样颜色,但街上已经不是安安静静黑灯瞎火。我背着包提着袋打马穿过由陈衍强诗歌的马灯照亮的彝良县城,街的远处在一片人头攒动中释放出和重庆话差不多的本土方言,离我很近的地方,我看见一个人在称秤,另一个人在为秤上的一大把蔬菜讨价还价,由于一条街上紧锣密鼓地站着走着那么多人,我只有走近才能听清楚他们的谈话。早上的风凉啊,但辛勤的人们起得比天还早,他们一定是一两个小时之前就做好了出门的准备,专程赶路到这里来,只为了生计,为了下个月的这个时候过个安心的年!为他们照亮前路的不是老天的光明,而是各自手里一把把在老远老远就闪烁着的电筒,我却不能多看他们一眼,因为我正走向7点10分发往彝良火车站的中巴。
是呵,我要离开彝良了,群山还在雾气中打水洗脸,我不愿离别,但也好过等到天亮的时候,让彝良的朋友来送别。西藏同胞以白色而圣洁的哈达迎接远方到来的客人,彝良兄弟以耐寒而高贵的天麻送别即将远行的友人,我口袋里提着,衍强送我上乘的新鲜野生天麻,以及一盒包装精致的干天麻,我把一大袋的友情与感激放在汽车的行李架上,汽车启程了。
“从彝良县城到火车站坐车要一个小时。”我记得衍强对我说过的话,一路上我可睁开眼睛将这段路程的景色看个够。车没开多大会儿,晨曦就隐隐裱上了洛泽河旁群山的棱角,近处的河水唱出了远处群山的好汉歌,好汉歌一路将汽车追击挤逼到悬崖峭壁的死角,汽车一拐弯抹角,我就见不着你,峰回路转,你再度出现在我的眼前。越来越多的盘山路,由着往前走的车,我透过车窗,总能望见我已走过的路,那曾经是谷底,那曾经是弯道,就像人生一样,但现在已远离了那些路,唯一不变的是,仍然驰骋在自己的道路上,仍然向着最终的目的地进发。路与人生有什么区别,摸不准前路的跌宕起伏,也许又会滑入某段下坡路,无可避免地,还有悬崖上的弯路,也许一路坦荡,也许会遇见什么差错。差错不期而至,我们在半山腰,大概是轮胎爆了一个,车停了下来。好在后面跟上来的一辆大客车,是从彝良去昭通,好心的司机停下车来,经过我们这辆车的司机与售票员和他的交涉,我们被安排上了大客车。坐上还没有启动的大客车,透过车窗,一群去结伴上学的十来岁的山里娃走进了我的眼睛,他们个个生龙活虎,脸上涨着山里娃特有的潮红,厚实又质朴的棉袄裹着他们尚显幼小的身体,他们成群结队,向公路的远方走去。这么荒凉的地方,我猜想,他们的学校一定还很遥远,要走很长一段路,他们天天都重复着这一条路,既寒冷又危险,他们是不是有着梦想,有朝一日离开这个地方,或是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自己的子孙不用再走这么远这么险的路去上学?从领头的那个小男孩的脸上,我看到了希望,因为他稚嫩的脸,热情洋溢的表情上,写着他不怕苦难不惧艰险的精神。而当他们消失在车窗外,大客车也随轰鸣的引擎声上路了。
大客车开了十多分钟,铺架在远处桥梁上的铁轨就出现在我眼前,车停下来,几步路,登上了有冰霜的回家的月台。等待火车的那几分钟,我在月台背后的一个大坝子上,被波澜壮阔的高山吸引,它们有的已经银装素裹,落雪的多少,以存在方位和高低度以示分别,太阳,从雪山的反方向探出头来,“出太阳了,这些雪到中午就全部化完喽!”旁边一位和我在车上认识的彝良小伙手指着大雪山的方向笑说。我望着雪山,萌发出激动而又敬畏的心,然后又把目光拉回到雪山下零落的小屋,以及刚才已被我穿过的脚下的群山,看不见的山路十八弯……我开始回想起刚才我遇见的那群孩子,他们与生俱来的坚毅,又回想起彝良县城的朋友们,从昭通落脚以来结识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的质朴,他们的善良,他们的热情好客,还有他们——那份从石头缝里挤出的孤独,飘动中无法捕捉的梦想——即使穷尽我飞沙走石的诗句,也追不上他们一个谦卑的微笑,我只有在莫大的感动中回归到一个平凡的人,和他们在一起,在彝良的某一个山坳里,方寸的土地上,共同——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任泪水打湿胸襟,让笑声四处飘扬,朝着共往的方向,迎接崭新的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