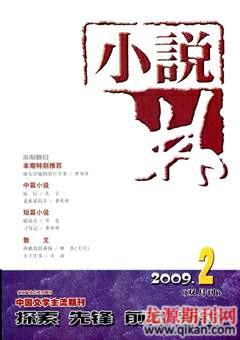乡下往事
王 羽
童年时,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去乡下住一段时间,因为那儿是我的乐园、我的天堂。姥姥家、大姨家、老姨家都住在乡下,她们住在同一个县,分属三个公社的三个自然村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常回忆一些童年时的往事,每当回想起那些乡下往事,总感觉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梦游
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梦游,发生在四十年前,也就是在我不到五岁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住在乡下的姥姥家。
仲夏的夜晚,月亮仿佛是一个银白色的大圆盘,高高地悬挂在夜空中。水银一样的月光倾泻在大地上,东北大平原的黑土地是那么的朦胧而又神秘。在朦胧的月光里,微风中的庄稼变成了墨绿色,姥姥家的三间土坯房变成了深黑色。
白天,我与屯子中的小伙伴疯跑了一天,晚上累得像小死狗一样,躺在姥姥家宽敞的大土炕上,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东北农村的房子,盖建的比较统一,一律坐北朝南。房门多数在房子的中间位置,走进屋子,首先看见的是大大的厨房,进门不远,是左右两个大大的锅台,越过锅台是东西两个屋子的门。宽敞的东西屋里,南北窗遥遥相对,窗下就是东北农村有名的南北大炕。通常,人们睡在朝南的大炕上,因为南炕向阳,北炕基本不住人,只放杂物。相对来说,南炕比北炕要大得多。
东北农村的大土炕历史悠久,好处多多。土炕的第一个好处是保温持久,东北农村每到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人们主要依靠大土炕来抵御严寒。漫长的冬夜,一家老老小小躺在大土炕上,厚厚的土坯将做饭时吸收的热量,慢慢向外释放,热量传递给躺在土炕上的每一个人,这样的热传递一直可以维持到天亮。土炕的另一个好处是冬暖夏凉,夏天人睡在土坯炕上,既凉爽又不得病。俗话说的“花脏钱、睡凉炕,都是作病的事”,这里说的凉炕,是红砖砌的炕,而不是土坯砌的大土炕。
整个夏天,家家户户的南北两个窗子都开着。和煦的夜风从一个窗子轻轻地涌进来,又从另一个窗子悄悄地挤出去。流动的风儿既带走了屋子里的闷热、潮湿,又吹跑了吸血的蚊子。
临睡前,贪吃的我接连吃了几个香甜的大香瓜,睡了不一会儿,我就让尿憋醒了。眼睛涩涩的不愿睁开,迷迷糊糊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接着再睡。我实在不愿意起身,于是翻了一下身,赖在炕上不起来。我不想理睬快要憋不住的尿。
耳边传来姥姥和妈妈的说话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轻、很柔,声音听起来有些飘飘的。姥姥和妈妈的说话声,犹如催眠曲,我经常在她们轻柔的交谈声中入睡。可是,现在我却再也睡不安稳了,不得不爬起来,尽快去解决内急问题,否则就有控制不住的危险。
我迷迷糊糊从炕上爬起来,手扶炕沿,半睁着眼,用脚在地上划拉,磨磨蹭蹭找我的两只鞋。坐在炕头的姥姥,抽着旱烟,关切地问:“小雨呀,干啥呢?”
“尿尿去。”我嘟嘟囔囔地回答。
姥姥要下地,躺在我身边的妈妈说:“妈,不用去了,小雨快五岁了,让他自己去吧。”姥姥不放心地叮嘱道:“别到里面去,里面黑,就在外面尿吧。啊!”
姥姥身材高挑、慈眉善目,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姥姥比一般农村老太太有眼光、有见识、有知识,在艰苦的年代里,姥姥和姥爷坚持供我的几个舅舅和姨妈们上学,让他们成为识文断字的人,为他们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姥姥小的时候,念过几天私塾,她现在还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姥姥还会讲很多故事、出许多谜语,姥姥讲的故事,我常常听得入迷,姥姥出的谜语,我费尽脑筋也猜不出几个。
我答应一声,半闭着眼睛,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外走。姥姥家的屋子,我一天出来进去无数次,闭着眼睛也不会撞到墙上。走出睡觉的东屋,拐过大大的锅台,向前走几步,就到了房门口。姥姥家的茅厕在房子的西边,转过西屋的墙角,向前走十几步就能到地方。
来到茅厕前,我站住了。茅厕里面黑糊糊的,气味难闻。我站在离茅厕几步远的地方,快速解决完问题,马上转身往回走。
夜空如洗,繁星点点,深邃、遥远而又神秘,数不清的小星星在夜空中眨着眼睛,仿佛在讲述着什么。夜空中慢慢飘来一大片墨黑色的云,将月亮遮挡起来,也挡住了月亮周围的很多小星星。这时,屯子里大喇叭播放的《新闻联播》结束了,开始播放雄浑有力的结束曲——《国际歌》。
在《国际歌》声中,我半睁着眼睛,迷迷糊糊径直踏上一条小土路,忘记了拐弯。
小土路的左侧是一堵矮矮的土墙,右侧是农家的菜园子。院子里依次是矮趴趴的茄子和柿子,然后是土豆和包米等植物,我的目标是前面的房子。快走到房子跟前了,大片的云飘走了,月亮露了出来,大地恢复了银灰色。
走到黑洞洞的窗子前,矮矮胖胖的我吃力地从敞开的窗子爬了进去。窗子下面是大土炕,我倒在土炕的炕席上又开始呼呼大睡。
熟睡中,我觉得妈妈将我抱了起来,还与人说着什么。妈妈说:“谭大婶,谢谢你,我走了。”我觉得很奇怪,谭姥姥家在姥姥家的前面,现在已经是晚上了,黑灯瞎火的,妈妈去谭姥姥家干吗?
第二天早晨,姥姥和妈妈一起问我:“昨晚你去谭姥姥家干吗?”我说:“我没去谭姥姥家呀,我在炕上睡觉呢。”妈妈笑着说:“臭小子,尿完尿,你顺着尿道去了谭姥姥家,你是爬人家后窗户进去的。人家发现北炕上突然多了一个大胖小子,吓了一大跳。”姥姥埋怨妈妈道:“我说跟着,你偏不让,多悬,人家要不来告诉一声,你去哪儿找小雨呀。”
我结结巴巴地问:“这……这是咋回事呀?”妈妈说:“这叫梦游,知道吗?”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匆匆忙忙吃完早饭,又出去与小伙伴们一起疯跑了。
偷瓜
农村有句俗话:“歪瓜裂枣,见着就咬。”说的就是夏、秋两季好吃的东西多,孩子们可以大饱口福。一年当
中,这两个季节是孩子们最盼望的,因为这时的孩子们不再为没有零嘴吃而发愁了。家家户户的前后园子、黑土地里随处可以找到好吃的东西,孩子们可以放开肚皮大吃大嚼,肥沃的黑土地,慷慨地向孩子们提供许许多多可以解馋、果腹的好东西。
最好吃的东西当然是香瓜和西瓜,其次是黄瓜和柿子。这几样好吃的东西,摘下来擦擦、洗洗就可以吃,而且各有各的美味,让人百吃不厌。黄瓜和柿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子里都种一些,而香瓜和西瓜则只有生产队才种植。
遗憾的是香瓜和西瓜这两样最好吃的东西,每个生产小队种得都不多,因为香瓜和西瓜终究不是粮食,只是一种奢侈品。为了让孩子们和社员在夏天改善一下口味,每个小队每年不得不种一些。
通常,每个小队都将瓜地选在离屯子很远的地方,这样做有诸多不便,比如分瓜的时候,社员们背着香瓜要走很远才能回到家里,家人给看瓜的人送饭要走很远的路。但是,再不方便,瓜地也选在那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怕屯子里的小玩儿闹们偷瓜。
屯子里大一些的孩子都在上学或是下地干活,这些孩子没有时间偷瓜。不上学、不下地的孩子太小,嘴虽然馋,但不敢独自去遥远的瓜地偷瓜。因为大人们都在地里干活,去瓜地的路上基本没有人,再加上夏季炎热、骄阳似火,小玩儿闹们馋得口水横流也只能忍着。通往瓜地的土路上静悄悄的,只偶尔跑过一两只舌头伸出很长的狗。
与我一起玩儿的小伙伴有五六个,我们一天除了疯跑,就是寻找好吃的东西。初夏的时候,好吃的东西还很少,黄瓜、柿子还只是一朵朵盛开的小花儿,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渐渐的,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最早下来的蔬菜是茄子和辣椒,我们开始大吃起来。吃的时候,我们专找小的摘,小茄子吃起来甜丝丝,嫩嫩的,口感非常好。辣椒我不常吃,因为我分不清哪个辣椒辣,如果咬一口辣的辣椒,要难受很长时间,小伙伴们又吃辣椒又吃茄子,而我非常专一,只吃茄子。
往下摘茄子的时候,一般都是小伙伴们摘下来,然后递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吃现成的。因为小伙伴们都知道,我是哈尔滨来的小孩儿,笨手笨脚不会摘,弄不好会把茄子秧揪坏。
茄子、辣椒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更好吃的食品——黄瓜。于是,我们不再吃茄子、辣椒,一起吃黄瓜了。吃黄瓜是分阶段的,黄瓜刚能吃的时候,我们吃不大不小的黄瓜,时间长了,这样的黄瓜吃腻了,我们开始吃嫩嫩的小黄瓜,最后吃老黄瓜。我现在还记得老黄瓜的滋味,老黄瓜的皮呈老黄色,外表麻麻咧咧,里面的瓜瓤又酸又脆,黄瓜籽滑溜溜的,吃起来别有滋味,只是吃老黄瓜有些麻烦,需要将老黄瓜皮吐出来。当然,我们是在大人许可的情况下,才吃老黄瓜的,因为一些老黄瓜是要留下来做种子的。我们一边吃黄瓜,一边流着口水想香瓜。
一天,我们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商量着去偷瓜。我们这帮小玩儿闹年龄相差不多,只有小泉一个人比我们大两岁,他自然成了我们的领导。小泉领着我们出了屯子,走在乡下的土路上,我们欢快得像一群出窝的小鸡崽,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快到瓜地的时候,小泉对我们说:“一会儿到了瓜地,你们一定要听我的,每人先选好要偷的瓜,然后听我的命令,一起动手。注意,谁也不能把瓜秧扯坏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知道他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因为只有我笨手笨脚,有弄坏瓜秧的可能。
瓜地的一面是乡间土路,其他三面种着大片的土豆,因为土豆秧子矮,里面藏不住大一点的人。我们这帮小玩儿闹长得都不高,在土豆地里只需弯着腰、低着头就可以藏得严严实实。大家在小泉的带领下,偷偷接近了瓜地。来到瓜地和土豆地的结合部,我们都趴下了,一双双小眼睛紧盯着香瓜,馋得喉咙里恨不得伸出一只小巴掌,将又香又甜的香瓜扔进嘴里,大吃大嚼一顿。
看瓜的老头挺勤快,在瓜窝棚里待不了多一会儿,就走出来看看。瓜窝棚旁拴的那只大黄狗始终懒洋洋地趴在那儿不动,只有两只耳朵偶尔摇晃一下。
我第一次偷瓜,紧张得心怦怦乱跳。我早瞄好了目标,那是一个碧绿的大瓜。盯着大瓜,恍惚中我产生了错觉,仿佛我正在香甜地吃它。突然,小泉压低了声音说:“开始行动!”事先大家演练了很多遍,所以动作都挺快。我们冲出土豆地,向选好的目标扑去,将瓜摘下来后,掉头爬进土豆地,然后弯着腰,一溜小跑钻进了包米地。
跑到屯子外,一个个累得浑身大汗,大家坐在树趟子里,开始吃瓜。我偷的大瓜长得太结实了,我抡圆了小拳头,砸了半天,大瓜纹丝未动。大瓜圆溜溜的,没地方下口,眼睁睁看着香瓜,却吃不到嘴里,急得我直想哭。
看到小伙伴们一个个吃得摇头晃脑、甜嘴麻舌,我更加着急。这时,小泉走过来,接过大瓜看了一眼,说:“哎呀,你偷的这个大瓜指定不好吃,还没熟呢。我蒙了,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生瓜?能吗?就数我摘的瓜大。”
“瓜大就能吃吗?”小泉见我不信,拿着大瓜在树上使劲磕了磕,大瓜终于裂开了。我接过大瓜咬了一口,果然涩涩的,还没有黄瓜好吃,只好心痛地将大瓜扔到草棵里。我垂头丧气坐在那儿,不敢看小伙伴们,我怕控制不住,口水流出来。
这时,小泉递过来一个香瓜。香瓜不大,但瓜皮黄嫩嫩的,还没有掰开,就已经闻到香味了。我接过香瓜,擦都没擦,使劲儿咬了一口,真甜、真好吃!我抬头看看小泉,才知道,每个人只摘了一个瓜,而小泉毕竟比我们大两岁,他在极短的时间里,竟然摘了两个瓜。
挨冻
年纪大一些的朋友都能回想起来,七八十年代的哈尔滨,几乎家家住的都是平房,到了冬天,需要自己烧炉子取暖。那个年代,每逢冬天,人们是很遭罪的,因为天太冷,取暖设施太落后。但是我要说,那时在城市居住的人是享福的,乡下农村才真的很冷。
冬天,黑土地上的庄稼被收割一空,东北大平原一览无余,站在广袤的原野上,极目远眺,天与地深远而广阔。冬天的乡村,大雪漫天、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没有遮拦、肆虐的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呼啸着刮在人的脸上,人便有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
社员家家户户的住房都是一样的,窗户和门不像城市是双层的,一律是单层的,门扇、窗扇和门框。窗框咬合得不好,有很大的缝隙。门、窗上的玻璃几乎没有完整的,很多玻璃出现了裂纹,显得摇摇欲坠,为了不让玻璃掉下来,不得不用纸条糊上,勉强维持着玻璃的完整。面对掉角、裂纹的玻璃,谁都没有办法,只好这么着了。俗话说“针鼻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每当刮风的时候,强劲的北风呼啸着从这些缝隙、小洞钻进屋子,发出阵阵怪叫,不仅将屋子里的热气吹散了,还使得屋子里充满了鬼怪式的恐怖。
有些人家有一种原始而有效的取暖设备——火盆。火盆是一种厚厚的大泥盆,口小、肚子大,早晨做完饭,将灶坑里带火、不再冒烟的柴火掏出来,装入大泥盆里压实,然后端到大土炕上。屋子里的人谁要是冻得受不了了,就围着火盆,用一个金属的小火铲,一层一层慢慢将上面的灰拨开,下面的火就露出来了,烤一会儿人就好受一些。
刚过完春节,我又来到姥姥家。虽然数九寒天已经过去,但天气依然很冷。呼啸的北风夹着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天地变得白茫茫混沌一片,道路两旁的电线在凛冽的寒风中发出“吱吱”的尖啸声。北风刮过白茫茫的大地,犹如狂奔的野马一路呼啸着奔向远方。
屋里的温度早已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每次刷干净碗、筷,必须把碗、盘里的一点剩水空干净才行,否则一摞饭碗一会儿就冻在了一起,必须用热水烫一下才能一个个分开。头天晚上放在脚底窗台上茶缸里的水,第二天早晨已经冻得结结实实。厨房里的大水缸不敢注满水,如果水缸里的水太满,水冻结成冰体积变大,会将厚厚的水缸涨裂纹的。
这天,吃完早饭,姥姥手脚麻利地收拾完屋子,然后上炕坐在炕头,一边抽着细细的纸烟,一边与我和老姨唠嗑儿。我不到六岁,老姨二十多岁。因为太冷又漫天飞雪,我不能出去找小伙伴玩,老姨也不用去公社上班,我们在家陪着姥姥,三个人围着火盆坐,一边说话一边烤火。
屋子外面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密,北风越刮越猛,屋子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渐渐的,我和老姨冻得受不了了,我们两个人手脚冰凉地将所有衣服都穿上,然后紧挨着火盆躺在炕上。饶是如此,浑身上下只有挨着火盆的地方有点热乎气,其他地方还是冰凉冰凉。
裸露在外面的鼻子、脸被冻得凉飕飕,鼻子开始往外流淌清鼻涕,屋内的温度似乎到了零下十几度。我和老姨被冻得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可是姥姥依旧坐在那里,慢悠悠地抽着烟、慢悠悠地拨着火盆里面的灰,好像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姥姥家的小花猫看到屋子里唯一的热源——火盆,被几个人围着,它无法靠前取暖,冻得它不得不钻进了灶火坑,因为那里还有最后一点热气。
快到中午了,姥姥开始下地做饭,小花猫从灶火坑里钻出来,浑身上下沾满了灰,变成了小灰猫。带着满身的灰,小花猫跳上炕,紧挨着火盆趴下了。
东北乡下的冬天虽然寒冷无比,但也有许多乐趣。我是正月里的生日,这个时候,小鸡早已不下蛋了,姥姥积攒的鸡蛋也吃完了。按老规矩,过生日必须擀面条、煮鸡蛋吃,于是姥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雨,穿好衣服,带上帽子、手套,姥姥领你找鸡蛋去。”我好奇地问:“姥姥,去哪儿找呀?”姥姥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跟着姥姥走出屋门,走向前院的柴火垛,姥姥指着柴火垛的根部说:“你去那儿找吧,那里面有鸡蛋。”柴火垛的根部早已经被鸡们刨出一个大大的洞,我半信半疑地钻进去,用戴着厚厚棉手套的双手在柴火里乱划拉,果然找到很多鸡蛋。不过鸡蛋冻得像石头蛋一样,一个个硬邦邦的,个别冻裂的鸡蛋淌出的蛋清、蛋黄又将其他鸡蛋粘贴住,七八个鸡蛋就紧紧地冻在一起,变成一个奇形怪状的大鸡蛋。我干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不再感觉冷了。
很快,我从柴火垛里掏出来几十个冻鸡蛋,姥姥用瓦盆端进了屋。过生日时,我不仅吃到了煮鸡蛋,还有一大盘炒鸡蛋,吃的真过瘾!真解馋!
原来,天气越来越冷,小鸡不再进窝下蛋,而是钻进又避风又暖和的柴火洞里,将一年中的最后几个蛋下在了里面。因为姥姥饲养的小鸡多,有三十多只,所以我才能找到那么多冻鸡蛋。
历险
历险是我在大姨家时发生的事,那时我刚刚四岁。大姨家住的房子与姥姥家的房子不一样,姥姥家是那种泥抹的、平顶的房子,而大姨家是那种起脊的、苫盖草辫子的房子,我听大人们说这叫草房。房顶的样子虽然不同,内部的格局、样式还是一样的,只是房子里住的人不同。姥姥家的房子是,姥姥和二舅住在东屋(姥爷去世已经很多年了),西屋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汉;大姨家则是,大姨一家住在东屋,西屋住的是大姨夫的弟弟一家人。
介绍得这样详细,是要引出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大姨夫弟弟的大儿子,他名叫小会。小会与我同岁,但生日比我小。我俩反差挺大,我又高又胖又笨,小会又矮又瘦又灵活;我是“见多识广”的哈尔滨小孩,小会是“孤陋寡闻”的乡下孩子;我长得漂亮,小会长得难看。小会小的时候,不招人喜欢,有些讨人嫌,但是他比我灵巧,比我跑得快,对农村各种玩儿的东西比我知道得多,所以我俩整天形影不离。
大姨夫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大姨是屯子里的妇女主任,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我大姐姐,她在公社卫生院上班。因为大姨一家人的关系,再加上我小的时候招人喜欢,所以一走出大姨家,就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与我说话、给我好吃的。像什么香瓜、沙果、李子、杏什么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不过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将好吃的东西塞给我,却不给小会,不知是因为小会长得难看,还是他讨人嫌。总之,很多人都告诉我,“好吃的不给小会,留着你自己吃,听见没?”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是肚子滚圆,兜里装着没吃完的好东西,趾高气扬地走在前面,小会则流着哈喇子,蔫头耷脑跟在我身后。快到家了,我见周围没有人,掏出兜里的好东西给小会吃,所以每次大人们见到我俩走进院子,小会都在吃东西,肚子却是瘪瘪的,而我没有吃东西,肚子却鼓溜溜的。
这天,我俩吃完早饭又出去玩儿,走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屯子里的水井附近。离水井不太远有一帮小孩在玩儿,我在大姨家住的时间短,不认识那些孩子,所以就独自走到水井边看新奇的井架子,小会跑过去与那帮小孩一起玩儿起来。
看着水井架子和辘轳,我觉得很好奇、很好玩,于是笨手笨脚使出吃奶的劲,顺着辘轳把子爬了上去。骑在辘轳上,我来回摇晃,仿佛骑在高头大马上一样,得意扬扬感觉特别威风。这时,小会因为讨人嫌,玩儿了不一会儿,被那帮小孩揍了出来,他们不跟小会玩儿了。小会讪不搭地到处找我,突然看到我骑在辘轳上,吓得他魂飞天外,一路嚎叫着往家飞跑。
还没跑进院子,小会儿的声音已经传进了屋里,“大娘!大娘!小雨爬到辘轳上去了!大娘!……”
屋里的人都听到了,立刻乱成一团,大姨闻声马上从屋里跑了出来。
大姨那年四十多岁,平时大姨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稳稳当当、有条有理,遇到突发事件或是危急关头,大姨头脑相当冷静,处理突发事件,大姨最有办法,而且办法最有效。
举个小例子就能看出来,有一年深秋,大姨将刚刚出锅的鸡蛋羹端上饭桌,这时小会的爸爸干完活饥肠辘辘回到家里,看到桌上的鸡蛋羹,他马上拿起桌上的一个大勺子,舀了满满一勺,送进嘴里并立刻咽了下去。你想想,滚烫的鸡蛋羹在嘴里、胃里该是什么感觉,肯定是鸡蛋羹到了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烧一样的巨痛。小会的爸爸烫得、痛得满头大汗,浑身发抖,热泪双流,在地上直转圈儿。屋里的人都惊呆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有大姨头脑冷静,她立刻从厨房端来一瓢凉水,命令小会的爸爸一口气喝下去。结果,大姨的沉着、冷静,挽救了小会的爸爸,这个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在瞬间化解了一场灾难。
此时,大姨跑得飞快,将善跑的小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来到水井附近,看到我还坐在辘轳上臭美,远处围了许多人,人们议论纷纷,谁也不敢走上前,都怕将我惊吓得掉到水井里。大姨向众人摆摆手,然后悄悄从后面慢慢靠近我,伸出手将我紧紧抱住后,一下子将我从辘轳上抱了下来。周围的人群一片欢呼,我愣愣地看着大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姨将我抱到井边,指着深深的水井,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看看,多危险呀,要是跌下去,会淹死的。”大姨虽然又气又惊又后怕,但是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而是耐心地向我讲解里面的利害关系。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没感觉有多么危险、多么惊心动魄。
回家的路上,大姨气还没有消,她踢了小会一脚,骂道:“小东西,小雨是市里孩子,不知道水井危险,你还不知道吗?你咋不拦着他呢?”
受了委屈的小会没当回事,跟在我们后面一起回家了。
馋肉
大姨是屯子里的妇女主任,每天都很忙,既要下地参加生产,又要为妇女们的家庭纠纷花费很多时间。通常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量,一般人是很难兼顾各种家务的,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大姨则不然,工作没耽误,家里的各种家务也没耽误,当然大姨是全家人里面最辛苦、最劳累的人,一天的工作量、一天的劳累只有她自己知道。
大姨另一个长处是做饭特别好吃,普普通通的农家饭菜,大姨做出来,味道立刻不一样,特别香!可以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吃大姨做的饭菜是一种享受。因为大姨饭菜做得好吃,所以县里的干部、公社的干部来屯子蹲点、检查工作,都在大姨家吃派饭,干部们吃好了大姨做的饭菜,换别人家,干部们不愿意吃。
那时农村没有大米,细粮只有白面,招待干部们,主食有时是馒头、有时是烙饼,最不济也是白面和包米面的混合干粮,做的菜豆油放的多一些,个别时候还有干豆腐、水豆腐,甚至能吃到肉。这在四十多年前的农村,是相当不容易的。
下来的干部,加上陪同的大队的领导,每次人数都不少,大姨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家务,还要给干部们做饭,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不过,有苦也有乐,每次大姨做的饭菜,干部们吃完,还能剩下一些。
干部们吃完饭,由大队领导——大姨夫陪着去了大队部,家里人开始吃饭。大家吃得特别高兴,像过节一样,大姨挨累,全家人享口福。我在大姨家遇到过几次干部们吃饭,干部们走后,我瞪圆了眼睛,吃得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将肚子吃得滚圆。
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春耕完事了、夏锄也完事了,风调雨顺,屯子里什么事也没有,干部们不再下乡了。不到五岁的我想,干部们现在肯定也想吃大姨做的饭菜,可是没有借口、没有理由,他们没法来,只能像我一样,馋得流口水。
干部们不来了,我就吃不到高标准的伙食了。时间长了,我开始盼望干部们再到大姨家吃饭,可是干部们不知道我的想法,没事不下来。虽然大姨做饭好吃,虽然大姨每天给我单独做干粮,并将做好的干粮放在小筐里,然后将小筐挂在屋子的房梁上,可是我还是想吃干部们的伙食标准。
那时农村每个人的口粮都不多,大姨必须想方设法调剂每顿饭,不能顿顿吃干的,如果那样的话,口粮不可能吃一年,又不能饿着家里的人,所以说做饭劳心费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每天我的任务就是玩,疯跑一天,到了吃饭的时候,看着桌上的饭菜,我立刻想起好多天没吃到豆腐和肉了,仿佛豆腐和肉的香味钻进了鼻子,我立刻就馋了。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想豆腐和肉。
大姨每年都要喂养一口大肥猪,过年的时候,将大肥猪杀了,留一小部分猪肉全家人改善生活,其余的卖给左邻右舍,换一些买油盐的零花钱。养猪是辛苦活,为了让猪长膘,一天要喂好几次,猪长得越大吃得越多,喂猪的人越辛苦。
住在大姨家,我觉得自己和大肥猪差不多,大姨既要为我精心做吃喝,又要喂饱大肥猪,这两件事耗费了大姨很多的精力与时间。
时间越长,我越馋,总想吃肉。于是,每天我都盯着肥头大耳、臭烘烘的大肥猪发呆,闻着猪粪味,想的却是香喷喷的猪肉。一开始,家里的人谁都没注意我的反常举动,时间长了,大姨夫终于发现了问题。
这天,我正盯着大肥猪看,大姨夫走到我身旁,问:“小雨呀,臭烘烘的猪有啥好看的?”我仰着脸看着大姨夫,问:“大姨夫,能把猪屁股割下来一块吗?”大姨夫惊讶地问:“啥?把猪屁股割下一块?猪还能活吗?你要干啥呀?”我说:“我想吃猪肉了。”大姨夫摸着胡子茬,不说话了。说完话,我扭头跑出院子,又出去玩儿了。
跑了大半天,快吃饭的时候,我跑回大姨家。刚进院子,就闻到一股香喷喷的肉味,我立刻连蹦带跳跑进了东屋。果然,饭桌上有一大碗肉,我急急忙忙爬上炕,立刻扑了过去。大姐姐拿过毛巾,拽住我,将我的手、脸擦干净,我坐在饭桌旁,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大姐姐逗我,她问:“小雨,你吃得是什么肉哇?”我将嘴里的肉咽下去,马上又抓起一块,说:“是猪屁股肉!”屋里的人都笑了。
原来,我出去玩儿的时候,大姨夫抓住一只正在下蛋的大母鸡,将辛辛苦苦下蛋的母鸡杀了。大姨将母鸡放进大铁锅里,炖了一个多小时。我吃的不是猪屁股肉,是鸡肉。
作者简介:王禹,笔名王羽,男,1963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原籍辽宁沈阳,大专文化,工程系列工程师,中共党员,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当过七年印刷厂铅排版工人,十余年国家二级企业(塑料加工行业)微机室主任、仓库主任。2002年离职,同年8月开始写作至今。
责任编辑 何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