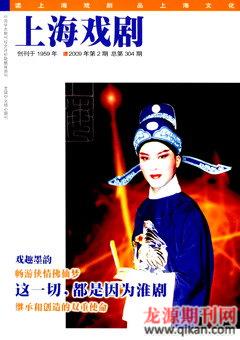生命的重量
刘彦君
在人们心目中,周瑜就像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一样,早已超越了对那个三国历史年代人和事的追忆,而上升为一种理念、一种情怀或是一种性格。当以这样的理念、情怀和性格观赏义乌婺剧团新编历史故事剧《赤壁周郎》时,我们再一次试图回到那个年代的情境中去,重温周瑜这位东吴都督因气量狭小、嫉贤妒能而造成的人生悲剧。
但我们失望了,同时却又倍感欣慰,因为创作者笔下的周瑜,远离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不自觉地运用“典型”方法塑造出的那个气量狭隘的周瑜,远离了近千年来戏曲舞台上演绎的那个嫉贤妒能的周瑜。《赤壁周郎》中的周瑜,成了一个不断以善念和良知战胜自身性格弱点的周瑜,一个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渴望以英雄自律的周瑜。这是创作者对周瑜形象所做的最大改变。这个形象似与陈寿《三国志》中的周瑜有些接近,与苏东坡笔下那个“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也有几分相像。更重要的是,这个形象传递了我们现代人对于人的观念和理想。这是一个有着生命重量的、令当今观众能够也愿意理解的新形象。
崭新的视角赋予这一老故事以新的立意。这种视角没有停留在道德层面,人们无法用忠孝节义来解释周瑜的行为,也无法用是非、对错来判断他与诸葛亮之间的较量。全剧甚至没有把他们各自放到一个群体中去衡量其贡献的大小,就像时下许多剧作塑造英雄时常做的那样。
该剧也不是以恢复历史原貌为目的。在情节的铺展中,虽依然有“蒋干盗书”、“借刀杀人”、“草船借箭”、“借东风”等经典片段,但这些片段并非为了表达历史的进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它们或被推到幕后,或被压缩为过场,成为瑜亮二人智慧和胸怀展示的背景。而周瑜“礼送诸葛亮回夏口”作为本剧的核心内容,也被纳入了周瑜情感和心性变化、发展的生命轨道。
通过在崭新视角下演绎的这个故事和这一形象,创作者确立的是一种人的视角,展示的是一种阳光、积极的人生境界。作品试图通过开掘周瑜身上的善念与人格精神,来传扬一种乐观处世的英雄式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形态,让它像灯火一样带给人们光明和温暖,引导人们向善、向美。这种立意,标志着该剧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就艺术而言,目前的历史剧创作不缺历史角度,不缺道德角度,缺的恰恰是从历史到人、从道德到人的这一角度。
这一个周瑜让我们感到陌生。尽管他争强好胜、嫉贤妒能的心理以及狭小的气度在舞台上也有所展现,但全剧强调的却是他与诸葛亮之间的英雄情结和作为“知音良伴”的情感纠葛,强调的是周瑜对自身高大形象的看重和刻意打造。在作者笔下,二人初识时惺惺相惜,在看似寒暄的客套中隐隐透出真心;小乔“有诸葛先生相助,夫君如虎添翼”的期待,也将周瑜的潜意识转化成显意识,准确地道出了二人能够对话与合作的现实基础。在这里,小乔的生命形态与周瑜是互为补充的。她是周瑜的一个陪衬、影子,是他自我的一个方面,也是他内心意识的一个外化。
正因有了这样的铺垫,导致周瑜在几次刁难、欲杀诸葛亮时犹豫再三。此外,周瑜还有精神层面的顾忌。“莩船借箭”之后,争强好胜的周瑜因未能提前识破诸葛亮的计谋而顿起杀心,但最终还是罢手了事。“不费我东吴一分钱粮,平白得了十万支雕翎”以及“杀诸葛逼刘备投向曹营,助曹操灭东吴大祸旋生”等等,当然是能说得出的原因,那说不出的还有他潜意识中以英雄自许的自我定位。他对自己的公众印象是很在意的,他不能在世人面前暴露龌龊的心胸,破坏他的高大形象。
诸葛亮正是看准并把握了这一点,才敢于在借瑶琴提醒他君子之盟的前提下去借东风。大功告成之后,已登上山下滩口芦苇荡中小船的诸葛亮引而不发,坐待其变,直至用琴声唤醒了周瑜身上的热血英豪之气,使他演出了一场“礼送诸葛亮”返回夏口的好戏。周瑜对诸葛亮从猜忌、较量,到拜托、求助,再到“待来日还君春风一百年”的应承,其间情感脉络变化推进的轨迹清晰可贝。
通过这种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创作者想告诉观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斗争、消灭和对抗,还有对话、理解、合作的可能,即使是持不同理想、抱负甚至不同见解的那些人们。胸襟狭窄如周瑜这样一位早被历史和舞台定型了的古代人物,尚有羞愧和转变的英雄之举,更何况其他人、更何况现代人!这样的观念激活了整个创作,建立了一种可以穿通各种境界的思想和行为逻辑,从而打破了多年来周瑜形象塑造中的模式化倾向。
该剧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创作者对周瑜内心世界的建构方式。整个舞台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就是周瑜和他自己。对这位权倾一时的大都督来说,杀诸葛亮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从不制造任何杀诸葛亮的理由——杀诸葛亮是一般人的认识,不是周瑜的认识。周瑜在行动时,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这是剧本的深刻之处。周瑜要面对的是自己,他的犹豫来自对自身完美形象的一种期待、设计和实现。
前面几场戏中,周瑜之所以不敢痛下杀手是出于利害和权宜的考虑:“本以为世无敌万里河山任我驰骋,今方识山外山还有个孔明!他他他计高一筹占我上风!留得诸葛卧龙在,东吴周郎难安宁!欲杀诸葛除后患,强敌曹操逞狂凶!手按宝剑心难定,何时出鞘亮青锋?”但创作者并没有按这样的思路赋予周瑜为国家利益而放弃个人恩怨的形象内涵——那将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英雄塑造模式。
戏剧情境按照新的构思向前推进。当东风已起、两家联手胜利在望之时,杀诸葛亮已成为东吴官兵的共识。张昭明确指出:“孙刘两家,破曹是友,曹破是敌。东风既起,破曹在即!今夜已是变友为敌,必须即刻除掉诸葛亮!”不仅如此,甚至主公孙权也传出口谕“诸葛亮小船驶出滩口,弓弩手乱箭射杀!”然而,周瑜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他顶着来自上下的压力,仗着“凡军阵之事,瑜皆可自决之”的特权喝令:“所有伏兵放下弓弩,礼送诸葛亮先生归去!”
可贵的是,这种选择不是从历史的角度,也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从人性价值的角度,是从信守承诺、自我形象完善的角度作出的。历史判断建立在功罪的基础上,道德判断建立在利害的基础上,而周瑜的选择则建立在人的生命本体基础之上,这是创作者对这一形象最为成功的发掘。以此为轴心,剧作叙述焦点向审美回归,回归到了人的自身,回归到了周瑜对自我形象的定位上——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到底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在该剧中,周瑜的自我世界是被放大了的,如果说他在外在世界中是个成功者的话,那么他在内心世界的自我感觉中却是个弱者。面对诸葛亮的豁达、谦和、不卑不亢,他显得那样促狭、狂妄、焦虑不安。他见不得别人的成功,见不得别人的智慧高出于自己之上……他不满意自己的这一形象,他期待着以另一个形象(起码是与诸葛亮相当的形象)来寻求外在的确认,当然,首先得由自己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自我挑战的过程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忍受折磨和痛苦。创作者直逼人物的内心现场,将周瑜对自己一次次的说服、推翻、再说服的过程反反复复地呈现在舞台上,将周瑜内心的挣扎、摇摆和煎熬一层层地揭示出来。这种带有解剖、忏悔因素的心理体验,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品位,且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而丰满。也许,人类最难战胜的就是自身吧。因而,当周瑜从那种酸楚、嫉恨等情感的失控状态中走出,当他重新回复理性、通达、高贵的气质,特别是当他按照心目中那个英雄形象来拿捏自己,按他所希望、所设计的那个重情谊、重然诺的样子去实现自己时,观众不得不由衷地竖起大拇指来!
博大、睿智、重然诺、重情谊……作为一种历来公认的人性美德,在任何时候都是衡量生命轻重的秤砣。它为“这一个”周瑜增加了生命的重量,使每个现代观众都能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因而产生强烈的呼应和共鸣。
作为一位女小生,性别的差异增加了楼巧珠塑造周瑜这一形象的难度。她知难而进,真诚地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去体验角色的喜怒哀乐,去揣摩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征,与导演一起为周瑜精心设计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舞台造型、音乐唱腔和身段动作等,使之脱离脸谱化、程式化的单薄与刻板,代之以形神兼备的丰满与鲜活。同时,楼巧珠在深入挖掘婺剧传统表演程式和技巧的基础上,还从其他剧种借鉴了一些表现方法,尝试用新的艺术语汇和艺术元素探索、丰富这一角色的精神风貌——“耍翎子”的特技,就是她驱车数千里,专程从山西梆子剧团学来的。
《赤壁周郎》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人物的内心世界却异常丰富;人物之间的外在关系比较单纯,而人物的心理冲突却十分激烈。尤其是周瑜性格中本身具备的那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多变面孔,成为考验演员内心是否充实的“功夫戏”。楼巧珠根据戏剧情境设置和人物情感的要求,对起、坐、转、跪、走、跑等表演身段进行精心提炼,层次分明地再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对这一角色的塑造作出了突出贡献。楼巧珠还设计了周瑜在与人物交流时心里一套、嘴上一套的多重听觉和视觉形象,如周瑜在得知诸葛亮识破他的“借刀杀人”之计,特别是听到鲁肃钦佩不已地赞叹:“啊呀呀,诸葛先生料事如神,成竹在胸,天下无人可及也!”后,有几个“啊?…‘啊?”“啊!”的笑声。这种既有恼怒、又有掩饰、更有尴尬,假中有真的复杂状态是很难把握的,但楼巧珠通过声调高低的调整和面部表情的变化,准确地表达了人物隐秘而丰富的内心景象。
周瑜的转变之多、之快、之陡,最鲜明地集中于全剧最后一场。它考验着演员对表演分寸的把握,它将所谓“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的衡量标准,从对演员评价的各种度量衡中高高举了起来,形成一个考验演员全方位能力的巨大问号。楼巧珠举重若轻、不动声色地将人物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各种“潜台词”准确、生动、恰到好处地外化出来,将人物的性格、情感、心理的变化组合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有机格局,从而展现了把握作品、人物、技巧的多方面才能。
东风起时,周瑜对诸葛亮的佩服脱口而出:“诸葛亮他真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这时,楼巧珠对语气节奏的处理是平缓而由衷的,面对主公要自己务必杀死诸葛亮的命令,他执意不肯“曹军未破,诸葛无错,叫我如何行此背友之事?”然而,当诸葛亮真的不见了时,他又怒不可遏:“啊!你、你、你们为何竟让他走失?”并下了“随我速去南屏山!”的命令。这时,楼巧珠的语速明显加快,急切中凸显了周瑜性格中小鸡肚肠的一面。接着,在“放行”还是“射杀”的选择使周瑜“心发虚、手发软、张口好难”的一大段戏里,他的羞愧、他的狭隘,以及他最终风发意气的每一个变化,都与楼巧珠欠身、迈步、转体等动作以及眼神、表情、语气刚柔缓急的节奏一一对应,且没有露出停顿或起始的蛛丝马迹。楼巧珠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的精彩表演,为周瑜这一形象的厚重增添了神采和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