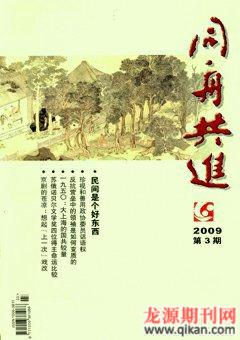京剧的苍凉
施京吾
祖父是戏迷,尤迷杨派,擅唱《洪羊洞》、《文昭关》,一直唱到90多岁,实在唱不动了才住口。父亲也是戏迷,可惜嗓音条件差了些,所以以品戏为主。我在襁褓中就开始听戏,听了近30年,听到亲戚们各立门户,听到祖父不再唱。我生在“文革”前夜,等能跟着大人哼哼的时候只剩下八个样板戏。父亲喜欢京剧,也教我唱。他拉琴,我就装模作样要么“朔风吹,林涛吼”,要么“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可唱来唱去就那几个段子,时间一长,没了耐心。
如今,我也年过四十,除了偶尔陪父亲看看电视上的演出,基本与京剧绝缘了,但京剧的事情我还关注着。
读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书的副标题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不过我觉得,读起来最有意思的是我这样的“半吊子”,大多数术语不用解释就知道,许多剧目都有耳闻,对书里八位传主觉得很熟悉,离得并不远。
印象中曾问过一次祖父为什么不唱新戏,他一捋山羊胡子,呵呵一笑:那是年轻人玩的。似乎有些鄙夷。父亲则是古今兼达,很少臧否,但更喜欢新戏,觉得老戏的程式老了,不太适应现代生活。我也觉得现代剧目比传统剧目好,但只是感觉,不是喜欢,因为新戏容易听懂。
那时年龄小,闹不清“文革”的“伟大意义”,也不知道演员是分“派”的。看了电影《沙家浜》,回家一问,扮演郭建光的是谭元寿,叫谭派;那个最坏的刁德一是马长礼扮演的,都说他是马连良的侄子(实际是1954年马连良收马长礼为义子,而马长礼入的是谭门)。于是,又知道了马派——当然,不知道的是他在批判自己义父时又是那样的义正词严。
“文革”结束不久,样板戏的声音一下全没了,收音机里开始播放传统戏。传统戏以前从没听过,道白听不懂,就听播音员报这个戏是谁唱的,那个戏是谁唱的,后来放学路上听见广播里报奚啸伯的《白帝城》,没听说过呀,回家问,父亲“哦”了一声:“奚啸伯的戏也让唱了。”这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四大须生之一。
中国式的吊诡在于,历史总处于一种无常的反复中,哪怕是刚刚经历过的,很快就能重新来过一遍。如同言慧珠、马连良、奚啸伯们从传统京剧舞台上依次消失一样,浩亮(钱浩梁)、杨春霞、童祥苓们也“嗖”地一下从样板戏舞台上集体消失,正应了那句老话:你方唱罢我登场。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以演员接受审查为过程,以消磨掉最好的艺术年华为代价……一切都是那样熟悉,那样具有鲜明特色。好在这一次没再走向极端,现在,样板戏不仅被传唱,甚至还被奉为“红色经典”,这固然是一次进步,只是进步的速度和代价严重不成比例。而这里我要说的是“上一次”,是言慧珠、马连良、奚啸伯们经历的那一次。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资料渐渐多起来,一看,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没一个活着。怎么就都不在了?呀,竟然有一半死于“文革”期间:马连良、荀慧生、尚小云、奚啸伯,当然还有以外的裘盛戎、麒麟童(周信芳)、叶盛兰等。那时的文章经常说他们在“文革”中如何受到残酷迫害,死的又是如何地凄惨,套用一下章诒和的书写风格:宣布他们罪状的时候斩钉截铁,为他们平反的时候掷地有声,横竖都是道理。
中国京剧是在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京剧的起源以徽班进京为标志,至今约220年,比起其他的传统艺术门类,历史要短得多。京剧的荣耀无非就是到宫里为慈禧庆祝一番生日,或者被哪个达官贵人请去唱堂会。那时的政府很少关心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的戏班、科班都是艺人自己组织,完全私人化、自生自灭的。因此,京剧繁荣依靠的唯一途径就是剧场和观众,竞争十分激烈。残酷的竞争之余,也有些好处:政府既然不关心京剧的成长,也就不会去干涉。因此,尽管京剧剧目鱼龙混杂,京剧艺术却在短短百余年间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进入上世纪30年代,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以及叶盛兰、裘盛戎、周信芳等艺术家开创的各大流派使京剧艺术迈上了巅峰。
从《伶人往事》的描写中不难看出,艺术家为了京剧的发扬光大可谓呕心沥血。那时的人不懂得用现代发声原理来解释发声技巧,先靠师傅手把手言传身教,往后全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和悟性,尽管艰难,却符合艺术的一般规律:越是个人的,便越是艺术的。梅兰芳为梅派艺术宗师,就是因为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梅派弟子何止万千,但如果走不出自己的道路,就不可能超越梅兰芳。程砚秋也学过梅派,走的却是自己的路。程派创立之后,他的代表剧目只能由他或他的弟子来演,不论是《锁麟囊》还是《荒山泪》,即便换成梅兰芳亲自出演,都不是那样的效果。同一个剧目由不同的演员演出,效果不一样、感受也不同,京剧的妖娆和迷人之处也就在这里。
建国后,京剧进入组织化程序,原生态被打破。在京剧中加入一定的政府力量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是否尊重艺术的规律。人为地割裂艺术纽带,结果可想而知,恰恰,这正是当时京剧面临的状况。这个过程以组织介入为发端,以“戏改”为口号,以样板戏为标志,以失去观众、京剧没落为结果,而其中尤为令人叹息的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内行领导内行。
比方“革命样板戏”,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却被许多戏迷叫好?原因正在于它们是内行领导内行的结果,不仅江青不是艺术的外行,那些样板戏的主要扮演者谁不是个顶个的“角儿”?而且,不论是否叫“样板戏”,只要还是京剧,就不可能彻底摆脱京剧的特征,这是由京剧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比如,演杨子荣、李勇奇的只能是童祥苓、施正泉;演郭建光、阿庆嫂的只能是谭元寿、洪雪飞;演李玉和、李铁梅的只能是浩亮、刘长瑜。换了谁感觉都不对(当然也有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不仅听的感觉不对,连扮相的感觉都不对。
曾经看过一些讨论上世纪50年代“戏改”的文章,说京剧在那时就产生了一定的危机,认为京剧改革是必然的。确实,随着西方文化和现代艺术的进入,艺术形式多样性已经呈现,但具体到实际情况,那时的京剧还没有到非改不可、一改到位的地步。上世纪50年代初正是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当红的时候,他们不断推出新剧目,观众连“捧角儿”还来不及,怎么就突然面临危机了?京剧危机的产生在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要改变它的方向,当它被扭转到连流派的创始人都无戏可演的地步时,危机就是必然的了。看了章诒和的书,才真正明白京剧危机的由来:那是巅峰状态的突然摔落。比如程派的创始人程砚秋,规定他只能演“宣传和平”的《荒山泪》而不能演“阶级调和”的《锁麟囊》。
“戏改”的极致是“样板戏”的出现。它使京剧的空间变得极为逼仄,除了在内容上大搞“树样板”、“三突出”以外,在音乐上规定只许用一个特性音调,有时把音乐处理得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越到后期的作品情况越严重,像《龙江颂》里江水英的一大段二黄导板和另一段反二黄慢板,那真叫好听,可难度也相当大,结果几乎没几个人能把这两段唱周正了。具体到剧目上,可能每个样板戏都是成功的,但最大的危害却在于斩断了京剧艺术与观众的联系,把一门艺术变成孤零零的与京剧历史毫无关联的剧目。而改造者的手段则比京剧艺术更加“艺术”,所有艺术大师的光辉在“革命”改造的手段面前无不黯然失色。艺术只能由“政治”来选择,从内容到形式必须彻底“革命化”,每一个身段、每一个台步都需要具有革命性和阶级意识……这样的事举世罕见。
尽管艺术家们并不懂得革命的深刻涵义,但还是努力地向革命道路上靠拢。不论言慧珠还是马连良,在“革命样板戏”的演出态度上是极其端正的:既然老戏不让演,那就在革命的新戏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吧,哪怕是跑跑龙套。可是封建社会舞台上的帝王将相能摇身一变为无产阶级舞台上的“革命龙套”吗?在一个连血管里都要流淌着百分之百纯洁的无产阶级血液的年代,答案只有一个:不能。于是,我们看见了尚小云的倾家荡产,看见了言慧珠悬挂的尸身,看见了叶盛兰痛苦的凋零,看见了奚啸伯绝望中的离世,看见了马连良在凌辱中气绝而亡,看见了病榻上的程砚秋对自己剧目的凄苦期待。大师巨匠们所繁荣的京剧艺术却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成为绝响。
《伶人往事》实在是一种智者的书写,没有郑重其事的悼念,没有期期艾艾的悲伤,但每翻过一页,都令人为伶人们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哀伤。那种海报一出、万人空巷的壮观景象,那种大幕未开、呼啸一片的激动场景再也看不见了。演员在心灵上离开了京剧,京剧在舞台上远离了观众。
与真正不看戏的相比,笔者对京剧算略略知道一些。但知道京剧的渊源,知道剧目的变迁,知道演员的生平并不等于真正懂得了京剧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艺术家的风骨、气度、才情。我们看的只是角色,看不见角色后面的那个人。穿上行头不等于拥有了传统。传统是一种传承、一种生活,当失去这样的传承、失去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传统。传统的丢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丢失了传统中最美好、最优秀的那一部分。
京剧作为舞台艺术,我们看惯的是别人的命运,而京剧自身的命运竟也如此悲哀曲折。每翻过书本一页,都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为章诒和书写的那些人和事,也为京剧的悲凉命运。
写到此,夜已深,耳边仿佛飘荡着《文昭关》:“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苍凉、哀婉,天空中飘荡着几缕难以言传的感伤。
——评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