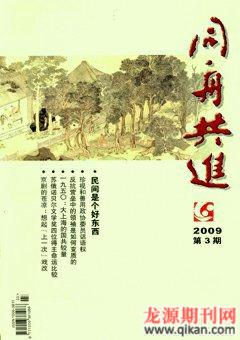立足民间并非权宜之计
作者简介民间学者,曾任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1988年“下海”创办民间研究机构。改革之初曾有受人瞩目的“三驾马车”,他以力促我国第一部破产法出台而名列其中——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曹破产(曹思源)。近年来又被称为“曹宪政”。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时,在《财贸经济》丛刊首次发文倡导制订企业破产法。1982年毕业,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工作,其间曾主持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一波三折后,我国第一部破产法终于在1986年12月2日震撼出台,鄙人头上赚得一顶“高帽子”,曰“曹破产”。正当许多朋友为破产法问世纷纷向我贺喜之时,我却于1988年从国务院机关辞职下海,搞起了民办研究机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
当时一些朋友很不理解:“你在国家机关刚露头角,发展潜力很大,为什么突然辞官不做了呢?”我能说什么?正如《诗经》所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之所忧,乃是政治体制改革。此忧从10年浩劫开始,那时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头百姓,都保证不了自己的生命与尊严;全国人心思定,却动乱频仍;直待“文革”结束,国家才趋于安定。反复思索中,我陆续写过一些文章,譬如1981年以来就多次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破产法立法完成之后,我在一些报纸、杂志、电视台提出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人代会旁听制度以及选准政改突破口等建议。
这些建议曾引起很大反响,但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机关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曹思源,你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到处发表,虽然是个人署名,但人家都知道你是国家体改委的干部,纷纷推测是我们国家体改委的主张,造成很坏影响!”
这种冲突越来越严重,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人要急国家之所急,做推动政改的工作,恰恰不宜坐在国家机关里。上哪儿去呢?四顾茫茫,终于发现有个好去处——重回民间。于是我站在中南海纵身一跳——下海,办起了民间思想库。那时还不知道国际上对此有个专用名词——NGO——非官方机构。
有人说,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怎么能由民间推进呢?我说,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几经反复,才能有效推进。
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从似乎是“天衣无缝”的旧体制中发现问题、找出症结、探索规律、提出改革的思路与操作方案,这些都只能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反复的调研,在逐步成熟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决策,再贯彻执行,而不能简单地自上而下,以上层决策为全过程的起始点。体制改革形成决策之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尤其需要思想敏锐与思想勇气,这恰恰是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的优势。官方机构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影响,难免有看眼色做研究之虑——因此二者的效率往往大相径庭。
关于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的问题,我自1988年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呼吁,并年复一年进行院外活动,通过人民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每年都失败了,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在失败的同时,每年都有所进展。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终于写上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像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革,固然是全国人大的工作成就,同时,它难道不是中国民间力量16年不懈推动的结果吗?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是靠国家财政拨款供养的官方研究院(或研究所,下同);第二类是由民间自筹资金运转的民间研究院。我国目前第一类是主力军,第二类是辅助力量。但从世界各国发展趋势看,第二类才是主力军,第一类则是辅助力量。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将来也必然以民间研究院为主力。
从更大范围说,国家的主权属于谁?属于人民。我国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这里的“各种途径和形式”,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间接的,即通过公仆去行使公民的权力;另一种是公民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投票选举、进行政策研究,集会、结社、出版、发表自己的意见等。
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公仆代表公民行使间接民权,却忘记了作为主人的公民还有大量无须别人代表的直接民权。某些地方机关突出仆人,却淡化主人,岂非笑话。只要把本末倒置的关系顺过来,就不难理解:在改革的推进中,必须立足于民间。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共和国的根本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