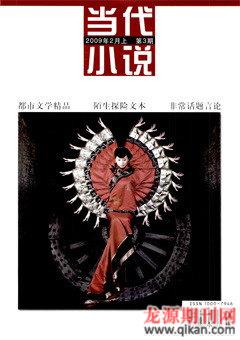游戏逻辑背后的生存话语
巫 丹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绵密而温存的笔触书写她对人与周围环境的别样体验。如“三恋”中情感的决绝,《长恨歌》中上海的人世繁华后的苍凉,《富萍》中“社会边缘状态的世俗日常生活”下移民的生存意志等等,无不包含着作者创作进程中从未中止的对人生存困惑的书写与思考。《遍地枭雄》延续了王安忆对人的生存际遇的关注,将人物置于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社会命题中进行反思,作者巧妙地用一种游戏逻辑将人物“从常态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并在这个“异样的境地”里展开了带有张力的人物生存审视。
在《小说家的十三堂课》的第一堂课“小说的定义”中,王安忆很推崇纳布科夫对小说的定义“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李洁非在《王安忆的新神话》中的评价也得到了王安忆的认可,李洁非解释了神话的本质——“实际上乃是对于自然、现实、先验的逻辑的反叛”,“它拒绝接受这种生而被给予的真实”,这是反自然、反现实的。好的小说是作家独特的“心灵世界”,它有着自身故事发展所要求的逻辑。在《遍地枭雄》这部小说中,作者独特的心灵世界通过游戏逻辑得以阐释,游戏逻辑可以说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条线索,游戏逻辑背后原有生存话语的式微。当然,游戏在消极、回避生存现状的同时,也有着游戏主体对生存的另类的建构。
一、游戏的开始
《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游戏”词条有以下几种解释:①游乐嬉戏、玩耍;②犹戏谑,也指不郑重、不严肃;③文娱活动的一种。分智力游戏(如拼七巧板、猜灯谜,玩魔方)、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抛手绢、跳橡皮筋)等几种。由此可见游戏是作为人生存的一种非正式的消遣休闲的活动。一种逻辑训练,是游戏主体为调节生存压力的有益需要。
在小说的前四节中,游戏逻辑在宁谧的乡村环境中隐现地展开,人与事都有触手可及的历史现场感,也是当下城郊乡村生活的写实。一般说来。乡村生活蕴含的“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漫流的自由的状态”,历来是作家倾心的着力点,正是这种状态给作家提供了多样的思考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第三世界文化对自身文明的焦虑和对西方文明与价值的失望与困惑”:对民族国家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目标诉求和价值指向产生的困惑与焦虑。
这一部分,作者以内敛的话语方式,温情的包容,赋予文字背后隐在的张力,书写着乡村到城市分娩中出现的阵痛,以及乡村中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表层结构上,韩燕来所在村庄的人们,虽然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冲击最大的城郊地带,生活空间却是闭塞,他们不为身边建筑物垃圾淹没的农田、陌生的机器轰鸣声所动,沉浸在自我的日常生存游戏中。深度结构里,那种放低期望的生存话语隐忍地解构着人对遥远的理性价值诉求,以及人在游戏中生存意义的式微。
隐现的游戏逻辑在小说中表现在,儿时韩燕来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村界上与邻村孩子的争夺地盘,以及后来韩燕来与服装厂的工友向齐老板讨要工钱等,以至其后赋闲在家打麻将,都是一种游戏的态度,“反正他(韩燕来)也没事,跟着跑跑还能看热闹。”游戏是自主、自愿的活动。无事可做的人们选择用游戏对抗时间的流逝。在这一部分的乡村生活中多次提到打麻将的情节。这里打麻将不同于赌博。后者已经不能算作游戏。乡民在土地被征用。失去耕作的空间,时间也因此被无事可做的无聊拉长,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就用于成人游戏——打麻将中,因“向来是土里刨吃的生计,便不会冒投机的险,赌注就下得很小”,“只是消遣”。这里的打麻将作为游戏,并不因为有利可图而游戏,其真正的乐趣在于“赢”,而并不在于赢钱。
在游戏进行的背后,展现着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给乡民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游戏取代劳作。人不再恪守传统的农耕方式,不再为经济收入而奔波,甘于现状,也不愿融入上海这个城市中,缩在自己的乡村的壳里,在自己的空间中游戏,时间的固有意义被取消。人生存的终极主题隐去。人在这里不再是启蒙话语下抽象的人,而是生活着的真实的日常状态的“小写的人”,精神理想在此搁置。价值论维度在此中止,人的欲望就是活在当下,活在时间的流动中,活在游戏的消解中。
二、游戏的深入
读者的阅读经验从小说的第五节受到挑战,期待视野的转折是很明显的。线性的游戏逻辑得以延续,并超越,此时的游戏话语已无处不在。人物与环境都充满陌生感和不可知性。从人物语言逻辑的训练,到传奇般的游侠经历。都如“镜花缘”似的,一切都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看似不无目的的游戏之中。
在这一新游戏中,韩燕来在圣诞夜的出租车被劫一事,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突变,韩燕来被三个劫匪集体游戏的魅力深深吸引,由受害者转变为劫匪,一起开始逃亡生涯。其后作者采用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形式将人物命运勾连起来,逃亡经历本身就是一场游戏,被劫人与劫车人由矛盾的对立关系,转化成一条战线的匪徒,并且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在逃亡生涯中,他们面对的无尽的困惑与焦虑,称王称霸的遥远的目标指向无法满足当下生存的需要,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大王在一年的逃亡生涯中,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领导着三个小“枭雄”闯荡江湖。在这个小集团中,流亡生活时时处处地潜于游戏。他们用游戏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大王通过游戏训练逻辑。有词、成语、事三个阶段从初级到高级的语言“接龙”课程,反逻辑的新的扑克牌玩法,说命题作文等等,培养三个小“枭雄”的应变能力,提高团体“作战能力”(偷车)。谷鲁斯认为“……小猫戏抓纸团是练习捕鼠,女孩戏喂木偶是练习做母亲,男孩戏打仗是练习战斗本领。所以游戏就是学习。”由此可见,大王创制的游戏训练法是在看似他漫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游戏”背后,有着深层的功利性。游戏在非功利性的表面下,是为了提高小集团的作战水平。为以后的介入社会,称王称霸做准备。
尽管游戏是一种非正式的活动,但参与游戏的主体态度通常是非常严肃的,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游戏之中的。对待游戏的严肃性远超过对待现实生活,“凡是现实里的严肃问题,他们都抱有着轻松戏谑的态度,相反,凡是游戏玩耍,他们都是郑重其事。来不得半点含糊。”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哲学,在游戏的非现实世界里,淡忘现实矛盾与困惑,缩在游戏的壳里。
这种非常态的生活,正是作者创作的着力所在,异样的生存状态为审视人生存的焦虑与困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话语场域。作为对当下个人生存审视的一组符码,作者将人物置于只有代号没有名字的一个小集团中。可以说,游戏是贯穿整部小说的线索,并推进情节发展,但显然。这一线性的游戏逻辑背后有着更重要的维度来勾连故事的行进,那就是原有生存话语的
式微。
三、游戏逻辑背后的消解意识
《遍地枭雄》的游戏逻辑背后有着作者对生存的思考,以及对经济建设的现代性反思。作者借助于游戏的话语形式,通过对城乡、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表现其对现代化的两重性思考,可以看出。王安忆在这里对所谓现代性表现出远非简单的赞赏或批判的极端话语。游戏只是故事的外壳,壳里的内容才是作家的“所思所想所要表达的”。也正是当下生存话语的一种阐释。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同时,农村向城市蜕变的过程中有着分娩的疼痛,这种疼痛就隐藏在游戏故事的壳里。
从历史目的论看,城市化进程得以成功的进行,就现代性来说。这是一种合理性必然欲求,但这一过程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价值诉求的深度改变为代价,致使人尚未能够及时适应社会的转变,一味沉入游戏中,理想目标消解在空洞的时间流逝中,这是一种更为深层的精神无依与城乡焦虑。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更为明显的贫富分化,城市化进程给世人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尤其是在进程中被边缘化的诸如“三王”一类的人。可以说这几个“枭雄”都属于社会的底层群体,物质基础是匮乏的,精神世界处于迷茫。大王是其中的精神领袖。他的理想价值指向是称王称霸,现实并未给予他相应的受教育机会,初中毕业后。从乡村走入部队。希望改变生存境遇。却又回归乡村。再次从乡村的出走,对他来说。意味着反抗与冒险,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仍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壁垒,不得已走向了劫车的犯罪之路。用“枭雄”指认底层带有反抗的姿态。
拿游戏当生活,游戏就是生活。不存在崇高的理想,试图用“游戏”的逻辑消解现实中的困惑,表层上道德的话语隐去,尽管他们慷慨、活泼、会耍小聪明,这只能是无谓的反抗,现实不会就此退场。他们时时感到恐惧与孤独,在城市中集体失语。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人的现代化的滞后。他们对现实产生怀疑、对未来世界的不可知。使他们蜷缩在自己的壳中,小心翼翼地观照着壳外的世界,即使这个世界近在咫尺,却也在他们思想意识的触角遥不可及的地方。他们陷入了历史的空白与孤独的情绪之中,在游戏中消解崇高,填充苍白的时间,这时的时间只是一种流动,向前不可遏抑地延伸。人被时间的洪水裹挟而下。不能驻足,无法停留,在时间的向度上无可拒绝地存在着,并因此沿着洪水无可回溯地走向生命的终结。空间维度上,人在主观上拒斥离开现有的方位,在游戏中逃遁现实,沉醉于唾手可得的当下俗世生活,一任时间自由流动。
四、游戏逻辑蕴含理性精神
游戏意味着轻松和愉快,并不被赋予物质需要或道德责任。在《遍地枭雄》中,游戏的魅力可以说是游戏主体的非理性得到宽容,得到肯定。在游戏中消解现实焦虑,但在游戏这种非理性的形式背后,有着游戏主体在潜意识中对未知世界的幻想,以及由此带来的企望强化了对彼岸的皈依,在建功立业的目的指向下,游戏主体以独特的方式介入现实世界,他们试图通过游戏的非理性形式正是游戏主体为提高“小团队”的战斗力,得到社会认可与接纳所做的理性选择。
现实世界对游戏主体来说是陌生的,迷宫般的壳外空间罩着的神秘面纱,面纱下光怪陆离诡异的世界,他们手足无措,又在深层的内心趋求中希图融入。这时他们就把人生的价值寄托于一种价值指数远高于能力可及的人生位置之上,称王称霸。突围当下现实,并坚定地相信这种价值存在和达到的必然性。充满理想色彩的生活以游戏的逻辑突进,这只是现代性给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一种虚妄的乌托邦幻影。
游戏是有其既定规则限制的,尤其是游走社会中必定要受到公共规则——法律的制约,小说中的游戏主体“在地的隙缝里流窜,最终还是落入窠臼”,难逃现实的规训。游戏主体企图在“游戏”的逻辑中消解现实的困惑,幻想在游戏中躲避现代性带来的焦虑。既然游戏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就无可避免地受现实社会的规约,偷盗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伦理上都是错误的,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个“游走”的故事,剥离形式的壳,我们看到的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出走——堕落——毁灭。王晓明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中,认为王安忆“……总是怀着善意去刻画人物,却又不断在这里那里揭出他的一点毛病。”小说中的四个枭雄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尤其是韩燕来。生性纯净,由劫车的受害者变成劫车团体的一员,最终他们无一不被这个城市所拒绝。这四个并非面目可憎的男性,在小说的渐行中读者很容易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怜悯之心。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想融入而不得。他们的生存状态有种决绝的宿命感和挽歌式的悖离。城市有着现代化所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但人——尤其是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空间、生存价值在发展进程中却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甚至破坏,对此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结语
游戏逻辑是王安忆思考当下人的生存话语的一个特殊语境,在这个游戏语境中王安忆有意将人物置于非常态的生存空间中,也正是作者为凸显在中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人生存状态的改变。从理性上说,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转型是合乎社会发展的历史目的论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正是为了提高国人整体的生存质量,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身份的自我认同。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有了突飞猛进的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开展改变了国人原有的生活方式,生存价值超越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阐释范畴,人对生存境遇的改变缺乏心理准备,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无以参照,人对现有世界产生怀疑,对未来世界的不可知感到迷茫,由此给世人带来了生存的焦虑和困惑,甚至出现四个“枭雄”为改变底层的生存境遇而堕入犯罪之路的情形。可以说。将人物置于游戏话语中思考游戏主体的生存状态,是王安忆这个小说文本的独到之处,也是一次文本试验。“大王”们没有真实名字,人物只是一种能指的符码,处于一种身份的焦虑,人物在游戏中生活,试图在游戏中改变生存现状,通过游戏训练逻辑思辨能力提高团队偷车水平。可以看到王安忆对枭雄们的经历是持一种宽容的理解态度的,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一直关注人的生存价值的作家,作者尽管理解“枭雄”们的生存状态,但最终还是理性地将这个劫车团伙的罪责归于法律。但现实中,“三王”之流的“枭雄”的游侠生活只是极少数的特例,并不代表中国当下大多数生存境遇改变的世人的生存选择,尤其以这种极端的游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