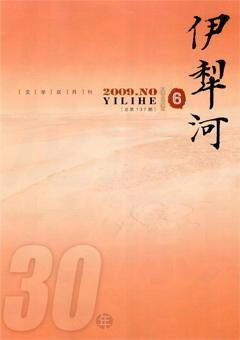厄内斯特.海明威:行动的人
邱华栋,小说家、诗人、评论家。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20年来,写作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骑飞鱼的人》、《单筒望远镜》、《教授》等8部。获得上海文学奖、山花杂志文学奖、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等10多次。
行动的人
厄内斯特·海明威首先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其次,他才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因此,我对某个中国作家说“海明威身上贴着假胸毛”这句话耿耿于怀,感到不满,因为害怕别人雄壮的人,自己恰恰是虚弱的,不过,也许他对海明威过于外在于文学本身的行动哲学不能接受,那么,这句讽刺还多少可以理解。海明威是最近50年来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影响最大的美国小说家,他的作品的销量,一定也是美国作家在中国最多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明威是挡在自己作品前面的人,他以自身的传奇性和行动性,将小说写作第一次变成了行为艺术,他的行动和小说写作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小说史上是一个奇观。而且,海明威写的还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小说,他以其文本上的风格化叙述,将小说的叙述带到了一个新高度,拓展了美国文学的疆界,与威廉·福克纳一起将二战之后的美国文学提升了一大截,将小说发展的中心强有力地从欧洲带到了美国大陆,改变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尤其是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创造出非凡的成就,昭示了小说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他留给我们的财富。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大都市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小村镇奥克帕克村,父亲是医生,母亲爱好文学和艺术,他们一共生育了6个孩子,海明威是第二个。厄内斯特·海明威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让他拉大提琴,教他欣赏美术作品,而父亲则教他钓鱼和打拳击,教他体育上的各种本领。这在海明威后来的发展中,奇妙地统一在一起,成为海明威一生受用的两个方面。按说,这行动性非常强的体育和偏向内向式的艺术审美活动恰恰是相反的,但是海明威在性格相反或者说互补的父母亲的影响下,吸收到了他们各自的长处和优点。中学时代里,海明威的体育成绩就非常好,游泳、足球、射击、拳击都是他擅长的运动,他还参加学校里的乐队,拉大提琴,并且很聪慧,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写短篇小说,并且向学校里的刊物投稿。1917年,在他中学毕业之后,他去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记者,开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在早期的新闻写作当中,由于新闻稿件对简洁和准确、生动和具体、短句与活泼的文风的要求,使他积累了很特殊的写作经验,日后他创造出电报式的写作风格,与这个时期担任记者是不无关系的。
1918年,19岁的海明威参加了美国在一战中的部队,担任红十字会车队司机,主要在欧洲南部、特别是意大利的后方医院服务,在一次遭受袭击中身受重伤,经过治疗,次年回到美国,在家中继续写作。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担任《星报》驻欧洲的记者,在巴黎、日内瓦等地活动,并且在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下,认识了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诗人庞德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在写作上进步神速。1923年,海明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三个短篇和十首诗》,次年在巴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个集子收录了18个以尼克、实际上是海明威自己的化身为主角的短篇小说。1926年,他还出版了中篇小说《春潮》。《春潮》是对他的文学启蒙老师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黑色的笑声》带有恶作剧性质的戏谑模仿。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海明威初露头角的作品,虽然在销量上很小,但是已经呈现出海明威独特的语言和叙事风格,引起了作家同行、评论家们的注意。
海明威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小说出版于1926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居留的美国青年,他们的生活面临危机,残缺不全又找不到方向,描绘了一代青年的迷惘和幻灭的感觉。这可以说是一部艺术家小说,书中刻画了想当作家和艺术家的青年在巴黎的困顿、探求和失落,充满了后期印象派式样的光影感,死亡、疾病、伤残和心理问题笼罩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巴黎的五光十色和艺术气质并没有抚平这些青年心灵的失落感,反而使他们找不到出路,更加迷惘。美国侨居巴黎的女作家斯坦因对海明威说过,“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词,放在了扉页上,可见他对这句评语的满意和欣赏。《太阳照常升起》也因此成为了“迷惘的一代”这个短暂和影响不大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作。这本书的出版,使海明威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前途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大陆。于是,1927年他回到了美国。
海明威逐步地确立了自己的“硬汉”文学风格,是以192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为起点。这部短篇小说集题材广泛,描绘了拳击手、西班牙斗牛士等硬汉形象,他们在面临人生困境和抉择当中,显示了男人的力量。尤其是死亡的威胁来临的时候,男人们竟然直接面对,毫不退缩,呈现出美国精神的一面。美国精神带有拓荒者的创造性和冒险性,这些品质在海明威的笔下,都有呈现,可以说海明威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写作题材,找到了能够引领美国文学向前走的方向。
行动的小说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影响最大的几部作品之一,我觉得也是他少数几部最好的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性,描绘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在意大利前线负伤,住进医院之后和一个英国护士的悲剧爱情故事——女护士难产死亡,年轻的军官带着悲情离开了欧洲。小说从主题上是反对战争的,情节上带有通俗爱情悲剧小说的影子,隐含着大男子主义的观念——女护士的死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即将面临世俗生活的难题,使小说带有了希腊悲剧的壮美色彩。小说的语言干净利落,叙述扎实简洁,细节生动具体,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描写,人物的性格也比较生动,但是稍显得平面。小说里有很多警句一样的议论,是对那个时代非常有力的批判和判断。今天看来也非常有力量。从小说的形式上来讲,这是一部多少有些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海明威还是在语言和句子上,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这个烙印非常鲜明,就像美国西部的牛仔给自己的牛打上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牲畜的符号一样,这个烙印就是精湛的叙事艺术,是属于海明威自己的,以精练、简洁、生动和省略为特点。尤其是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个部分,几乎可以和《百年孤独》的开头部分媲美,特别值得分析。开头部分确立了整部小说的叙述语言风格和语调:
“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和平原可以望见群山。河床里尽是卵石和大圆石,在阳光下显得又干又
自,河水清澈,流得很快,而在水深的地方却是蓝幽幽的。部队行经我们的房子朝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把树叶染成了灰蒙蒙的。树干也蒙上了尘土。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到部队不断沿着大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动,纷纷飘落……”在写景的文字中蕴涵着战争即将摧毁这一切的担忧,简洁、具体和生动的句子立即把我们带到了现场。而小说的结尾则更加出色,是小说史上最值得分析的结尾之一。据说海明威改写了39遍,才感到最终满意。在这里我引文如下:
“我走到房间的门口。‘你现在不能进去,一个护士说。
‘不,我能。我说。
‘你还不能进去。
‘你给我走开,我说。‘另一个也走开。
但是等我把她们赶走以后,关上房门,拧熄了电灯,并没有丝毫用处。这好像是在向一尊塑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房间,离开医院,冒着大雨回旅馆去。”
和《百年孤独》开头那句绕口的、包含了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不一样,《永别了,武器》的开头和结尾则是现在时间的。结尾是对一种情景的描绘:男主人公要去向恋人的遗体告别,两个护士在场,他把她们赶开了。然后,他默默地举行了一次告别仪式,没有悲痛欲绝,没有呼天抢地,没有大声哭泣,他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那里。强烈的感情,恰恰全部隐藏在简约的文字背后,但是效果却特别巨大。用动作和形象表现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动,用精粹的句子描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用简练的对话来呈现人物的性格,达到了超凡的效果,这就是海明威的叙事艺术的魅力。
1930年代前期,海明威居住在佛罗里达,后来又迁到了古巴,这和他喜欢大海有关。他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捕鱼、打猎和读书。1932,他出版了关于西班牙斗牛士的长篇专著《午后之死》,这本书将斗牛上升到雕塑艺术和死亡美学的高度。它本身并无离奇之处,但是,里面有从斗牛引申开来的他对文学写作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后来被称为是“冰山理论”的一段话:“冰山在海里移动是很庄严宏伟的,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海明威后来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所努力实践、并且几乎达到了完美境地的文学理念,就是这个冰山理论。在他简约的叙事语言背后,读者仍旧可以感觉到、乃至阅读到他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海明威在叙事艺术上的巨大贡献。193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到》,1935年出版了他在非洲狩猎的笔记《非洲的青山》,描绘了一年前他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及好朋友卡尔一起去非洲打猎,共打了三头狮子、一头水牛、二十七只各种稍微小一点的动物,书中描绘了打猎的惊险和非洲奇特的自然,还有他对好朋友卡尔的争强好胜以及与妻子的和谐恩爱,可见这段时间里,他过着多么逍遥自在的生活。
1937年,海明威出版了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这是一部中等水平的小说,描绘了在美国社会里单枪匹马闯荡的哈里的一生,他在古巴和美国之间走私,最后丢掉了性命,成为了一个悲剧英雄。小说的结论是:这个社会,一个人闯荡根本不行,是海明威对自己硬汉哲学、行动哲学的一种悲观的反思,体现出冒险和硬汉的精神,带有悲剧的震撼力量,但是同时也显得单薄。
同一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爆发,他作为记者筹集了几万美元和几辆汽车赶到了那里,去支持共和政府,反对佛朗哥的法西斯军政权,次年就发表了他一生中惟一的剧本《第五纵队》。剧本共分三幕,题材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以马德里保卫战为背景,粉碎了马德里城中的一个间谍网的故事——尽管这场内战最终以佛朗哥的军政权上台结束。近距离地观察西班牙内战,带给他创作激情,荷兰导演伊文斯执导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的解说词也是海明威写的,并且最终由他自己操着美国中西部口音来配音。1940年,他出版了以这场内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描绘了一个美国支援战士乔顿参加了西班牙游击队,奉命去炸掉~座桥梁,最后孤独地壮烈牺牲的故事,故事情节发生在三天的时间里,十分紧凑。在小说的辅线中,穿插了爱情故事以及游击队员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小说的篇幅翻译成中文有40万字,是海明威所有生前出版的小说里最长的,因为有大段的内心独自和回忆,使小说显得有些拖沓和冗长,而他的“冰山理论”在这部小说里尽管有所体现,但是却不明显。可见“冰山理论”更适合短篇小说的写作。海明威参与政治的热情掩盖了艺术上的精湛表达,而且,内部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有些拼凑和硬性虚构的痕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在小说艺术上很一般的作品。不过,它作为反映如今早就被人们忘记的西班牙内战的小说,倒留存了下来。
行动的哲学
海明威一直信奉一种行动的哲学,他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尽管他博览群书。他是一个行动的人,只有在行动中,他才可以写出他的小说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最为令人称道的就是,改装他的那艘名字叫“皮拉尔号”的游艇,使之变成了可以反潜艇的炮艇,在大海上寻找德国潜艇。不过,没有关于他和德国潜艇遭遇的任何记录。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他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最后战斗,因为他的身份是必须保持中立身份的记者,战后他被审讯,结果无罪释放。
海明威在小说写作上的高峰是《老人与海》的出版,这部篇幅只能算是一个中篇的小说出版于1952年。此前的1950年,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过河入林》,描绘了一个参加了战斗的上校前往自己过去战斗过的地区,回忆当年的战争的故事,有大量的心理描写,但是故事和叙述都缺乏有力的支撑,显得苍白贫乏。但是,篇幅不大的《老人与海》则相反,描绘了一个古巴老渔民桑地亚哥,在出海之后打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但是当他想尽办法、费尽力气与周折,把大鱼拖回港口的时候,那条大鱼已经被鲨鱼啃得只剩下了骨头架子。这部小说以一个老渔民的命运,上升到了象征的高度,将老渔民幻化成可以以耐力和信心抵抗任何人生挑战的符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小说塑造了一个硬汉,一个老年的渔民,但是和他以往所塑造的那些硬汉,比如斗牛士、战士、打猎者、偷渡和走私者不一样,这个老年渔民的经历不仅和古代希腊悲剧中的一些角色有呼应的关系,还成为了一个寓言,一个现代基督;一个巨大的人类命运的象征,同时,他的“冰山理论”在小说的叙述中运用得非常成功,简洁的叙事和纯粹的动作描写,反而使得小说有着硬朗的骨架和密度,掩盖了长度和难度的匮乏,以自身的强大力量,征服了所有的读者。这部小说本来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结尾部分,结果海明威把前面几个部分全部删掉了,只保留了有26531个词的这个结尾——这是他自己统计得出的数字。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给予了毫不吝惜的赞美,还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他
却说:“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尽管他试图抵挡别人对他作品的有趣分析,这部小说也是他自己觉得最满意的。因为该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当年的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并且,由于这本书的出版,两年之后的195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词中有这样的评语:“和他的任何一位美国同行相比,海明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寻求准确方式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朝气蓬勃的民族……作为这个时代伟大风格的缔造者,海明威在25年来的欧美叙事艺术中有着重大的意义,这种风格主要表现为对话的生动和语言的交锋。”
海明威喜欢参加各种冒险的活动,包括战争、打猎、捕鱼、观看斗牛等等,还有酗酒和两次非洲打猎中的小飞机失事,实际上都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损害。在他的体内,一直留着一些弹片,这些弹片总是带给他神经上的痛苦,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海明威就离开了古巴,回到了美国,居住在爱达荷州,还去西班牙看斗牛。他对斗牛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研究,从中可以发掘出他一以贯之的硬汉美学和人生哲学。1960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描绘斗牛的专著《危险的夏天》。因为身体的病痛,加上还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他于1961年7月2日用自己的猎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的方式自杀。海明威连死亡的方式都是那么具有行动感,那么的主动,那么的热烈而又让人佩服。他以自身的实践来证明了自己的行动哲学。这个方面,他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
在他的身后,留下的遗作还有不少,由他的遗孀整理出版,包括长篇回忆录《流动的盛宴》(1964)、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1970)、《海明威书简》(1981)、长篇小说《伊甸园》(1986)、《曙光示真》(1999)等等,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并没有超过他最好的几部小说。《流动的盛宴》回忆了当年海明威在巴黎流浪和闯荡的经历,其中,对很多同代作家、尤其是对菲茨杰拉德的描绘最为逼真。小说《海流中的岛屿》分成三个部分,描绘一个画家一生中的三个片段,画家的三个儿子分别死于车祸和战争之后,画家自己决定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去。小说的主人公带有海明威自己的影子,尤其是第三个部分中,画家在海上执行巡逻任务,和海明威自己改装游艇成为一艘小兵舰的经历一样。画家硬汉形象仍旧是他塑造的典型人物,画家怎么遭受生活的打击都没有倒下去,所以这部小说在主题上是重复的,由于是遗孀整理的,篇幅达中文42万字,可以说行文的剪裁也并不出色,不能像海明威自己那样痛下板斧,是一部很一般的作品。
《伊甸园》也是海明威的遗作之一,小说的原稿有1500页,在出版社编辑的多次删节之下出版了,翻译成中文在17万字。好像海明威不写他自己就不行一样,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一看就是作者的化身。小说的时间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人物有三个,青年作家大卫、他的新婚妻子和妻子的女友,他们三个人形成了一种多少有些畸形的恋爱关系。小说的题目叫伊甸园,显然就是为了描述亚当和夏娃当年吃禁果的感受,小说的主题就是情爱和性,带有变态性爱的场景是小说的特色,也是海明威多年都没有修改并出版这部小说的原因,小说的三个主人公完全可以从海明威和他的第一第二任妻子身上找到原型,从小说的情节上可以看出海明威某些生活的真相和隐衷。
小说《曙光示真》则以他和第四任妻子玛丽前往非洲打猎的经历作为背景,其中刻画了海明威自己在当地结识的一个黑皮肤的女友黛芭和他们夫妇的关系,隐含了一种三角的微妙关系,但是这种三角的男女关系却处理得相当好。经过了出版社编辑的削删面世的小说只是手稿的一半篇幅,其力度和艺术水平都无法和他的那几部杰作相比。
海明威以他简洁如同电报电文一样的语言风格,引发了一次文体上的创新革命,这一点后来在世界上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影响的痕迹。因此,我觉得他的长篇小说不如他的短篇小说好。在他的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中,《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是最好的,分别展示了他创作中最重要的符号价值和文学阶段:《太阳照常升起》是他早年开创出“迷惘的一代”文学风格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则分别描绘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他的印记;《老人与海》则代表了他的“硬汉文学”的高峰,并且具有着古希腊悲剧和圣经故事的动人力量。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则是非常风格化的,无与伦比的,开创出了短篇小说写作的一个新天地。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白象似的群山》、《杀手》、《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等。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他就像拿着一把斧头的人,砍掉了整座森林里的枝枝蔓蔓,省略和空白恰恰丰满了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省略之后的满溢,也实现了他要“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见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以及以八分之一的显露来展现八分之七的隐含内容的冰山理论的文学理想,对话往往是他的短篇小说里最精彩的部分。他一共写了70多个短篇小说。1972年,纽约一家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收有24个短篇小说的《尼克·亚当斯故事集》,这是从海明威生前发表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和一些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中挑选的,主人公都是尼克·亚当斯,这个连贯在小说中的人物像是一个旁观者,主要经验取材自海明威的青少年成长的经历,以及对这种经验的挖掘和超越。
海明威是一个敢于挑战前辈和同辈的作家,他的自我感觉一向特别好,几乎是一个自大狂。他曾经和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打过笔仗,互相较劲,吹牛说自己更热爱大海,而不愿意憋屈在福克纳的那个小县城里,但是,实际上,福克纳却比他更加的具有深度和厚度。他痛恨批评家,骂他们是“呆在文学身上的虱子”,这恰巧地妨害了他自身的完善。因为评论家在他的创作后期,对他的写作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指点,他全听不进去,以硬汉式的粗暴作风,猛烈攻击善意批评他的人,这显示了他性格上的刚愎自用和目中无人。他经历了4次婚姻,这也成了美国报刊上的花絮,也许,从心理学和人格病理学上来分析海明威,会得出更加有趣的东西。
对海明威的总体评价上,我觉得,他的长篇小说有很多都是不成功的,重复和过于风格化、外在化是通病,小说的主人公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化身,他通过塑造那些硬汉来重新塑造自我的形象。但是,他却是20世纪少数几个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历史上,我把他排在福克纳和索尔·贝娄之后。他接近了文学的峰巅,但是,就像他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里开头一段文字,描绘在乞力马扎罗山雪峰的旁边有着一头风干了的雪豹的尸体没有人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一样,我觉得,那头雪豹就象征着海明威自己,他是在努力地攀登文学颠峰的时候,最终功亏一篑,后继乏力,英勇地死在了半山腰,获得了一种永恒的遗憾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