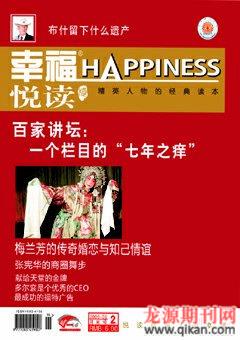小平同志果然爱冒险
赵 耕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即将出发前往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此行的意义非同凡响。而驾驶专机送邓小平出访的任务,落到了尹淦庭身上。
尹淦庭说,当年飞往美国的航线和现在不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冷战时期,去美国的飞机无法从广袤的苏联国土上空飞过,因此只能向东经过日本,之后穿越太平洋才能到达美国,全程一共14343公里。飞机足足要飞上17个小时,其中有12小时都是在太平洋上空。即使当年最先进的波音707飞机也无法一口气飞过去,中间必须加两次油,所以最终确定的航线是北京——上海——安克雷奇——华盛顿。
这条“最佳航线”却给尹淦庭和他的同事们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起飞之前得到报告,后面的三站天气都不好——“安克雷奇,中雪”,“华盛顿,大风”,最令人头疼的是上海,“大雾,能见度300米”。按照当年的技术水平,机场能见度低于800米飞机就不能降落,专机只能先在北京等待上海云开雾散。
大家把飞机暂时不能起飞的情况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把头扭向窗外,仿佛在自言自语:“天气这么冷,老同志们怎么受得了啊……”——停机坪上,欢送的人群还没有离开,不少老同志依然站在那里,想目送这架意义非凡的飞机飞上蓝天,向华盛顿飞去。
最终,大家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先“开车”,让飞机滑行一段,作出即将起飞的假象。欢送的人群眼看着飞机滑出停机坪,开上了跑道,终于纷纷散去。而实际上,飞机在跑道上转了一圈之后,又悄悄回到了原地。
40分钟之后,上海方面再次发来天气预报——大雾越来越浓。大家只好向小平同志报告:“上海的大雾使能见度只有300米,飞机一时还走不了,请您下机休息一下好吗?”
一贯沉着冷静的邓小平却有点着急了:“美国方面都已经安排好了,耽误了行程怎么办?”
尹淦庭立即与同事们研究对策,很快达成一致:为了争取按时到达华盛顿。飞机必须马上起飞,如果上海天气转好,按原计划降落虹桥机场,如果无法降落,就直飞东京,加油后再飞向美国。
按照这个飞行方案,专机“第二次”起飞了。
飞机经过济南上空时又收到天气预报:上海天气逐渐转好,能见度已经由200-300米上升到了800-1000米。听到这个好消息,驾驶室里一片欢腾——按原计划,降落虹桥!
谁知飞机刚进入“上海走廊”,大雾再次升腾起来,能见度又降到了600米。眼见雾气越来越浓,这样的天气条件远远达不到降落标准,但再想改道东京已经来不及了,飞机只能尝试“超标降落”。
地面能见度太低,飞机落地必须依靠机场的“盲降”系统。偏偏虹桥机场的系统又在这时出了故障,飞机上的仪表指示左右摆动,给降落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因为视线不清晰,飞机已经很接近地面了。负责驾驶的陆洪明才猛然发现,飞机向跑道左面偏出了足足50米!
陆洪明狠狠压下右操纵杆,想用最后的机会对飞机方向进行修正,不料由于惯性太大,“矫枉过正”,飞机一下子又偏到了跑道右边。陆洪明再想向左修正,已经很勉强了。情急之下,所有机组人员异口同声喊出了两个字:“复飞!”陆洪明一面大声答应着:“同意!”一面加大油门,飞机抬起头再次升入空中。
飞机一圈圈在上海上空盘旋,驾驶室里也展开了一场争论。领队徐柏龄和机长尹淦庭商量之后认为,东京机场的安保措施做得如何不得而知,临时改降那里不够稳妥;而安克雷奇预报有中雪。一旦夜航到达那里之后不能降落,还要临时再选择一个空军基地,机上没有美籍领航员领航,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事已至此,只能再一次尝试降落在虹桥机场。
第一次降落的失败或多或少影响了大家的情绪。为了稳定军心,经验丰富的徐柏龄亲自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准备第二次降落——一旦又不成功,只能请示小平同志,考虑改飞东京。
幸运的是,第二次降落成功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靠飞机上的仪表盲降仪瞄准了跑道,飞机终于稳稳降落在虹桥机场的跑道正中——此时机场的能见度只有500米。
事后虹桥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现,第一次降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航向台上落了一只小鸟,飞机盲降仪表指示受到干扰,才没能准确对准跑道。
最终到达华盛顿的时间只比预定的晚了一个半小时。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尹淦庭还是很感慨:“那次的天气状况,换了一般人估计就不让起飞了。之后我们都开玩笑说,小平同志果然是个喜欢冒险的人!”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