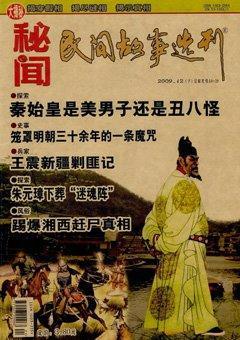古代流氓的恶行
三石
流氓作为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特征则表现在行为方面,也就是说,流氓行为是流氓群体的重要特征。流氓行为,如果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低级下流,如果具体言之,则可细分为“骗”、“讹”、“打”、“抢”、“淫”等诸方面。
骗
行骗是流氓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行骗方面,流氓所采用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预设圈套是流氓行骗的最常用的方法。这种预设圈套的行骗形式往往难以被人们发觉,其手法可谓阴险狡诈。早在宋代,有的流氓就开始采用“设局”以骗财的办法。
在杭州,就曾有一种“美人局”,以娼优假扮姬妾诱引少年为事,从中骗诈钱财。《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故事,所讲的就是这种“美人局”。有一姓李的客商,在杭州发了横财,来京都临安走门子花钱买官衔。这个人下榻在一家旅店里,对门有个宅院,门首垂着帘子,常有位少妇站在帘后看街上热闹。隔帘花影,娇声莺转,引得这个正处寂寞中的暴发户心生非非之想。有一天,李正站在店坊房门偷看对门,有个卖黄柑的小贩经过。他既想吃黄柑,又舍不得掏钱买,便建议和小贩以“关扑”方式做交易,且借此在意中人眼里显露两手。没想到这一招不但没有露脸,反而输了本钱,心怀懊恼。恰在此时,对门宅院里出来一个小童子,端一盘黄柑送给李某,说是本家主母见李输了本钱有些不忍,特送家藏柑子给官人尝尝。李某见美人有关爱之心,于是春心大动,便顺杆向上爬,也收拾一些礼物拜托小童回谢,于是就牵上了线。此后,少妇常使小童送些菜肴点心之类给李某,李某也常送一些礼物给美人。几番周折之后,二人便搭上了“关系”。某晚,李某趁夜与美人幽会,不想正欲行苟且之事时,男主人突然回家,捉个正着,李某见事不妙,便跪下请求“私了”,男主人借此派仆人将李某财物劫掠一空。次日,李某再悄悄探看对门,已是人去楼空。
此外,还有以访取官场隐私以借机行骗的,有假成亲害夫以讹钱者,有借官府官人之名以行骗者,真可谓是花样繁多,不胜枚举。
讹
设计讹诈,可谓是一种阴险毒辣的流氓手法,其花样甚多。
道光年间,烟禁很严。在广州一地,嗜鸦片烟者很多,有一位西关的千总,“藉以渔利,所得不赀”。时有一无赖,名陈谭,“善以诈欺取人财”。于是,陈谭在千总对门赁一民屋居住,每次出入,就用舆马。后来,人们就经常看到“豪仆三五,宾客杂沓,日集于党”,所以都以为他家是巨室。一天,忽然有一仆人被责打,创甚。仆人偷偷逃出来,埋怨他主人,并告诉千总道:“我因小小失误而被主人责打,而我家主人其实犯了更大的罪责,还敢如此作威作福。”千总问:“你的主人犯了什么罪?”仆人道:“今天我就给他抖露出来,就是吸鸦片烟。”千总问:“你有证据吗?“仆人答:“大白天不吸,到了漏三下,才开始吸。”千总庆幸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就用话诱仆道:“我奉上官之命,专门在此禁吸鸦片,如果获得证据,就酬劳你百金。不过,你得替我带路。”仆人答应。到了夜深之时,仆人带千总前往,随从还有几个当兵的。到门前,一拥而入,将陈谭捆绑,并带走他的烟灯烟枪,陈谭一到千总衙门,就大笑道:“到了这里很好,我就不走了。”千总问:“你是谁?”陈反问:“难道你不知我是陈谭?”千总道:“咄!现有证据在,你还有什么话说?”陈谭取过枪掷于地,问千总:“你仔细瞧瞧,这个也可以当证据?”千总仔细审视枪之斗门,在竹节下面,根本不可吸食。到了这时,才知道被他骗了,就只好深自引咎,放陈谭回去。陈谭不许,“千总乃出金为谢,遂挟以归”。
按理说,这位千总靠禁烟专门敲诈烟客,也算门槛很精。可是,面对阴险歹毒的流氓陈谭,他却显得逊色三分,也乖乖地钻到陈谭所设的圈套里去了,最后落得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打
打群架,横行市井,以强暴之力诈取市井百姓的钱财,这也是流氓的又一手段。宋代流氓时常在城市里欺行霸市,欺负乡村入城小农,动辄打人,而且打人的拳法还自成一派,号称“社家拳”。南宋时期,还有一批不逞之徒,专门“以掀打衣食户为事”。即使受害者告官治理,也毫无作用,以致其害益甚。这类流氓活动,在当时也有专门的称呼,称为“打聚”。动不动就打人,在街上如凶神恶煞一般,这大概就是人们对流氓的基本印象。
流氓这种“打”,通常情况下是对一般平民百姓的,然而有时流氓之间也发生冲突,出现互相仇杀的局面。如在江苏太仓沿海一带,就有一些流氓以贩卖私盐为业,继之则结党行劫,最后导致“互相仇杀”。天津的混混儿经常打群架,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也算是耀武扬威;上海的白相人也常在茶馆中“吃讲茶”,如果言语不和,最后也诉诸武力,靠斗殴解决问题。而流氓与流氓之间的寻仇打殴,比起流氓殴打平民来就更为凶惨了。
清代,松江青浦县周浦西六里,名苏家桥,此地就有一些流氓,时常扰乱社会治安,还动不动就斗殴打仗,有时他们内部也发生一些流氓群体之间的群殴。据载,苏家桥一带,比较有名的流氓有陆寅、王六等人。有一次,他们拦路抢劫了一客商之米,被周浦镇乡兵擒获,就地斩首。周浦镇地方虽小,但流氓的“打仗”活动却极多。镇上大富之家不多,而小康之家确也不少。镇上的人获知此事以后,知道苏家桥的流氓会前来寻衅报复,于是一些“强梁者立起议论,倡为先锋之说。分一镇为四境,每铺之富商店铺,或粮数,或钱数,各就其地,每日送与强梁者为防护焉。整备刀枪器械,置造旗帜衣甲,编十家为甲,练集乡勇,铸成大炮,以御抢掠”。应该指出的是,这其中的所谓“强梁者”,也无非是一些流氓打手,只是由于他们才敢出头露面,充当斗殴中的“先锋”,所以当地百姓才将安危寄托在他们身上。在当时看来,做这种抵御流氓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不久,苏家桥的流氓却真的纠合梁家角并塘口等地的流氓,前来周浦镇报仇,“三更时分,东西发号炮,各家惊愕”,“人人结束执械,思图混战”。这场混战,实际上是一次乡镇流氓之间的大斗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抢
抢劫,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强行抢夺财物。抢与打往往难以截然分开,也就是说,抢经常是通过“打”的手段来实现。换言之,流氓在抢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抵抗,就得通过打来保证财物从别人手中转到自己手中,所以流氓取财往往是打抢同时进行。
一般性的抢劫已为正经的良民所不耻,而更为可恨的是,那些流氓之中的凶狠之徒,在通过打抢以获财时,有时还要以杀人为前提,也就是所谓的“谋财害命”。如浙江桐乡县乌青镇有一马姓幼儿,才四五岁,两手戴着银圈子。马姓族内有一无赖,就将幼儿哄骗到荒野,“杀而夺焉”。
“趁火打劫”也是流氓们在抢劫过程中常有的事。在清代,流氓不但趁火打劫,而且还亲自放火。就当时杭州的情况而论,就经常发生火案,而纵火者,实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当然,他们纵火之本意也是“利在抢夺”,乘混乱,任意抢劫。这种趁火打劫,清人有专门称呼,即“抢火”。关于杭州流氓的“抢火”活动,清人毛奇龄曾作如下记载:“乃不幸失火,则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间,名为救火,实抢火也。”清人还就“抢火”一行作有竹枝词一首,词云:“打阵聚赌作营生,抢火拦丧党横行。敝俗总由明失政,转移风化仗官清。”这首词所说的虽然只是清代上海一般意义上的流氓行为,不过,其中“抢火”也是所提内容之一。
淫
晚清时节,由于西风熏染日烈,中国的社会风气也日渐开化,往昔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已不再恪守闺房的寂寞,而是频频步出闺阁,时常出来抛头露面。年轻女子抛头露面机会的增多,这就为那些“轻薄子弟”调戏良家妇女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据《申报》载,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城中城隍庙前,一妇人独行。此妇人年甚少,相貌却颇美。当时有两个轻薄无赖男子,一名相交,一名徐锦,见这位妇人孤弱无伴,就从后面追赶上去。近前以后,嬉笑指点,品其妍媸。这两个无赖感到光说兴犹未尽,于是再赶行几步,到四景园茶室门前,就挨妇人之肩而过,竟伸手摸妇人胸部,“兼肆谑浪”。这位妇人一时大惊失色,急忙用两手紧握其臂,大呼捉贼,两人意欲甩手逃跑。此时路人聚集,全环视妇人,向她询问何事。妇人如实道来,“具言所行,众人均笑詈之”。于是将这两个无赖捆送县署,“二人共荷一校”,在四景园门前示众三日。
流氓不仅调戏良家妇女,而且还诱奸妇女,专干性犯罪的流氓活动。同治年间,浙江郸县城内西双桥,有吴姓婆媳两人,专门以替人收生为业。婆婆年达六旬,而媳妇尚属少艾,且丰姿秀美。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里三更时分,行人已经绝迹。忽来一恶少,持灯一盏,命轿一乘,说是前来请收生。还说地点在小教场,韩姓家,请您媳妇去,大概属于难产,实则满嘴谎言。仓促之间,婆媳俩也来不及多细想,媳妇就“登轿径去”。婆婆看到轿夫身着棉绸小衫、纺绸裤子、广式镶鞋,与一般轿夫的装束不同,心里也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就请邻里五六人追赶上去。正好碰到恶少与轿夫商妥,打算借演武厅作云雨台,“意将轮奸”。显然,这位轿夫也是无赖的党羽。后来看到有人喊叫而至,只好弃轿而去,狼狈逃窜。
选自《中华传奇·大历史》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