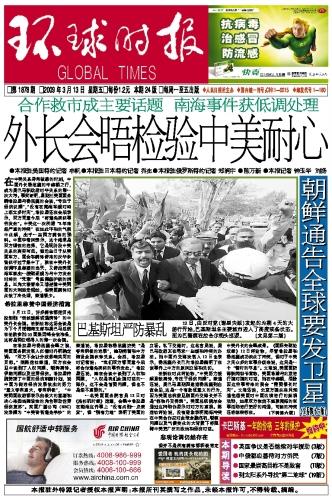诗歌缘何离我们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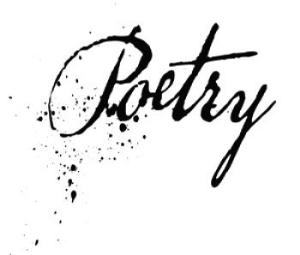



贺文玄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文坛上还有诗人的一席之地么?至少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上看,诗人仍占有牢牢的一席之地,近年获奖的就有捷克的塞弗尔特、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美国的布罗茨基、墨西哥的帕斯、爱尔兰的希尼、波兰的申博尔斯卡……然而在一长串名字的背后,却是诗歌的边缘化、小圈子化。一方面,诗歌的流派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复;另一方面,为大众所熟知的当代诗人、所广为传诵的当代诗歌,却似乎越来越不多见了。
是当代诗人不努力么?似乎绝不能这样说。即使在物欲横流的欧美,也同样生存着许多以诗歌为主业、甚至以诗歌为生命的所谓苦吟派诗人。他们或甘守清贫,笔耕不辍;或不辞辛劳地颠沛流离,一面积累灵感和素材,一面为自己诗集的出版募集资金。
是支持力度不够么?有一些,但似乎还不能这样说。尽管诗歌的边缘化人所共见,但各种形式的诗会、诗歌节,几乎每周都会在地球的某个地点开展。尽管当代诗歌的行情并不被市场看好,但诗人们仍得到不少支持和资助:诺贝尔奖及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不消说,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文化部门都设有专门扶植诗歌发展的基金……
是人们不再喜爱诗歌了么?似乎同样不能这样说。雪莱、普希金、海涅、波德莱尔等的诗集仍是被一版再版的畅销作品;以诗歌语言书写的古典戏剧、寓言和童话故事,更拥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可以说,诗歌的群众性,本不应比其他文学体裁更糟。
但不能不承认诗歌的边缘化: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数量和比率并不见下降,但能被记住名字的越来越少;每年推出的诗集并不见下降,但能卖得出去的越来越少———在被公认纯文学生存状态最好的法国,一部诗集的“经典印数”是200册,这几乎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数字。不能不承认,诗人的世界离人们越来越遥远。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崇尚自由、个性的西方诗人们开始毫无顾忌地打碎传统诗歌的束缚,竖起一面又一面新诗歌流派的旗帜。这种勇敢和创意开辟了全新的诗歌天地。然而物极必反,对传统过度执拗的抗拒抵触无意中让当代西方诗歌远离了流淌千年的泉源,而对自我和主观意识的放纵又让本已是小圈子主义的当代诗歌团体、流派如白细胞般不断分化、滋生,旗号越来越多,每面旗帜下的人却越来越少。
诗歌仅仅是感悟的载体,仅凭形式的翻新是不足以动人的。虽然大多数诗人也在努力地感悟社会、世界和时代,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信息传递的速度在加快,数量在剧增;另一方面,留给诗人(乃至所有人)感悟或呼吸的空间却在减少,加上西方当代社会生活相对平稳,不论“大隐隐于市”的入世派诗人或秉持行吟传统的苦吟派诗人,他们的诗词灵感也不能不被有限的阅历所束缚。
正因如此,在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社会动荡和人生变故更多更复杂的非洲、拉美等地,当代诗歌仍具备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论是在军政府时代饱受家国之痛的阿根廷人赫尔曼,还是“诗人之鹰”尼加拉瓜人卡德纳尔,身为约鲁巴人却对同族虐杀其他民族行为公开表示愤怒的尼日利亚人索因卡,山河破碎、身世浮沉,令他们的诗歌饱蘸生命的浓墨重彩,而同样的感悟和经历,又令他们的诗句产生广泛的共鸣。
不仅如此,在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当地诗歌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更密切。在那里,当代诗人不会羞于谈及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也不会为了小圈子的认同而迫不及待地和传统、民间的诗歌习惯划清界限。墨西哥大诗人帕斯从不讳言传统对自己的影响,塞内加尔的桑戈尔(首任总统,后离职专事诗歌创作)和索因卡等人虽用法语、英语创作,但他们都毫不讳言自己诗歌的黑人气质,甚至公开宣扬“黑人性”创作道路。更何况在这些“西化”的诗人背后,还有无数“草根诗人”,如始终坚持用伊博族语言写诗、被西非民间诗人推崇为“我们的诗歌之王”的尼日利亚大诗人达鲁黑。
当诗歌离人的世界越来越遥远时,诗歌的世界注定也会变得越来越遥远。虽然这并不妨碍当代诗歌在特定的文学圈子里继续得到推崇,也不妨碍我们对当代诗人的执着、探索和努力,表示应有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