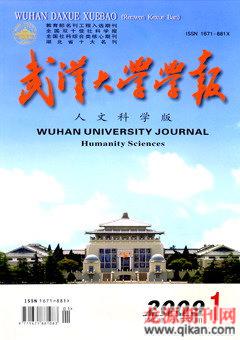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及后果
郭小安
[摘要]大众媒介是西方宪政民主的重要基石,是维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保持相对独立性是其发挥民主功能的前提和关键,自由化和私有化是其必然逻辑。但种种迹象表明,大众媒介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结果,媒介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但其结果却难逃市场化商业逻辑的宿命,被形象地称为“挣脱了铁的枷锁,却陷入了银的枷锁”。因此,解读西方民主政治下大众媒介异化的表现、原因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对于我们破除西方新闻政治的神话,了解媒介与民主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大众媒介;功能异化;政治后果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1-0115-08
大众媒介伊始曾经被认为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石,是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重要实现途径,而保持相对独立性是其发挥民主功能的前提和关键,私有化是大众媒介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必然逻辑。正如美国学者基恩所说的那样:“市场竞争是实现报刊和广播电视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关键条件……自由竞争可以确保意见市场的形成。”而且,传媒的自由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促进服务,能够更好地与公众的口味相吻合,还能带来竞争之后多元化选择的好处,而政治官僚控制下的媒体却做不到这一点。“公共服务性广播的原则是趋炎附势的,它为少数人谋利益,其基础是泛商业化的偏见,它窒息了个人的需求,其结果是不能充分利用频谱,从而导致节目贫乏。官僚制下的公共媒介制作节目,并不注重质量,只是对节目以及节目的时间安排不厌其烦地反复审查。一旦有不合意之处,便动用去哪里硬性撕破契约。同时,对公共服务性媒介消费者的选择进行了系统而任意的审查,威胁着表达自由。”所以,解除规则、自由竞争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中大众媒介功能发挥的前提和保障。
但是,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媒介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但其结果却难逃市场化、商业化控制的宿命。在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和市场竞争的法则驱动下,媒介逐步由多元化格局走向了并购、重组,最终形成了寡头化垄断的局面,其后果是媒介成了市场和寡头集团的傀儡,成了几个寡头集团分权逐利的工具,客观性和独立性越来越受到质疑,正朝碎片化、戏剧化、庸俗化、形式化方向发展,被沦为“企业盈利压力、政治谎言和公众低级趣味共同作用下的难以理解混乱的产物”。同时,也间接导致了民主由公共性走向消费娱乐性,政治参与低下,政治效能感下降,政治民主越来越走向形式化等。可以看出,大众媒介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结果,相反,市场化的过度竞争导致了大众传媒背离自由主义新闻的根本原则,逐渐偏离其正常轨道,造成了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了民主本身。因此,解读西方民主政治下大众媒介异化的表现、原因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对于我们破除西方新闻政治的神话,了解媒介与民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大众媒介的民主功能
大众媒介作为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载体,自其诞生起,就不可避免地刻上了政治的烙印,正如社会传播学大师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媒介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任何新闻媒介无法超脱于政治。”总的说来,大众媒介在民主政治中具有以下几个功能:
(一)议题设定功能
“议题设定”的概念是由科恩于1963年提出来的:“大部分的时候报纸的力量并不在于叫人们去想什么(what to think),而是极成功地告诉读者可以想些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这一经典的论断被认为是议题设置理论(the agenda-setting theory)的标志性开端。随后,它得到了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等人的证实。他们的中心假设是:公众会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会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后来,议题设置理论得到了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的证实和发展。他们选取美国1968年总统大选为案例,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和科恩的判断如出一辙:“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这方面则相应的下降。”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从此,议题设置理论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而慢慢流行开来,成为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议题设置功能也被看作是大众媒介基本的政治功能,成了解读媒介与民主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
(二)政治输入与反馈功能
政治输入和反馈是政治系统理论中的重要范畴。美国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认为,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而政府过程就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公众意见和民意)输入、输出及反馈过程。政治系统的平衡有赖于输入与输出的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依靠反馈实现的。通过反馈,政治系统就可以不断进行输入——输出——输入——输出……,从而使自身无限延续下去。如果没有反馈,政府就无法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有效判断,从而直接影响到输入与输出环节的数量与质量。社会总体环境通过各种反馈环节不断地向政治系统输入,给当局决策提供原料;政治系统为了生产“输出”,便对原料进行加工,而这个加工的过程就是一个巨大的处理和转换过程。大众媒介作为信息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主要工具。在现代社会,公民越来越少地直接参与政治,而是借助于一些中介组织和机构,大众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工具,也成为公民主要的政治输入和反馈的渠道。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大众传媒的政治输入和反馈确实至关重要,并已经成为现实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政治社会化功能
“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这一概念,自1958年美国学者伊斯顿提出以来,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尝试对此内涵做出界定,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政治社会化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就个人层面,它是个体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塑造政治价值和政治人格的过程;就社会层面,它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传播、交流、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得以自我延续和发展的基本保
证。传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主要是围绕着家庭、学校、单位及个体所在的社会群体展开的。因此,其政治知识、政治心理特征及行为受所处环境和文化的制约。而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媒介的出现,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接触全世界各地政治文化及不同政治社会所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的机会,有人形象地把电视等大众媒介称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四)政治监督与纠错功能
政治纠错和政治监督被认为是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大众媒介作为公共信息的主要传播工具,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监督和纠错的主要体制外力量。政治监督的前提离不开知情权与表达权,可以说,没有公开和透明就没有知情权,而新闻媒介是公众了解各种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大众媒介可以使社会事务透明化,可帮助受众行使知情权。所以,大众媒介被称为是打破政治神秘主义的天然杀手,是“打开政府抽屉的卫道士”。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甚至把喜欢揭露政治社会阴暗面的新闻记者们说成“扒粪者”,来比喻那些只朝下看、不往上看,既不抬头望天,也无视王冠,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新闻记者。大众媒介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对政府行为能形成有效制约和约束,被形象地称为是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可以说,监督与纠错是大众媒介与生俱来的功能,“对于新闻记者来说,通过调查报道来告知公众,揭露腐败和纠正错误,这是不言而喻的职责。”
二、大众媒介功能异化的表现
如上所述,大众媒介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石,是维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但同时,大众媒介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发挥其正面功能的同时,也时刻有“作恶”的潜能。当前,大众媒介在市场化、商业化的逻辑下,其民主功能遭到了异化,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
(一)从独立、中立性到市场的附庸和傀儡
独立和中立性被认为是大众媒介能否保持客观和公正的关键因素。随着市场力量不断地腐蚀大众媒介,大众媒介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地位,不得不沦为市场的傀儡,其客观性和中立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传播学大师阿特休尔也指出:“新闻媒介好比吹笛手,而给笛子定调子的人是那些付钱给吹笛手的人。及时付钱的主子身份不清,情况也是如此。”在解除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驱动下,大众媒介逐步由多元化格局走向了并购、重组、垄断,并最终形成了寡头化垄断的局面,造成的结果是:大众媒介成了市场和寡头集团的傀儡,成了几个寡头集团分权逐利的工具。正如罗伯特·哈克特所指出的那样:“集中和垄断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越来越少的新闻公司来获取关于通过丰富多元的党派报纸集团来提供一个负有竞争力的意见市场的观点有点过时了。”在商业化、市场化逻辑作用下,大众媒介正朝碎片化、戏剧化、庸俗化、形式化方向发展,人们对大众传媒对民主的促进作用越发质疑。正如美国学者施内德所揭示的那样:华盛顿越来越成为个体企业家的天堂,他们不需要政党的支持,而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媒体形象口(第22页)。总之,新闻媒介看起来确实独立自主,看起来确实在向权势们挑战——俨然成为政府第四大部门。然而,只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显然就会看到这种关于新闻媒介权力的信念,只是那些拿它追逐自身目的者手中庞大的武器而已。正如李献源所揭示的那样:“这些貌似可以呼风唤雨、权倾一世的‘无冕之王,不过是那些私营大企业老板的雇佣伙计。”
(二)从公共批判性到“娱乐至死”
监督和批判被认为是大众媒介发挥民主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的一种普遍趋势是:大众媒介正在由公共批判性走向娱乐性,美国学者博兹曼把这一现象比喻为“娱乐至死”。他这样描述道:“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大众媒介娱乐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硬性新闻的减少而软性新闻0的增多。新闻消费者的点差和观众收视率的数据证实了严肃的、有关政治和国际问题的硬新闻不太受欢迎。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新闻题材是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消费领域对他们有影响的话题,例如犯罪、名人、明星绯闻、健康以及娱乐等。在关于美国新闻兴趣方面的调查中,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得票率最低(除了突发性的国际危机,如“9·11”那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如果我们看看不同年龄段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例如,在50岁以上的年龄组中,对于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感兴趣的人最多,比20%多一点;但在18到29岁的年龄组中,这一比例只有10%。与之相比,所有的年龄组对于犯罪新闻的兴趣都达到40%。
大众媒介娱乐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开始由公正和客观性走向戏剧化、娱乐化和夸张化。在娱乐化使命的驱使下,媒介提供的内容不再是信息,而是一幕幕戏剧。为了谋求“好看”的效果,媒介不惜将任何严肃的新闻弱化、娱乐化。由于着力于煽情和刺激,信息就不再是信息,而是加工粉饰过的“虚拟影像”。这样,选择新闻的标准完全是情绪战胜了理想,新闻政治里面充斥着低俗、戏剧、离奇、夸张的片段,而新闻的公正性和批判性正在丧失,以至于“现在我们的新闻只报道校园枪击事件,不报道学校;只报道火车撞车事故,而不报导交通;只报导地方政治家的丑闻,而不报导选举本身只报导最近的谋杀案,不报导正在下降的犯罪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媒体中的各种犯罪和暴力事件频繁出现的同时,真实的犯罪率其实是在下降的。比如,美国全国电视网中关于谋杀的新闻,从1993年到1996年,增加了700%;而实际上,这一段时间社会上真正的犯罪率下降了20%。
(三)从新闻自由到滥用自由
大众媒介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确定下来的,它本身作为西方宪政民主的一部分,既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又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下来后,成为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工具。约翰·弥尔顿在其论著《论出版自由》中首先提出言论自由的主张,认为言论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一个共和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并且从法律上加以保障人民只有通过言论自由才能监督政府。”可以说,新闻自由是政治民主的逻辑起点,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机部分。美国的新闻自由植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中:“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可以说,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成了大众媒介的“庇护伞”,成了获取特权的“尚方宝剑”。但是,不幸的是,大众媒介在新闻自由的幌子下,在很少受到权力约束的情况下,开始走向异化,从享有自由到滥用自由,这种行为越来越遭到民众的质疑和不满。“在美国,无论是政客还是平民百姓,人们对新闻媒介的不满和憎厌与日俱增。目前,大众媒介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获得了格外的保护权。”这种缺乏约束的自由,在商业目的的驱动
下,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媒介新闻自由滥用已经使新闻自由变成一种侵害别人自由的新闻自由。大众媒介由一个约束、监督政府权力的机构演变成了独立的特权机构,“谁来监督和控制媒体”已经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四)从“人的延伸”到人的控制和奴役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曾经把媒介比喻成“人的延伸,”在他的笔下,媒介即万物,万物皆媒介,如石斧是手的延伸,车轮是脚的延伸,书籍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媒介是人体感官能力的延伸和扩展:文字印刷媒介是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是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延伸。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媒介已经越来越从人的工具性延伸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控制和奴役手段,大众媒介从人们主要的信息交流和传播载体逐步成了扼杀人的个性和思想的“麻醉剂”和“按摩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意见的自由市场”背后各种权力之手,正在默无声息地掌控着人们的观念。受众不过是枪弹射击下应声而倒的靶子,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正如陈兵所言:“因为先进的传播科技,受众观看、聆听及接触世界的方式越来越简单和直接,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公众的免疫力正在被蚕食。因为这种享乐主义,其实是引导媒体陷入虚拟贩毒的深渊。色情信息、暴力犯罪信息、失实信息、诽谤信息、侵犯隐私的信息正在成为媒体贩卖的毒品。”美国心理学家巴克指出: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愈来愈大,“随着依赖性的不断增大,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亦将愈来愈大”。同时,受众在电子图象、声音和低俗文字中流连,容易麻木于感官刺激。布热津斯基甚至把电视看作是恶魔,认为它导致了对公众新的奴役和控制,导致了越来越多人受制于媒介,产生了媒介依赖症,降低了对信息的辨别能力和免疫力,不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
三、大众媒介异化的政治后果
大众媒介功能的异化带来了诸多的政治后果,甚至有学者把西方代议民主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媒介的变异。尽管这种说法有些牵强,也有些“技术决定论的嫌疑”,但是,大众媒介的异化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对于代议民主的危机有着难以推脱的责任。总的说来,大众媒介异化造成了如下后果:
(一)政治参与水平低下——“没有公民的参与”
大众媒介从一种相对独立的体制外的监督批判力量,和代表民众公共利益的发声器等,逐步成了寡头集团统治下的工具。公民的身份逐渐向消费者身份过渡,在消费的世界里,那些刺激的、戏剧化的、娱乐化的事物注定是吸引关注的宠儿,而那些严肃的、与民生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政治事件却被边缘化。正如派伊所言:“新闻媒介将选举报道成一种政治比赛,由演讲、集会、记者招待会、游说以及也许还有辩论会等组成……而政治问题在选民的抉择中并未起多大的作用,这不足为怪,因为传播媒介不太关注政治问题。”这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公众慢慢地远离政治,漠视政治,处于娱乐的麻醉状态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对公众的信息轰炸也降低了民众对信息的消化能力和辨别能力,直接影响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效能感。人们常常抱怨新闻满天飞,过多的报道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应接不暇。电视总是倾向于向人们灌输多于他们真正需求的政治信息。大众媒介造成对人的思想的麻痹和奴役,加深了人们对政治的疏远。此外,大量负面消息的报道也加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对政治的厌恶与怀疑,导致的结果正如政治学家雷尼所说的:“对公众来说,政治通常是令人困惑、令人烦躁、令人厌倦、与生活中有关紧要的事毫不相关。”有调查显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比率每况愈下。从1972年到1988年,美国18岁到24岁之间年龄组选民的投票率降低了1/4。在1988年的大选中,这批人中间只有36%参加了投票。1972年,25岁到44岁之间选民的投票率为63%,而在1988年,这一年龄组的投票率降低到仅有54%。在30岁以下的美国青年人中,只有11%的人关注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首次高级会晤。就是在“柏林墙”倒塌、电视宣传登峰造极的历史时刻,这一辈年轻人中也只有42%的人在关注。他们中间有53%的人知道阿基诺夫人,仅仅是因为她曾经在一部有关菲律宾政府的电视连续剧中是一名主角。同样,在这辈人中间,了解导致美国国会发言主持人吉米·赖特下台丑闻的只有5%;认识国会发言主持人汤姆·弗利的,只有8%,这还是因为布什总统在发表一次重要电视讲话时,弗利正好坐在奎尔副总统的身边。美国这种公民参与的现状被形象地称为“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
(二)政治生态的失衡——政党政治的衰落和政治媒介化现象的出现
大众媒介还改变了原有政治的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力量格局。作为一种新的中介性政治力量,大众媒介与其他中介性力量如政党、议会等构成了一种竞争博弈关系。正如唐晓所言:“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格局,引起了西方国家权力的分配的变化。”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领袖可以借助传播媒介绕过政党和议会,直接诉诸民众,从而获得民主的认同和支持,造成权力的重新分配。美国一参议员甚至认为电视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电视极大地扩展了总统的权力,其效果如同一条宪法修正案正式地取消了政府三个部门之间的平等权力。”大众媒介造成的政治生态失衡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党政治的衰落和政治媒介化现象的出现。
美国学者班尼特和恩特曼在2001年提出了政治媒介化的概念,并指出:所谓政治媒介化,是指政治已经丧失其自主性,开始依赖大众媒介的重心功能,并持续被大众媒介的互动所形塑的现象页),并且在其《中介的政治——未来民主中的传播中》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介的政治传播已成为当今民主中政治与公共生活的中心”。从1952年开始,电视第一次介入美国总统选举过程,此后,电视逐渐主宰整个选举过程。电视介入政治给政治权力格局带来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以前的以政党为主轴的政治选举逐步变为以大众媒介为主轴的政治选举,帕特森形象地称之为“大众传播选举”。大众媒介逐步取代了政党的一些功能,从而使政党的功能衰退,具体表现在:(1)提名候选人的权力从政党转向大众媒介。(2)政党的忠诚度一直在下降,人们越来越关注候选人的个人风采和魅力,而更少关注其政策纲领。对于普通选民而言,政策纲领太复杂、太抽象,并不能吸引眼球,因为“电视播送的是图像,而不是思想;必须简洁明了,因为电视选民的政治水平并不高,而且电视又不适宜播放复杂的报告,而竞选成败与否恰恰取决于电视选民”。(3)独立候选人的出现进一步减少了政党的中介作用。有人形象地把这个现象称为电视民主、显像管民主、媒介民主等,也有人把传播式选举看作是“电视包装起来的特殊商品的销售”。
可以说,在媒体逻辑的冲击下,政党逻辑已经遭到严重削弱,政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在下降。媒体已经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意味着政治开始走向媒介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大众媒介造成了政治生态的失衡,“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传媒活动,现在的政治主宰者是那
些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和传媒行家”。
(三)社会资本的下降——“独打保龄球”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的一个概念,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都从本学科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布迪厄、科尔曼、林南等都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但真正使社会资本同政治发展联系起来、运用政治学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的当属美国学者帕特南。他在《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一书中从政治学的视角揭示了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并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它是摆脱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集体行动困境”的良方,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因素。
而在另一本著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中,帕特南却旨在反思现代科技特别是大众媒介给社会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现代美国社会发达的大众传媒削弱了人们的联系,阻碍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在现代社会中,繁忙的生活越来越让公众无暇顾及公共事物,而大众媒介的无孔不入和泛娱乐化的倾向导致了人们整日沉寂在电视当中不能自拔,而很少出去与其他人一起交流,使他们失去了与朋友或社团之间的来往。人们虽然拥有了更多的娱乐工具,但却使人际关系更加淡薄。于是,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公民社会的活力在过去几十年里明显下降了。”他这样描述道:“在当代美国,我发现社会参与减少的一些令人吃惊又令人沮丧的迹象是:与过去相比,今天有更多的美国人正在打保龄球,但是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组织的保龄球社团却骤然减少了。”这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公民精神在衰落,美国的资本在流逝。如果说19世纪公民热衷于结社并积极参与社区集体活动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国人是如此的独立(个人主义),以至于在闲暇时间再也不是去跟邻居聊天,或者参加社区集体活动,而是独自去打保龄球,或者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视,帕特南把这种状况形象地描述为“独自打保龄球”。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旨在重新唤醒人们对市民社会的关注,提醒人们警惕现代高科技给生活所带来的风险。而改变这种现状,大众媒介必须自我反省,否则公众将会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偏离正常的轨道越来越远。正如李献源在《传媒控制下的美国》一文中所担忧的:“只要美国的民主政治不能提供货真价实的品质和内容,这一代美国公民,包括他们以及下一代将要长大成人的美国公民,就会变得更加只关心那类带有惊险故事片刺激情节的社会新闻,和只关心自己小家庭的生活和周围小圈子的情况,而更加漠视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更加变得自我中心主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西方的媒体政治看似民主,其实是破坏了民主。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就说过:西方政党政治从本质上看,不是政党的逻辑,也不是媒体的逻辑,而是资本的逻辑。这一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大众媒介从一种民主的力量逐步成为一种反民主的力量,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和奴役力量,被形象称为“挣脱了铁的枷锁,却陷入了银的枷锁”。可见,自由竞争、解除规则并不是医治媒介异化的唯一良方;相反,市场本身也是一种控制和奴役手段,本身也能造成大众媒介的异化。正如过多的政府监管终究会带来政府失灵一样,同样,过度的市场化也会导致“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功能发挥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它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态,它的功能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选择性吸收”。如果说西方民主的现状(民主即选举)造就了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介的强势地位,那么,目前西方民主政治正面临治道变革,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强调更多的参与民主,主张更多的互动和参与。传统大众媒介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显得不合适宜,新的民主要求呼唤新型的媒介形态。所以,我们既要破除自由市场的神话,也要避免政府和市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思维;既要打破那种一劳永逸的静态思维,也要避免那种普遍化、绝对化的片面思维。大众媒介能发挥什么功能,应该发挥什么功能,是由现实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主题也不断要得到修正和改变。理想中的媒体和政治的关系是在政治和媒体之间存在一个理想的博弈机制:既能确保媒体相对于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又能充分发挥其在政治领域的能动性;既能保证其对政治的亲缘性和合作性,也能保证其适当的距离和张力,进而实现政治与媒体在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促进政治生态的平衡。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