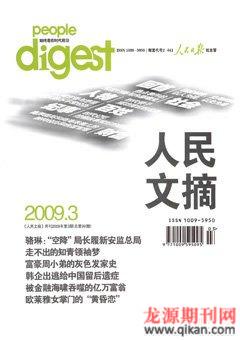茅于轼的乌托邦理想
白菊梅
“不能说,非要说;不能做,非要做,”这是业内人士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评价。过去几年里,茅于轼就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多个问题发表过一些“有悖常理”的观点,他也由此遭受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连番炮轰。尽管骂声不绝于耳,但他依然故我。
18亿亩耕地红线之争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面对记者,茅于轼对自己的观点依然不改初衷,“目前‘18亿亩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
耕地减少后出现缺粮情况怎么办?记者问。“可以向国外购买”,茅于轼回答十分干脆。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
茅于轼的这一言论通过媒体传了出去,在接踵而至的骂声中,多了“卖国贼”和“汉奸”的字眼。以往“出语惊人”之后,叫阵的大多是媒体和公众,而这次,学术圈里的专家也与他划清了界限。
茅于轼相信“市场是万能的”,但他显然忽略了一点——粮食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粮食和石油一样,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只要是战略资源,在国际上就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尽管茅于轼坚称“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但事实并不足以支撑他的这一观点。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2007年就提出警告,全球粮食存量处于25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粮食危机正呈现出蔓延趋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而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一旦中国缺粮,恐怕谁也供应不起。”国务院一位“三农”问题专家坦言。
曾有“经济学界的鲁迅”之称
采访中,茅于轼一直对记者坚称他的经济学观点都是“根据一些数据推导而出,并非拍脑袋的结果”。
“爱因斯坦写《相对论》从来没有调研过,都是经过数理逻辑的推导得出的,我也一样。虽然我的有些提法目前你们接受不了,不过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除非我国的城镇化没有进展。”茅于轼认真地说。
茅于轼对自己的理论从来都十分自信,但不争的事实是,近几年,他的这些观点却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而且,由于屡屡伤及大多数人的利益,曾有“经济学界的鲁迅”之称的茅于轼,渐渐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公敌”。
2007年1月,在某个众多房地产商云集的会上,茅于轼抛出了“只有廉租房才能帮助穷人解决住房问题,经济适用房只有缺点没有好处”的观点。对于廉租房,茅于轼建议,“廉租房不要修独立卫生间,只搞公共厕所。搞得不太舒服,才没人来抢,最穷的人才能住上。”网上反击声几乎是立刻响起,“不让穷人买房”“不让穷人上厕所”的指责不绝于耳。
2007年7月,茅于轼在某媒体上发表了题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他认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原因是为穷人说话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为富人说话则恰恰相反,所以都为穷人说话,没人为富人说话。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此文一出,反对、质疑之声四起,茅于轼也被迫继续写文章辩解。
2008年1月,茅于轼在参加一个论坛活动时提出“大学学费要提高”的言论。他认为,如果降低高校学费,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然而,这只是茅于轼的一厢情愿——“涨价论”再—次被指“荒谬”。
茅于轼为什么总是挨骂?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彻底的市场派。一切问题从市场观点出发。
彻底的理想主义者
茅于轼对数理推导的热衷和他的早期经历不无关系。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的桥梁专家。1955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开火车。那时,茅于轼的脑子里总是想着如何用最少的煤开动更多的火车,于是,他开始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1979年,茅于轼提出“择优分配原理”,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者。
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与相识多年的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在交谈中,茅于轼也承认,在经济学领域半路出家的他,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认识始终不是十分深刻,“我曾经一度提出土地私有化的建议,但考察菲律宾时了解到该国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民贫困,于是否定了这个建议。”一旁的夫人赵燕玲也连连点头,补充道:“茅于轼的性格特别木讷,连跟别人吃个饭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张嘴就说错话。他对社会的认识太简单。”
现实生活中,茅于轼是个对草根阶层有着深厚情感的“善良老头”。他创建“扶贫基金”,为民工提供小额贷款,还办过免费的保姆学校。“只要有人写信跟他说生活难、读书难,他就会给人寄钱,上了不少次当。我跟他说过很多遍,不要听信别人花言巧语,他每次都认真听,还不断点头,可结果呢,还是偷偷地去寄。”夫人发了几句牢骚。
茅于轼就是这么一个老人,80岁了,高高瘦瘦,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耳朵不太好了,要用助听器。可在接受采访时,他却不厌其烦地和你“较劲”,“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有人说我是乌托邦,其实我不是。”对于自己的理想,茅于轼依然保持着极端的热忱。
摘自《环球人物》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