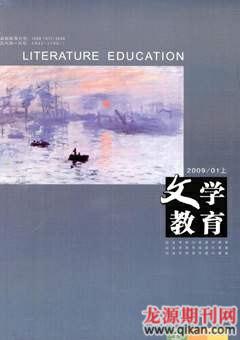《恨海》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
黄 瑶
吴研人的《恨海》以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为背景,描写了在动荡的时局中两对年轻人棣华与伯和、娟娟与仲蔼的情感经历,塑造出了棣华这一典型的近代女性形象。本文试从其女性形象、塑造方法及这一女性形象的成因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近代女性的典型:棣华
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棣华是被置于近代动乱时局背景中的女性。在她的身上,既有女性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意识,又有了隐约可见的坚强独立的萌芽,其命运与历史命运和传统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方面,棣华既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而具有贤良淑德的女性特征,有对自己有“父母之言、媒妁之约”的“丈夫”的依附,恪守礼教。她知书达理,逃难途中还不忘牢记“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自己和伯和交往时自重、自持。母亲病重时,她割股疗亲,呈现出孝女的风貌。棣华总是心思细腻,时常为别人着想。在逃亡的途中,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得知伯和境况后,表现出的关爱与宽容,在伯和离开后的巨大悲痛中,因为担心父亲而选择了出家,都标示了其身上具有的贤良的传统女性特征。棣华虽然与伯和最终未成礼,然而从过程来看,二人没有一条不符合传统的男女关系。在棣华看来,她早已确认了她与伯和的夫妻身份,以准妻子的身份为自己定位。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说:“实际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1]因而,她在精神上是依靠、依附于伯和的。纵使伯和最后堕落、消沉,她依旧对他不离不弃,从一而终。感情因此而愈见深沉与真挚。她的选择遵循了传统道德中对丈夫的绝对忠诚与对这种虽然还未成为现实的婚姻关系的坚守。陈仲蔼就评价棣华“又多情又贞烈”。
另一方面,在时代的大环境中,面临着新旧、内外两种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的碰撞,她有过挣扎和突破。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和近代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懂书文、会写字的细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进性。在第四回中,棣华写母亲的病情时,“那乡庄人家,看见姑娘们会写字,便十分稀奇,串讲出去。那店内的家眷……闻得棣华会写字,便走来招呼夸奖,称奇道怪”[2],可见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学习文化仍然不普遍,拥有学习条件和思想觉悟的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棣华虽然十三岁荒了书,但能读书识字也是一种先进的反映。面对混乱不堪的逃难生活,棣华亦有惊慌与恐惧,然而在母亲面前始终表现得勇敢而有主见,凭借自己的力量为母亲撑起一方天空的坚强与独立。如第六回中,面对义和团在天津卫放火的混乱局面,她一方面稳住母亲,另一方面查看实际情况,“心中不住的吃吓”,但为了让母亲宽心,她仍顶住压力“脸上不敢现出惊惶之色”,[2]愈发显出了她的勇敢与坚韧及对母亲的爱。与伯和重逢后,即使承受着来自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义无反顾悉心照料伯和,甚至“把药呷在口里,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里去”,[2]用语言和行动直白、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真情实感。
然而最终在伯和去世,其唯一的精神依附对象消失后棣华还是选择了削发为尼。当时急遽变化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沿革的传统观念使她不可能彻底跳脱已有框架的束缚,以“我”的独立姿态存在,加之失去了精神皈依,致使她又回到了传统女性的老路子上。
二、女性形象的塑造方法
在旧有的文学作品所运用的传统的塑造途径之外,笔者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一些表现手法,“倒叙、补叙、插叙、人物的心理刻画、肖像刻画以及自然景色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等许多描写手段的运用,都使这个时期小说的艺术手法、组织结构,呈现出了新的特色。”[3]文本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塑造出了棣华立体、饱满的形象,将这一可爱、可敬、又可悲的人物刻画得鲜活、生动。
全篇贯穿某些暗示性的情节设置为后文做铺垫,如第五回中棣华梦见伯和的车从身旁经过而没有理会自己,为后来伯和的浪荡与堕落做了预设,也昭示着她内心的隐忧与不安;伏笔的运用前后照应,使情节和人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有因可循,全文连贯流畅。如第一回中提及棣华不读书后,慢慢把读过的都丢荒了,为她后文中写病症和字帖埋下伏笔,为其知书达理和贤良提供佐证。在对棣华和伯和描写的过程中插入娟娟和仲蔼的情感经历时,采用插叙、补叙,比对强烈,解读了娟娟与棣华截然不同的选择与命运,彰显了棣华的美德,使故事情节更完整、时代背景更鲜明、人物形象更丰满,避免了单一的顺叙而造成的单薄与平淡;在刻画另一个女性形象娟娟时,多以他人言语或视角来描写,所着的笔墨较少,多用虚写而文已自明,虚实相生,在无意识中与棣华形成反差与观照;以棣华与伯和的情感变化和个人经历为主线,以社会的变革和历史命运作为复线的双线结构,为情节的铺展提供了保障,为棣华的形象塑造给予了依托,两条线索相辅相成、密切相关。
此外,反复和蒙太奇手法的成功运用对形象的塑造更是功不可没。文本中多次出现棣华的“脸红”与“哭”的肖像、动作描写,将其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用反复强调了其恪守传统女性的羞涩与道德、贞操观念以及感情的真挚深刻。在提及和伯和在同一炕上睡觉时、母亲询问伯和下落时、店家五姐儿打听失散者时、用了伯和的被褥后、失散后找到吸食鸦片而堕落的伯和再父亲面前表示关切、起身去面见病中的伯和时“只觉得一阵脸红又耳热起来,脚下便软了……进的门来,又是一阵脸红”[2]、伯和对她笑时棣华都会红了脸。将女子羞涩的姿态刻画得立体充盈,而又不会因为反复而显得累赘单调,反而更显出了棣华的纯真无邪,对贞操的坚守和对伯和难以割舍的爱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观念的投影。而她的几次“哭”也是形式各异的,既有“眼边不觉一红”、“不觉柔肠寸断,泪珠儿滚滚的滴下来”的暗自垂泪,触动了心事的辛酸泪流,看见伯和颓丧状时不经留下的泪水,又有梦见伯和不理她后的呜呜咽咽的痛哭,失去母亲哭到“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痛失伯和晕厥后的大声哭喊,都似将她心中的隐忍与哀苦、疼惜与挣扎融化在了这一次次的泪水里,埋藏在这一声声哭喊里,其爱之深切都和着泪涌入眼前。
蒙太奇手法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展示了人物形象,使人物立体化、真实可感,对社会背景的交代更详尽、全面。如将棣华对伯和的思念与伯和的浪荡无情用了交叉蒙太奇的手法,滋生出强烈的对比效果。棣华心中始终被伯和装的满满当当,即使再见到吸食鸦片后的伯和也还是难以释怀,更是将其颠沛和不幸归结到了自己身上,“都是我害出来的,越想越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来”。[2]而伯和却不见悔过之心,视烟如命,用他的淡然和冷漠回应棣华的深情,可知棣华发出“怎能够剖了此心,给他一看呢”[2]的感慨时内心是何其悲凉!这一交叉手法勾勒出了逐渐割裂的两个世界,也描画了伯和的无情和棣华的痴情;而棣华与仲蔼、伯和与娟娟创造出了平行蒙太奇的效果。仲蔼和棣华一样都是重情之人,也深深为棣华的悲苦命运而遗憾感伤,而娟娟却也辜负了他的一片真情,沦落为风尘女子,似乎在第一回中,书写者就借李氏之口向我们暗示了棣华和娟娟的差异所在,“王家娟娟,人到甚聪明……说话举止也甚灵动……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终日不言不笑的”。[2]这种平行的写法,突出了棣华与仲蔼心之痴、情之切,伯和与娟娟的浪荡与堕落,加重了悲剧的色彩。
三、女性形象的成因
棣华这一女性形象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主客观因素的合力所建构起来的。
客观方面来说,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棣华的命运必然与中国历史命运、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庚子之变的发生,整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之中,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内有义和团的运动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外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入侵,既有对改革救亡之路的探索又有探索中的矛盾及失败。处于新旧时代激烈交锋中的棣华,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冲击,产生挣扎,进而寻求突破,而又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仍身负封建礼教枷锁,难以摆脱几千年来女性这一身份沿袭下来的传统束缚,也无法逃离时局形成的无形推力。“《恨海》的悲剧是微渺的个人挣不脱大时代大社会的巨链”。[4]
就作者的写作立场而言,作为男性知识分子,他既想寻求突破又难以脱离男性的角度来刻画和描写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女性形象。女性似乎成了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因而最终作者还是掩饰了女性自身的觉醒。“也许再没有哪种角度比男性如何想象女性、如何塑造、虚构或描写女性更能体现性别关系之历史文化内涵的了。”[1]文人往往“对古典主义的爱情观默认,古典主义的爱情观是使爱情服从于责任意识、道德标准和最高的价值体系。在男权社会的漫长时期里,女性人生是依附于男性的。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与价值就在于找到好丈夫。”[5]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礼教的弊端日渐暴露在世人面前,作家仍然难以在一时完全脱离传统长久以来的压制,思想上难免有保守和消极的成分,加之其男权制思想的控制,棣华的形象切合了抒写者的潜在意识形态并以具体的人物作为阐释。长久以来,“男权制有一种男性认同——核心文化观念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的。”“男权制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由男性铸造的社会将女性视为低下的。”[6]因而女性作为定位于男性之下的社会存在,其为男性所付出的一切都在这种思想认同下变得理所应当。
主观方面来说,主要归因于女性自身的依附、从属意识。“她们的选择不约而同的通向一种道德完满的极致。这固然也是为了免却苟活和失节带给一个妇女的种种不幸。但归根结底,这种完满和不完满、幸福与不幸福的所有结局都已经被社会所预定。”[1]这一时期的女性深受着传统道德、贞操观和男权意识的影响,还没有认识到其自身的意义与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始终以他人的利益出发而尽可能的避免自己所作出的有可能给他人造成伤害的选择,“民初女性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多数将女性置于辅助和顺从男性的地位,集中体现了女性视角的仰视特点”,[7]以致最后选择了遁入空门而求得逃遁与救赎。
自古以来,中国的女性更多的是以男性的附庸身份出现的,其作为一种象征体系,被符号化与边缘化。“正因为女性是卑弱的,因此女性就没有独立的意识,她必须要服从于男性,这就是女性卑弱论的思维逻辑。”[8]作为女儿,棣华要极力遵守孝道,屈从与来自道德的羁绊;作为准妻子,她恪守自己的情感,直到伯和病重才终于抛开了外界的压束,一心挽救伯和。然而这样的双重身份常常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这个奉献的过程本身也是女性自我意识弱化而转向无意识的过程。“传统文学中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有大多拘囿与女人的娇羞、情人的温柔、妻子的贤惠和母亲的隐忍无私等。”[9]在社会定位的约束与规范下,女性逐渐变成了一种物化的存在,走向“无我”之境,“自觉不自觉的接受男性中心准则,将自身置于‘第二性地位”,[10]她们的抉择并不是以“我”的话语传达的,而是与所谓的道德上的圆满相切合的,这也是她们的悲剧难以避免的症结所在。用“出家”聊以自慰、寻求解脱,其实质是对自我的封锁与禁锢,亦是对现实的回避与逃遁,投射出了中国传统女性悲剧的侧影。“‘出走又意味着封闭,既是心灵封闭也是人际关系的封锁。她只能在物质空间和心灵的空间里守望。生存的现实迫使女性游离与退避。”[5]
棣华是千千万万近代女性的缩影,从她身上可以窥见传统女性形象的一隅,亦不乏进步成分。创作者以其细腻的笔触和丰富多样的塑造方法为近代女性作了注解,正如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每一个作家在描写女性之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的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11]也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些借鉴与启示。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2]吴研人:《恨海》,吴组缃、时萌等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书店,1990年10月。
[3]程翔章、邱铸昌:《中国近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4]黄锦珠:论清末明初言情小说的质变与发展--以《泪珠缘》、《恨海》、《玉梨魂》为代表,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
[5]田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库——走出塔的女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6]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7]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8]王晓丹:中国近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发展,曲靖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第2期,2001年3月。
[9]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10]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1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
黄瑶,女,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06级基地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