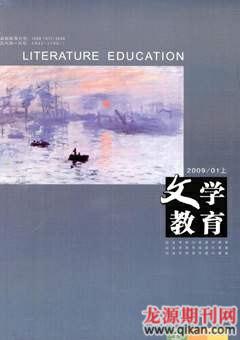曹禺的创作与女性形象两极化
曹禺,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在他的话剧艺术画廊里,无论是三十年代自由奔放、浓厚强烈的《雷雨》、《日出》和《原野》,还是四十年代素淡深远的《北京人》、《家》,曹禺的大部分创作中都塑造了触发矛盾和推动剧情发展的女性形象,如繁漪、陈白露、花金子、愫方和瑞珏等。但她们是两类近乎极端的女性形象,一类是以繁漪、陈白露和花金子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魔女”,她们极富生命力,散发着充满诱惑力的原始野性;另一类是以愫方和瑞珏为代表的爱的“圣母”,她们柔情似水,心软如棉,温顺柔弱。曹禺剧中的女性是寄托作家生命体验的载体,渗透创作主体的主观寄望。下面我将对这两类女性形象进行剖析,以其身上所承载的作家生命体验和创作自我为切入点,来探究曹禺创作心态和创作道路。
一、疯狂的“魔女”
“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镜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1]曹禺对繁漪的刻画更多观照于她的“魔性”上。繁漪的“疯狂”主要是由于“周家式”魔鬼宫殿对她精神和肉体的禁锢造成的。于是她变得异于寻常,疯狂地爱上丈夫前妻的儿子,在与周萍乱伦、变态的畸形关系中,背弃了作为母亲的神圣天职。繁漪的“疯狂”使她一方面更痛恨现状,另一方面也使她理智缺失,爱上一个实质上与周朴园无异的周萍,以致在周公馆上演了“客厅闹鬼”,又与四凤争夺情人,用计辞退四凤;更是在狂风暴雨的夜晚,不辞辛苦地尾随周萍到鲁家,如幽灵一般在窗外窥看周萍与四凤幽会;在周萍和四凤决定双飞时,繁漪痛苦愤怒到极致,不顾一切人伦关系,撕破虚伪的面纱。这一举动就如同那夜的雷雨,劈裂了黑暗,将隐藏于黑暗中的丑恶暴露于人前。一番狂风暴雨过后,繁漪最终也没有逃脱女人的命运悲剧:当周萍随着不该毁灭的周冲和四凤而毁灭,而应该毁灭的、以周朴园为象征的男权却没有毁灭时,繁漪最终成为真正被禁锢在阁楼上的疯女人[2],在由周公馆改造成的医院里,永远接受周朴园的怜悯。
《日出》中的陈白露是个挣扎于黑暗敏感的交际花,她在豪华的旅馆套间里接待各种各样的人物。较之繁漪由窒息的“囚牢”生活逼出的“疯狂”,陈白露的身上多了份在糜烂的“开放性”生活中作为一个“清醒”人的痛苦。她对自己的生活困境和社会黑暗过于清醒,无法麻痹自己,每当奢华过后,夜深人静时她就感到一片空虚,在丑恶的生存环境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陈白露最终选择了自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3]没有必要等待拯救,“睡了”似乎是对她这样一个渴望日出、却又无法摆脱黑暗桎梏的女人自救的一条出路。当年的曹禺和陈白露的处境一样,面对残酷生活和社会感到绝望,然而现实中作为男性,其面对困境毕竟与女性有差异,曹禺仍渴望有新的血液、新的生机,因此,《日出》还是在一片高亢的工人合唱中落幕,方达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陈白露却毫无留恋地“睡了”。
“女人长得很妖冶,……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走起路来,顾盼自得,自来一种风流……她的声音很低,甚至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4]花金子一出场,曹禺的这番叙述话语就给她定了形:原野里的一朵“野”花。原野里特有的大地的辽阔苍茫感染了花金子原始蛮性的生命力,造就了她大胆泼辣、纯真厚实的性格。金子比繁漪更“疯狂”,在她身上女性的反抗和欲望升级到最高峰。在金子的眼里,只有爱与不爱,没有该不该爱。金子在焦家非正常的生存环境中,她是“死了的”。在与仇虎重逢后,浑身散发着野性和生命力的仇虎,唤醒了她生命的激情,她不顾名节,与仇虎相爱了,虽然爱得偷偷摸摸,但她却感觉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为获得真正的生命存在和爱情生活,她抛弃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与仇虎逃到原野去。金子和仇虎一样是欲望的主体,但是一个有欲望的女人始终不能像男人一样被社会接纳,她要背负不道德之名,即使在金子随仇虎出走后,也只不过是再次坠入完成一个道德责任的深渊:在仇虎自杀后,她要承担起一个男人付托给她的母亲的“天职”。出走后的金子又在原野中迷失了。
二、为爱而生的“圣母”
40年代初创作的《北京人》和《家》,曹禺以他另一种生命体验,塑造了一类截然不同的理想女性,她们负载了作家的美好情愫和向传统复归的创作转变,也体现了作家的另一种艺术审美标准。
《北京人》里的愫方是个幽娴的女子,如空谷幽兰一般惹人怜爱,她有别于之前作品中的叛逆女性形象。从作家的描写可以看出,她是外在美和内心美兼修的女子,婉顺哀静、善良无私、温柔大方,她身上承袭了妇女所应有的美德。她有她苦难的爱情观:她愿为爱牺牲。她爱曾文清,把毕生的幸福放在他一个人身上,情愿守在生命的囚牢,用沉默把一切苦难都吞下去。“看着人家快乐,你不也快乐么”,[4]愫方将此奉为她的人生哲学,她把温柔的关怀给予了周围所有的人,唯独忘了她自己。她用温柔的目光和安慰的话语给苦闷不堪的曾文清以鼓励,给苦恼寂寞的瑞贞以帮助,就连对她尖刻凶狠的曾思懿和把她当佣人使唤的曾皓,她都毫无怨言地付出,就在这样的隐忍中迷失了自我。当然,曹禺始终不忍让这样美好的女性形象死去。在愫方的全部希望破灭后,曹禺安排了她与瑞贞一起出走。但是背负着那套爱情观和生命哲学的愫方,出走后又将会是怎样一番境况?曹禺留给我们悬念,这份没有言明的苦心似乎暗含了作家对愫方这一类女性的美好期望。
性情温柔天真,和蔼可亲应对进退都融融和和的瑞珏,仅十七岁就嫁进高家。她无微不至地体贴丈夫,为了更多地了解他,弥补自己知识的贫乏,她偷偷地看新书;为了觉慧的《黎明周报》,她捐出自己的积蓄;为了爱,甚至真诚地希望用自己的痛苦换取觉新和梅的结合。她也有着一套和愫方一样的极富牺牲精神的爱情观,“一个女人爱起自己的丈夫来会爱的发疯,真是把自己整个都忘了的”。[6]相比愫方,瑞珏的形象更多地负载了作家对完美女性的理想。受制于巴金原著中瑞珏最终死于难产,曹禺在改编的剧作《家》中,似乎不忍寄予了他不少感情和理想的完美女性死去,他把瑞珏的死写的极富诗意的凄美,在一片杜鹃声的写意环境,瑞珏生命弥留之际还在担心自己的丈夫,并表示自己很幸福,这是否意味着曹禺有意无意只让瑞珏的肉体死去,而让其为爱奉献牺牲的精神永留?
三、女性形象的两级分类与曹禺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道路
从《雷雨》到《原野》期间的曹禺,就像一个浪漫热情的诗人,奔放的感情火焰燃烧着他,塑造了一类锋芒毕露的魔女,她们疯狂、迷失。《北京人》之后,曹禺渐渐如一个冷静的画家,偏向肯定那些温柔娴静的女性,在她们的身上只感受到爱的温馨,不再有繁漪式的情绪。曹禺在他的剧作中选择女性的处境和挣扎来形象化他的情感与理想,“魔女——圣母”这两类女性形象寄托了他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因此她们表现出了不同的生命形态。
“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态度,直接源于男性回归自我又逃避自我的矛盾心态,‘两极化创作模式由此而生。……”。[7]“魔女”式的女性形象是他前期创作回归男性自我的体现,当时作家的创作心态表现的激昂热烈,焕发着少年意气。曹禺开始创作时恰逢“五四”运动,追寻民主的思想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而曹禺自幼就在一个没落的旧家庭里成长,被缚于因袭的畸形社会而苦闷懊恼。因此,在他前期剧作中,他追求的是生命的快感和个性的自由,反抗的是对爱和情感的压抑,繁漪这一类疯狂的“魔女”对情感的大胆追求正符合曹禺表现他创作心理的需要。但是毕竟由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的性别差异,曹禺作为男性审美主体所要变现的男性生命自我,在现实中一般女性是无法负荷的,所以作家只有将繁漪、陈白露和花金子身上的原始的蛮性夸张放大,使她们有别于一般女性,才足够表现作家这个阶段的生命体验。而作为爱和奉献精神化身的愫方和瑞珏,这类女性形象是曹禺后期逃避自我的创作倾向的产物,她们是负载了作家美好情愫的完满女性形象,作家创作心态上也更多的表现出对传统的回归。这一由反抗到回归的转变与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和作家步入中年后的人生阅历密不可分。随着4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重,时代氛围由追求个性解放转移到民族解放、文化氛围上,与曹禺同时代的作家致力于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的精华。曹禺在创作上也由极力表现反抗和欲望,转向对完美社会人的刻画。愫方和瑞珏这类有东方传统女性道德的女性就成为曹禺这一阶段创作心理的最佳阐释对象,她们负载着曹禺对传统女性的温柔坚强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追求。另外,曹禺在创作中也注入他对爱情的体验。四十年代曹禺经历了一次情感的波折,他与长相清秀、性格娇柔的方瑞相识。与方瑞的这段婚外情对曹禺创作心理上对女性形象的选择是有一定影响的。
从曹禺笔下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命运结局,可以总结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被作家赋予无限激情和生命力的繁漪、陈白露和花金子,在疯狂地反抗和挣扎过后,始终没有避免悲剧命运,分别走向禁锢、毁灭和迷失:繁漪精神分裂,陈白露吞药自杀,花金子失去一切希望。而相反,那些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传统女性形象,作家对她们倒是寄予了美好希望和憧憬。愫方最终迈出艰难而有希望的一步,和瑞贞去开拓新的生活。瑞珏虽终难免一死,但作家还是将她的精神长存。从这一角度看,早期回归自我阶段,曹禺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快感,到了后期,曹禺似乎找到了生命的所在,倾向肯定一种生存意识。另外,从花金子和愫方,两个同样是从“家”出走的女性的结局,也可以看出曹禺的创作道路日渐向社会规范靠拢。金子在抛弃道德规范,置种种威胁于不顾,甘与仇虎冒死逃离后,等待金子的却是在仇虎倒毙在黑森林的边缘,一切希望都丧失,只得重归对于妇女来说的另一条道德之路——生下她和仇虎的孩子,尽一个母亲的责任。金子还是不能走远。与金子狂野炽热的爱情形成鲜明对比,愫方为着所爱的人能够从痛苦的深渊中获得重生,心甘情愿地守着生命的囚牢,毫无怨言地为曾文清乃至他的亲人消耗自己短暂的青春。直到曾文清重归,幻想破灭,她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才决定自救,毅然地出走。这样看来愫方走的是一条有“希望”的路。但从我们所分析的愫方的爱情观和人生哲学来看,出走后的愫方必然也是寻找另一位能赋予她生命意义的男子,全心全意地付出她的爱情。两个绝然不同的女性,在出走之后都是走上了一条得到社会规范和主流意识形态等外在东西的肯定的道路,而这条路也就是当年曹禺所找寻的“正路”。[8]
参考文献:
[1]《曹禺文集》(第一卷),田本相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雷雨》第一幕,第39页。
[2]《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增订版),陈顺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65页。
[3]《曹禺文集》(第一卷),田本相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日出》第四幕,第443页。
[4]《曹禺文集》(第一卷),田本相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原野》序幕,第490页。
[5]《北京人》,曹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154页。
[6]《家》,曹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第148页。
[7]《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李小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22页。
[8]《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曹禺,《文艺报》,1950年第三卷第一期。
[9]《试论曹禺前后期剧作中的两类女性形象》[J] 张浩《广东社会科学》 2001年01期。
[10]《曹禺戏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J]刘芭《名作欣赏(学术专刊)》 2007年09期。
[11]《论曹禺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女性意识为关照视角》[J]蒋乐进,吴寒《巢湖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关姗姗,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