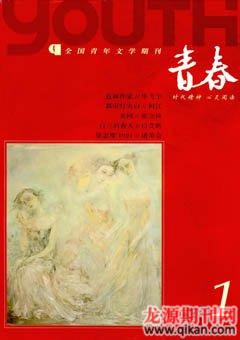路过麦当劳
宁 默
一
下午的太阳还是很热,背上都粘湿了,秋季的汗总是让人不舒服。她耳朵里插着MP3,背上一个斜背的大挎包,站在麦当劳的门口。空气里是烤鸡的香味,街上是形形色色的人。她注意地看了好久,那么多的面孔,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长的方的胖的瘦的,居然没有一张熟悉的。她熟悉的人——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算来也有一大群,可是比起眼前大街上的人,还是太少了,千万人中或许才能遇见一个熟人,千万之一的比例。她向来对自己的运气不抱信心。可是她并非为遇见熟人而来——大门被不断地推开,又不断地关闭。一个女人站在灯箱前打电话,不时朝着面前的空气撒娇,身子一扭,胸脯便一抖。她的声音盖过了街对面服饰店传出的周杰伦的歌声。公交车气喘吁吁地蹭过来,放出了十来个汗流颊背的人。一下车,这些人就消失了,仿佛水滴消失在大海。只有一个穿黑T恤的男人走进了麦当劳。她有种窒息的感觉。每当她使劲思考一个问题,就会有这种感觉。黑T恤是不是她要等的人呢--故事的开头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等待的人,引出许多被等待的或不被等待的人。
她从屁股后的挎包里掏出手机,想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在等他。她在手机上摁了好久,却找不到他的号码。她的手机号码簿里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她喜欢用英文字母或者阿拉伯数字来代替人的名字。现在那些符号就像蝌蚪一样朝她挤来,她无法确定他是其中的哪个蝌蚪,她甚至也不能确定有没有问他要过号码。她又产生了窒息感,只好仰起头看天。天蓝得像水晶。却有一个穿拖鞋的男人晃晃荡荡地走过来,擦过她身边,忽然小声问:要不要碟子?她白了他一眼,往旁边走了几步,那儿有一根广告柱,柱子上端的牌子上有一个坐着的女人,美妙的大腿微微分开,一双男人的手在大腿前打开了盒子,钻石瞬间放出光芒。图片的好处是能够牢牢抓住那瞬间的光,让它在半空中长久地闪耀。于是女人的腿永远微分。
又一个男人朝她走来。
就像电影画面一样,他越过一道又一道人流,坚定地朝她走来,靠在了广告柱上。他们对望了一眼。他穿着深蓝色的衬衫,眼睛里有微微的笑意,看上去很温暖。她喜欢温暖一点的男人,就像阿磊那样。阿磊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做我的新娘,我的两爿汽车美容店都归你管理。说这话的时候他连眼睛都在笑,她知道那表示他是真诚的。这的确是阿磊说过的最真诚而又最虚伪的话。当他又招收了一批女服务员之后,他就不再到她的小屋去了。没多久,她也换了工作,并且很快就记不起他的样子了。要不是看到眼前深蓝色男人的眼睛,她也许永远都不会想起他。
现在,她和他,一个无所事事的女人,一个来意不明的男人,站在同一根广告柱下,应该有一些故事可以发生,小说中都是这样设计情节的。她的脑子开始播放画面,他深情款款地走近她,对她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她幸福地笑着,等待他的拥抱。他打开车门,殷勤地邀请她上车--事实上深蓝色男人在马路那边的确有一辆汽车。她不记得他们对望了几次,他首先开口:陪我去兜兜风吧。口气坚定,根本不需要她的回答。
他的车里有一股劣质的清新剂的味道,她不喜欢闻。他问她喜欢听什么曲子,她想起刚才听到的周杰伦的哼哼声。汽车在哼哼声中上了城市的高架桥,她有点昏昏欲睡了。
梦里深蓝色男人抱住了她。他们赤身裸体。车里很暗,她看不清他的脸。从窗外一个又一个粗大的水泥柱子看,这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周围安静极了,他的喘息声格外粗重,伴着座椅偶尔的吱吱声。男人把她抱得紧紧的,她闻到他从鼻子里喷出的气息,很清新,没有一点异味。她享受着他的温暖,一边用脚悄悄地将窗户打开了一丝缝。她从报纸上看到,做爱的男女死于密封的车内,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的身份。微微的光线从缝隙里透进来,她仍然看不清他的脸,车内弧线形的小小顶棚护佑着他们的激情,她想起家,想起母亲的子宫。
他终于平静了,他们穿好衣服。她问他现在到哪里去,他说送你回家吧。她点点头。
她记得她最后朝他挥了挥手,他在车里坐着,车窗缓缓摇上,车子很快消失在车流之中——跟电影画面一样。每次她的回忆进行到这里都会被叹息打断,她觉得美好的事情总是结束得太快,也许应该问问这个深蓝色男人的名字或者电话,但是也许问了之后就再难保存这段纯粹的记忆了。她习惯了凡事顺其自然,该来的来,该走的走,恰似风流云散,各归其命。
就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岁渐增,她喜欢在回忆里打发多余时光。在回忆里她总是青春不老,并且奇遇连连。虚拟的生活绝对比现实的生活扣人心弦。有时她觉得自己不仅是优秀的梦想家,也是个不错的哲学家。
翻了半天,她终于从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本。她想也许那里记载着他的号码。可是电话本上也是一串串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她根本无法从那些符号里找出她要的号码。她想不起自己的这个古怪习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在带给她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麻烦。她沮丧地放弃了寻找,脑子里仅存的关于他的信息就是麦当劳。可是麦当劳与他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当她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其中也存在着荒谬,因为他们既不曾在麦当劳吃过东西,也不曾在麦当劳见过面,甚至根本不曾谈到过麦当劳。女人的直觉果真经不起推敲。
那么什么才是他们之间的联结呢?她揉揉发涨的太阳穴,怎么也想不起来。屋里遍布着各类布偶,公主和狗熊们躺在一起。茶壶干了,橘黄的靠垫一个在沙发上,一个在地上。还有翻开的杂志。几张写了字的纸。失水的苹果。没有盖子的药瓶。半掩的门。浴缸上反光。擦过窗玻璃的风声。楼下孩子的尖叫。女人的笑。汽车的轰鸣。头顶的星辰……所有这些,都熟悉得可以无视,却没有一样与他有关,她无法从它们身上找到他的任何信息。她想,之所以它们容易被忽视,是否就因为它们构不成事实呢?
她对着镜子点了点头。镜子里的女人也对着她点了点头。
二
她被电话铃惊醒了,翻了个身,用枕头压住了耳朵。可是铃声还在继续。是母亲。母亲说,老秦家的阿柏和女朋友吹了,老秦一直唠叨着让他来见你。还有,老家的房子要拆了,那里要建工厂……她有二十年没回过老家了,可是老家的每个人每个屋子依然熟悉,多年来母亲絮叨的主题一直是它。挂了电话,她钻进被窝继续睡,迷迷糊糊中就走进了村庄,人们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回老家去,他们说你的老家在哪里呀?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她没有地址,没有门牌号,没有电话号码。尽管老家的每个人每个屋子她都熟悉,可是她还是迷路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可理喻。
老家曾有很多童年的玩伴,如今他们大多散失于各处,再也聚不拢了。很多人都是这样聚了又散了,没有理由。爱拖鼻涕的阿柏总是需要借她的作业本。阿柏的爷爷有一个红灯牌收音机,每天黄昏,他都会跟着收音机咿咿呀呀唱京戏,她和阿柏伏在桌子的另一边做作业。她听得清的只有一句: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她不懂君子是什么意思。多年后她的暗恋对象对她说,我们只能是君子之交。她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她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学校图书馆,当时他正在看一本杂志插页中的麦当劳广告。她走到他身边坐下。他说他很忙,因为英国那边的学校已经落实好了。你要照顾好自己!他拍着她的肩膀说。他的上嘴唇正中有颗痣。他离开了很久了,她仍是喜欢对着手背上的痣想着他的痣。
起床,洗漱,下楼,上街。又是这条街,又是这根广告柱,不由自主。一辆摩托车呼啸着从她身旁擦过,吓了她一跳。穿睡衣的女人推开小吃店的门,将一盆污水泼在路沿下的下水道中,顺便使劲擤了下鼻涕,那声音仿佛撕裂了什么,空气中弥漫起一股黏湿的腥味。一男一女迎面走来,她的目光和男子的目光碰在一起。他的眼睛很亮。她觉得有时候一眼的感觉也可以很长久。她想起在单位的产品推广会上遇见的一位男士。在众多的男士中,他的浓金色的领带显得特别亮丽。当她注意地朝他看时,正巧他也回头朝她看,他们的目光瞬间碰撞了一下。她迅速低下头,专心地看手里的签到单,等她再抬起头,他已经无影无踪了。第二次碰到他的目光是在散会时,她跟在一群人后送别客户,在拥挤的门口,他又一次回头,她的目光便在瞬间接住了他的,她的心跳莫名地加速了。他收回了目光,只是一眨眼,就消失在人群中了,就像水滴消失在大海中。有时她很奇怪,为什么会对这两次回首记忆如此清晰,而有些不需回首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却忘得很快。
陌生人的眼睛让她陷入了恍惚。麦当劳门前依然人来人往,她低垂着的眼睛看见许多穿着牛仔裤的腿,长的短的,肥的瘦的,男的女的。爱穿牛仔裤并且能把牛仔裤穿得好看的只有陈致。她跟陈致相处了三个月,这应该算比较长的时间了,然后他也像水滴一样消失了。他说他是杂志编辑,她问是什么杂志,他回答过好几次,然而她至今都不曾记住那个名字。陈致每天八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家,中午他们会一起吃饭。无论工作还是休息在家,陈致总是穿着牛仔裤,他的腿修长笔直,穿着牛仔裤感觉特别好,她迷上了他的腿。她称他“我的牛仔”,他称她“我的小猫”。有一次她把他新买的名牌牛仔裤两条腿上都剪了个洞,他非常生气,差点把手里的杯子都摔了。她说那是猫爪子抓的,怪不得她。他就笑了起来,把她的头发揉得纷乱,并且不再生她的气了。他的脾气真是没说的,可是也许是因为太近了,她觉得他实在缺乏激情和个性。当她说要换个环境生活了,她看见他眼睛里的痛苦。他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她飞快地摇头否认。他低下了头,第二天他就消失了,连同他所有的牛仔裤。后来她曾经想过去找他,可是因为没有记住他的杂志名称,她的寻找就显得漫无边际,最后只好打消了主意。
其实,生活中的遇合比故事中的更快更不可预料。故事是虚构给人们看的,而生活是个人的真实,无法逃避的真实。然而她总是在试图逃避,期待着某种奇迹的降临——事实上她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奇迹。
陈致走后,她很快又带回一个男人。那是她在住处附近的菜场里遇见的一个年轻男人,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把吉他。一开始她以为他是乞丐,说好听些是落难艺术家。可是男人拿着吉他却并不使用它,他跟在她身后,要求给他一个馒头,或者一根油条,因为他太饿了。她在热腾腾的早点摊头为他买了两个肉馒头,他狼吞虎咽地吃了,陪着她买好了菜,帮她提到家。在开门的时候她有点犹豫,该不该邀请他进去呢?在她还没有打定主意之前门就开了,男人把菜拎进了她的厨房。男人坐在客厅的地上,说想睡一觉,因为一夜没睡。她拒绝了,因为她得上班去,屋子不能留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可是他一直在哀求她,他实在没有地方去,他必须睡一觉,才有精力筹谋后面的生活。她只好锁起了所有可以锁起来的抽屉和橱柜,他毫不在意地在沙发上发出了鼾声。下午她匆忙赶回家,发现他已经走了,沙发上的毛毯折叠得整整齐齐,冰箱里能吃的都不见了。后来的两天她一直细心梳理着屋里的物件,她想也许他还顺手带走了一些什么,可是她再也不曾有新的发现。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乞丐,落难艺术家,还是跷课的学生,逃婚的情人?关于奇迹的幻想总是五彩斑斓,像肥皂泡,一个个升起,又一个个破灭。
她还认识一位同一小区的女孩子,她是园艺师,非常喜欢插花。有一阶段园艺师每天都会买一束花来到她的小屋,为她摆出精美绝伦的插花造型。园艺师有着男人般的嗓音,园艺师喜欢用骨节粗大的手抚摸她,园艺师吻她的那天遭遇了车祸,死了。
三
当阿柏提出要在麦当劳门口见面时,她吃了一惊,并且本能地否定了。在这条街道上,她已经习惯了无望和茫然的等待,要是她的等待忽然有了结果,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她站在了地铁口。
很多小说或者电影都喜欢将邂逅的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地铁口,所以指责她矫情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人多的地方能让她觉得安心。
自动扶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他们从扶梯上出现,又从扶梯上消失,更多的人站着或走着,看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容。像那天的麦当劳门口,阿柏说他的手里会拿着一份晚报。于是她也买了一份晚报,在过道中的椅子上,灯光将人影层层叠叠地压上她的报纸,她看了几个标题就头晕了。抬起头,忽然发现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晚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过道那边有个卖晚报的老大妈。
她茫然了,她的寻找又一次变得无所凭依。二十年前的小邻居,她根本没有把握从人群里认出来。踌躇了好一会,她决定碰一碰运气。在第九个手拿晚报的男人出现时,她走了过去。嗨,她招呼道,你是阿柏吗?
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有着浑厚又清亮的嗓音。几句似是而非的对白之后,晚报男人对她说,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呢?就像电影里那样,他们步履暧昧地来到咖啡屋。晚报男人很健谈,因为陌生感尚未消除,她说话不多,多数时候是他在说话,他的嗓音不仅让她的耳朵舒坦,连心也渐渐安宁了。他滔滔不绝,讲手机短信笑话,还讲他朋友的糗事。他的朋友和人网恋八个月,见了面才知道是一个办公室的。说到这里他笑得喘不过气来,她附和着他笑,并且希望这种笑话永远没有讲完的时候。最后她又问,你真是阿柏吗?晚报男人想了一会儿,圆滑地说,明天我们再来喝咖啡,那时候告诉你。
第二天下班时她接到了晚报男人的电话。她在电话里打趣,娇笑,仿佛认识了很久的熟人,事实上这一天她都在回味他的声音。接下来的三天,他们天天在咖啡馆见面,喝咖啡,他给她讲笑话,她笑得咯咯的,脸色绯红。那个验明身份的问题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第四天,她走进咖啡馆的时候,看见晚报男人身边多了一个卷发男人,他们正谈得眉飞色舞。晚报男人说他们是同学,几年没见了。他们要了一些零食,她一边嗑瓜子一边听两个男人吹牛。卷发男人说话时面部表情极其丰富,而且总是伴随手势,要是她沉默的时间比较长,他就会对她说,你说是不是呢?或者说,再来一杯咖啡怎么样?
说话中邻座有个女孩忽然跑过来,用某种方言冲着晚报男人大喊大叫,晚报男人也大喊了一声站了起来,四目相对,一脸惊喜。那女孩子纵身入怀,勾住了他的脖子。他们搂抱着就出去了,她甚至都来不及吃惊。卷发男人抽完了两支烟,晚报男人才回来,他说很抱歉不能陪你们了,她还在门口等我。他匆匆穿好外套,一脸幸福地大踏步走了。卷发男人对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重色轻友。
后来他们两个也走了,出门时她打了个喷嚏,他及时递给她手纸。他们找了一个小饭馆,喝了点红酒。借着这顿酒,她知道了他的名字。她凑在他的耳朵边说,阿淼,你把我灌醉了。阿淼说,没关系,红酒养颜。
接下来她依然天天去咖啡屋,不过见面的人成了阿淼。后来阿淼才告诉她,他其实并不喜欢喝咖啡,他的胃不好。她为此深感歉疚,并再次感受到了他的体贴。于是他们把见面地点改在他的临时租屋里。他做的炒饭特别好吃,他说那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十多年的经验了,从上小学开始,他就天天早晨给自己做炒饭吃。吃过了饭,他们喜欢坐在地板上一起看杂志,她看服饰类的,他看军事类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她又一次感到了内心的温暖。有时她偷偷看着他黑亮的眉毛和光洁的额头,巨大的荒谬感会让她恍惚起来。每当这时候,他会将脸凑到她鼻子前,偷看我了吧?他坏笑着说,我是不是太帅了?她抿着嘴笑了,而且一笑就笑个不停,他把她扑倒在地,胳肢她。他们满屋子追打,就像小时候玩游戏一样。
后来她才发现阿淼也具有男人的通病,他懒得洗衣服,他总是在她来之前将脏袜子和短裤踢在床底下。她将它们找出来并且开始清洗的时候,他羞涩得就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有时候他确实像个孩子,在逛超市的时候,他一口气给她买了四个布偶,两个公主和两个狗熊。要让它们一对一对的,他说。他抱着四个大布偶在街上横行,咧着嘴巴唱歌。她跟在他身后,笑得眼泪直流,一点都没觉察早已路过了麦当劳。这真是奇迹。
有一天下班回来,他兴冲冲地叫她过去,他烤了牛排。他叉起一小块送到她的嘴边,味道怎么样?他急切地问。她觉得味道再好也没有了,在这个阳光即将沉落的深秋,窗外的树枝已经是光秃秃的了,可是她面前却有一桌丰盛的晚餐,一个男人正急切地等着她对于牛排的评判。她深深地点了点头,生活如此触手可及,她愿意这样的生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不再有意外来打扰。她拉着阿淼来到阳台,闭上眼睛,向冥冥中的神许了一个最真诚的愿--却忽地感到了窒息,某种恐惧在心底蠢动,像蜘蛛细长的爪子在抓她。
她紧紧地抱住了眼前的人。
果真,从这以后,她的夜不再是漫长无眠的了,每天一关灯,她就能迅速沉入酣睡,做一些甜蜜细碎的梦,醒来之后什么也不记得。她脸色红润有光泽,步履轻健,微笑着和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目光对视,并且再也不曾一个人去过麦当劳。她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幸福——直到有一天,电话铃忽然响起。她迟疑地坐起身,已是凌晨两点了,谁会在此时想起她?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穿越了半个地球,在电话彼端轻轻地问:你好,还记得那颗痣吗……
责任编辑裴秋秋
作者简介:
宁默,本名谢华,女,出生于七十年代,江苏作协会员,以散文和小说创作为主,作品散见于《雨花》、《青春》、《散文》、《山花》、《作品》、《散文诗》等纯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