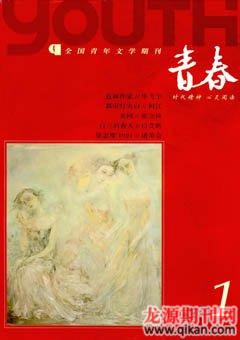美网
张立民
我轻轻按了一下门铃。
“你回来干什么?是不是吃了人家的闭门羹了!”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气呼呼的。但是声音并不难听,脆耳?对,脆耳动听,就是这样的声音,尽管口气里的怨恨有一定浓度了。前天,同学和我聊天时,说她的一个女朋友的声音脆耳动听,我一时难以理解。我感觉了一下我妻子的声音,好像不怎么脆耳。当时我就告诉她,我不明白脆耳动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同学狡诘地问:“要不,叫她明天打你一个电话?”“不,不了,我经受不起,不要打。”我哈哈笑着,窘迫地回答。
我望了一下铁门旁边亮着灯光的玻璃窗。是磨沙玻璃,不太透明。女人的声音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玻璃窗稍微裂了一道缝,却是朝门边裂的,我试图侧头朝那缝里张望,但是只是轻微晃动了一下脑袋,并没有真正去张望。我想这是不礼貌的。我感觉这应该是关羽家的卫生间。这个小区的房子我比较了解,我曾经在其中的某一套房子里违心地参观同事家的装潢。我对装潢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觉得装潢和装潢说明书一样无聊。但是我却因此了解这个小区套房的基本结构。对了,应该是个卫生间。果然,里面响起来了抽水马桶的声音,一个女人瘦小的身影从马桶里站了起来,只和我隔了一块窗玻璃。我通过亮光依稀看到女人影子的晃动和弯腰的动作。她的头发感觉有点散,弯腰更使头发朝她面部方向垂下去。长头发的她低头看着自己的下部,令人窒息般地停顿了几秒钟。影子的行为使我又开始窘迫起来,但是我并没有停止注视,我想这就是我猥琐的地方。里面的影子又动了起来,她很懊丧地把自己的内裤往上提,甚至在提到腰边时发出内裤的宽筋弹击腰部皮肤的“嗒“的声音。也脆耳动听。然后她又往下提裤子,外面的裤子,可能是睡裤,也可能是短脚便裤。
我感觉到时间有点长了,难道关羽没有听见?便下意识地再次拨打了关羽的手机。还是关机。这小子忘了充电了?真过分。我又轻轻按了一下门铃。
“你难道没有带钥匙?”卫生间里的女人的声音明显柔和了不少,她的责怪在我听来,已经是表面上了。我想起了我妻子,她说这样话的时候往往是来开门了,也就是说,“难道你没有带钥匙”和“我来开了,别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我心里漾起一阵暖意,随即又马上自责起来。陌生的,这是陌生的地方,里面有我的朋友和一个从没见过面的他的妻子,他的家我也是第一次来(尽管每次把关羽送到楼下时他总是叫我上去坐一坐),我感觉有暖意是不应该和不可言说的,也是不礼貌不道德的。
关羽是我的新朋友,我和他是网球场上认识的。他打了十来年网球,是个网球高手。而我却是个新手。我到球场的第三天,就和他互相留了电话。从此,每次去球场,不管谁先到,总会给对方打个电话。我的球技因此进步很快,一个月之后,完全掌握了单反和双反的技巧。一星期前,我开始学高发了。严格说来,他算是我的指导老师。关羽比我大三岁,事业有成,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外贸公司,有一辆保时捷越野车,更重要的是,他看起来每天都空闲(吃饭时他说:“我忙了,我的公司就完了。我不忙,说明我的公司运转一切顺利。”),去年他还独自一人去美国观看了美网比赛。这一切都令我羡慕。有时,球打得晚了,我和他,还有另外几个球友会去就近的餐厅喝点啤酒。餐桌上,我们谈论的话题比较狭隘,网球和女人,偶尔也说说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有一天,关羽向我介绍桌上其他几个球友的家庭情况时说:“我们这帮子人,感到庆幸的是,老婆都讨得很贤惠。”关羽还问我和我妻子的关系如何。我回答不上来,我说:“我不了解她,但是,她看上去很了解我。”我的话引来一阵哄笑。
我听得出,关羽有个很贤惠的妻子。我不太明白女人贤惠的意思,这有点令人费解,我理解,关羽他们口中说出的贤惠也许就是他们的妻子听他们的话,还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吧。从这一点看,我妻子也是贤惠的,我也有充分的自由。至于我妻子听不听我的话,我认为是次要的,我觉得她没有必要凡事从我,否则,我这个毫无计划的家伙会把家庭搞砸的。
关羽说:“今天晚上的美网,十一点整有莎芬的比赛,你来我家看吧,热闹。我家里的电视是34寸加等离子,音响效果特好,球弹在硬地上,有哌哌声。”
“哌哌?”我站在保时捷的车外隔着车窗朝里问。
“恩,哌哌!莎芬的Ace球落地就是这样的声音。他状态好的时候是无人能敌的。来吧?”关羽用探寻的目光看我。
“好的。我回去洗个澡,衣服上都出盐斑了。”
果然,门开了。背光中,关羽的妻子看了我一眼,马上又把门“碰”地关上了。
“你是谁?”她在里面冷冷地问,有点惊恐。
“我,我是关羽的朋友,我和他约好的,他在吗?”
“你约他干什么去?近段日子的一些晚上都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晃当!”关羽的妻子打开了猫眼门。我感觉她在上下打量我,但是我什么也看不到。
“没有,不过,傍晚经常一起打球的。今天是他叫我来你家看美网公开赛的,你问问他就知道了,他在吗?”
“没这么简单吧?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刚才在门外一声不响的,我问话你怎么不应?”脆耳动听,脆耳动听,我努力找寻刚才的感觉,但是找不到了。现在不是脆耳动听了,声音变得有些尖刺;也不再有暖意了,我浑身上下都是一种被怀疑的冷冰冰。
“叫关羽出来说话吧。他手机没电了,我打不通他的电话——刚才我在门外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他手机没电了。”我支吾道。
“他关机了。”
“那——”
“他不在家。”
“哦。那我就告辞了。”
“慢着——”关羽的妻子在门内沉寂了一下,声音又归复为先前的柔和,“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服。”
我在诧异中静静等待。楼道上的灯灭了,漆黑一片,我下意识地做了一个高发的动作,灯又亮了。是感应灯。这段时间,我的头脑里全是网球,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右手一挥一挥的,同事问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关节病了。但是我又感觉到在此时玩这样的动作似乎过份了一点,关羽的妻子本来就对我心存怀疑,要是被她猫眼猫到了,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门内又传来拖鞋的声音,大概是她从房间里换好衣服出来了。我下意识整了整身上的单衫,并用手指捋了几下头发--我的头发有点长了,哦,还有我这讨厌的胡子,急匆匆过来,又忘了剃了。
她没有开门,而是走进了卫生间。我看到她先把卫生间的窗户扣上了,对我说:“再等一下哦,马上好。”
等到她在卫生间整理好自己的头发,上了点淡妆,才把门开了。很礼貌地对我说:“刚才真是对不起。我和他有点矛盾——走吧!”
“什么?”我朝后让了让,一阵恐惧缓缓涌上来,“这,你要,要去哪儿?”
“带我到关羽现在在的地方。我知道他的身边肯定有个女人在。”她的声音又有点冷了。
(“你老婆对你比较了解?哈哈,看来你是很听你老婆的话的。”关羽把酒杯举了过来,其他的球友也把酒杯举了过来,都是一脸坏笑。)
(“什么意思?什么听话不听话的?你们难道,都是不听你们老婆话的?”满杯的啤酒下去,我不禁打了一个长长的嗝,我对喝下这杯酒很勉强。)
(“我们啊,”关羽会意地看了看他的同伙,朝我诡秘地说,“也不能说不听,也不能说全听。”)
(“是啊,”一个球友跟着说,“我们关老板,要听从的女人何止一个啊!”)
“我怎么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我这不也是到你家来找他的呀!”我迫切地解释道。
“我看你也被他带坏了。这次算我求你了,好吗?带我过去吧!到了那个地方,你自己离开好了,我会单独进去的——我必须这样做,对吗?”
“对对,但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晚上,我只和他在上岛咖啡喝过几次茶。我和他是刚刚认识的,没两个月,请相信我。”我把右手按在我的胸前,诚恳地对她说。同时又似乎有点后悔,她真是个漂亮的女人!
“真的?”
“真的。”我重重地点了下头,我此刻象个老实的学生,惟恐老师不相信的样子。楼道上的灯又灭了,我却一动也不敢动。
“那,你进来吧。你看灯都灭了。”
“不了,”我在黑暗中说,我看见背光把她薄软的白色无袖衬衣穿透,勾勒出她上身娇媚的曲线,有点丰满,却不胖,“关羽不在,不太方便,下次再来拜访吧。”我动了一下身子,楼道灯又亮了。我再也看不到她上身的曲线了。又一阵懊悔。
“哦?现在几点了?”她问道。
我下意识按了一下手机,手机锁着,屏幕不亮,便慌乱解了锁屏,说:“9点45分。”
“那不早了。”
“是啊,不早了。我走了。”
“我的意思是,关羽就快回来了。你们不是约好看美网吗?我看他就要回来了,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他平时也总是在这个时候回来,要么他——”她顿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要有规律。生活一定要有规律,”关羽对我说,我看了看其他几个家伙,他们都赞许地点点头,“没有规律的生活,老婆要怀疑的。”)
(“什么规律?我的生活也有规律,我即使没有规律,我老婆也不会怀疑我呀!”)
(“你呀,就是一跟筋。当然你不太明白,谁叫你是个乖孩子呢。要是有一天你不再乖了,肯定被你老婆看出你的问题来。”关羽把女服务员招过来,女服务员正蒙着嘴在墙角边上笑呢。关羽说:“别顾着笑,你以后也一样的,现在学着点,将来可以把你的老公管的牢点。快去,再上六瓶喜力。”女服务员笑着问:“还是三瓶冰的三瓶不冰?”“都冰的,越喝越热乎了。”关羽用手巾擦了擦后脖子,说,“把手巾和盘子都换一下,要快!”)
我坐在对面的长沙发上,我正对的就是关羽向我炫耀过的34寸等离子电视机,旁边对称各放两对音响,是丹麦的“尊宝”,价格是我不敢想象的。她坐在我一侧的单人沙发上。我看了看门,已经关上了,门内摆了两双拖鞋,一双是她刚才拖过的粉色木底鞋,那双大的,相必是关羽的吧。可见他们家平时客人不多。我的球鞋放在门外,执意不肯放到门内来,我觉得我球鞋的脏度已经超过这个清洁家庭的承受力。我赤脚进来(除了打球,我不习惯穿袜子),她看了看,没有再坚持,自己也赤脚了。
“关羽的爱好真多,想必很喜欢听音乐的吧?”我假装轻松地环顾四周。
“哦?你哪里看出的?”她漫不经心地问。我把头偏向一边,因为我突然发现她说话喜欢正视对方,这种礼貌对我来说很不习惯。
我点了点两对高档音响。她“呵呵”笑了起来,问:“你也懂音响,想必也喜欢音乐。这音响是我买的,喜欢听歌的是我不是他。他哪里有这个闲时间!我这里有恩雅的歌,这个苏格兰人的歌我特别喜欢,你呢?要不要放一点?”
“这个,不用麻烦了。坐一会好了。”我局促地挪动了一下屁股,害怕她再问下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歌星。
她还是坚持放音乐了,不过音量开得很轻。她把电扇朝我这边移了一下,我看到她脚背白皙皮肤下淡淡的青筋。她回头对我笑笑,说:“天气有点热。但是我害怕空调,你不会介意吧?”
“我不热。”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打开手机一看,10点。时间过得真慢啊!
关羽还是关机。我想明天在球场上要好好批他一顿了,有这么不讲信用的?
“你别打了,他的脾性我还不知道?他不愿意别人打搅他的时候,你即使把地球翻一遍也找他不出来。”她把头朝后一仰,靠在沙发上,白衬衣领子处叉得更开了,一个金属挂件露了出来,好象是一把宝剑的样子。
“别这样猜测,关羽他其实是个不错的男人,我们都很羡慕他的。”我说。我把视线从她的胸前移开(象生了根一样,有点困难),朝另一边看。我看到一个酒吧,酒柜里摆放着形形色色的酒。当然也有一大群关羽喜欢的喜力。这些酒瓶子在洞灯多角度直射下,散发出奇异的色彩。
“哈哈,才怪!”她又坐正了身子,目光直对着我,问:“你和他平时在一起,除了打球,还干了些什么?”
“没有啊,喝点啤酒而已。”
“喝酒?只是喝酒?”
“是啊,喝酒,没有其他了。“
(“男人在一起能干些什么?喝喝酒聊聊女人嘛!”)
(“不聊女人,这酒就喝得没道理了。”)
(“你有过女人吗?”)
“你有过女人吗?”
“什么?”我怔了一下。没想到关羽夫妻俩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啊,有过。”我自豪地回答。)
“我啊,没有。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你和我们一样啊!哈哈,你小子,保密工作蛮好得嘛!”)
“哦?这倒是稀奇事情。有句话说,近墨者黑。你别给关羽带坏了。”
(“那也是偶尔的一次,所谓的一夜情,没什么回忆,不值一提。”我摇晃着酒杯,脑袋里开始浮现出那个人的话:“我老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老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别这样乱猜,”我违心地笑着说,“关羽可是个顾家的好男人,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在外面有什么女人。”
(“我老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你口口声声说你和你老婆没有感情,现在看出来了吧!现在露出马脚来了吧!我还要嫁人呢!你耽误了我三年,我现在怎么去嫁人啊!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你干脆随便找一男人给我算了!”)
(“你真不是人,真不是人啊!你耽误了我整整三年,我还为你流了一次产。好吧好吧,这是迟早的结局,长痛不如短痛吧!”)
她狐疑地盯着我,脸上微微泛起一阵怒意。但这是一闪即逝的,她的涵养和生活的积累重新把自己装扮成平淡。她站了起来,鼻子里哼起了调子,这才使我感觉到原来还在放音乐。她走过我面前,即使赤着脚,也能让我感觉出罩在裙子下面的修长的腿。一阵香气拂过我的脸庞,是我不久前才熟悉的香味。
(“不把事情考虑成熟,是没有资格接近其他女人的。来,闻闻。”关羽向我招招手,他的手中捏着一瓶香水。)
(我走过去闻了一下,说:“恩,香。”)
(“不是叫你闻香还是不香,香水哪有不香的?你这个傻小子,”关羽得意地说,“我要叫你记住这个香味。”)
(“哦!原来你喜欢这种味道啊!”)
(“不是,是我老婆经常用这种香水。所以,我就常买这种香水送别的女人。这样,我老婆不会从我身上闻到其他的香味了。”)
“你用的是香奈尔牌子的?”我禁不住问。
她已经坐在酒吧那边的转椅上了,听到我的问话,惊讶地笑道:“呀!原来你对香水有研究啊!真看不出你来了。”
“不是不是,”我开始退缩,后悔自己的莽撞,解释道:“因为,因为我老婆也是,也是用这个牌子的,所以我闻得出来。”我老婆根本不用香水,要说我老婆身上有香味,那也是洗发水的香味。
“恩。这样啊。你,过来。”她的语调轻盈悦耳,又似蜜水般柔和。
“什么?”我愣在那里。
“你们男人不是喜欢喝酒吗?那么,你到这边来,我和你喝几杯。你喜欢喝什么酒?”
“关羽怎么还不回来?”我尴尬地笑着,自己问自己,又象在问她。
“什么酒,说呀!”
“这个,随便吧。”我走了过去,和她挨着坐在另一个转椅上。吧台边也只有这两条转椅。
“你说吧,这上面有的都行。我们边喝边等关羽。”她张开右手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啤酒吧。”我说。
“不行,啤酒不行,家里喝啤酒算什么,我没有意见,恩雅也会有想法的,哈哈。”
“恩雅?”
她侧身朝音响努努嘴,我这才又记起那个苏格兰歌星的名字。
“那随便吧,”我又看了看手机,“10点半了,这小子!”
她突然按住我的手,抢下我的手机,半生气半调侃地说:“不许打手机,我讨厌别人在我面前打手机。喝洋酒吧,你看看。”
“那,芝华士吧。”我应付道。
“芝华士我不太喜欢。黑方吧?”
“好的,最好加点绿茶,淡点,我酒量差。”
“不行,只能加冰块。梢等!”她滑下转椅,跑向厨房间。我听不到她跑动的脚步声。
(“不行,你是有老婆的,怎么可以对我说爱呢!”她在短信的后面加了生气样子的红脸。)
(“不行,我对你什么感觉我不能告诉你!”她跳下公园的秋千架朝草地深处跑去。)
(“不行,今天说什么也不要回去了,好吗?”她紧紧抱住我,她的头几乎要钻进我的胸腔里去。)
香奈儿的味道又包围了我,我看见她已经坐回到椅子上了,手里多了一大杯冰块和两个小酒杯。她边倒酒边问:“出什么神呀?”
“没有。”我低声说。我想起了和我度过三年时光的她。我撒了个谎:“我在想关羽大概快到楼下了吧。”
她冷冷地“哼”了一声。
(“兄弟啊,学着点,我老婆闻不到我身上其他的香味,她就不会知道我有其他女人。哈哈,我在外面做任何事情她都不会知道。”)
“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的事情我都知道。”她把一块冰小心地朝酒杯里放。
“什么,你都知道?”
“直觉。女人的直觉很灵的,特别是对自己老公,直觉绝对不会错。”
我轻舒一口气。她把杯子递过来,我接住,一口喝光。她笑着看看我,也干了。
“11点了。”我无力地说,我感觉我快要回家了,这让我失落。
“喝吧,今天我们尽情喝酒,别等他了。这个自作聪明的人今天不会回来了,我知道,只要过了10点,他就不会回来了。”她又干掉了一杯。
“不回来了?”我在惊异之中涌起一股无名的快乐,“那我——”
“你什么?你喝你的酒好了,觉得这酒怎么样?”她用探询的眼光看着我。
“不错,”我看了看她的神色,觉得她好象不太满意我的答复,便改口道,“很好,很好!真是享受啊!”
她笑了,仰起头大笑,笑得有点忘乎所以,刚才的矜持荡然无存。等到她把头低下来时,我看到她的眼里全是泪水(她还在笑)。我不知所措。她笑嘻嘻地把脸转向我,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别这样,请别!”)(这样正好,你也可以靠在我肩上的呀!),然后又把头低下去,把满脸的泪水擦在我的肩膀上(“你酒多了,不要喝了!”)(难道今天我碰到好机会了?),说:“享受?你觉得我这样的生活是享受?我在你们的眼里,是个不用工作靠丈夫吃饭的幸福的女人?”
“我不知道你幸福不幸福,但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好女人。”
“凭什么?”她拿过杯子和我碰了一下,“Cheers!他整天花天酒地,我凭什么就要做个好女人?也为什么不能做个坏女人?”
(“好好,从此后,我做什么都与你无关!我即使做鸡去也不要你来管!我要叫你看看我是怎样毁灭我自己的!”)
“别说了!你不能这样!”我无意间加重了口吻。
她抬眼看我,把头朝左边斜,又把头朝右边斜,“呵呵!呵呵!看你一副假正经的样子。你是男人吗?”她用手掌拍了拍我的胸膛。“呵呵,是男人的话就给我说真话,难道我真的看不出你这种人的心?难道你从进门开始没有对我动过坏想?说!有没有?呵呵!”
“没有!”(当然有,怎么会没有?)
“真没有?你如果老实说有,今天,今天晚上我就满足你。说吧!”
“真没有!”(难道说没有你就会放过我?笑话!)
“你是个伪君子!难道我不知道你在楼道口按门铃开始就一直在偷窥我?”她用食指点我的鼻子,我闪过了,但我感觉到鼻子上又新冒出一层汗。
“这个——真没有,你,别误会。我不是那样的人。”我的语气软弱了下来。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她朝空中挥了挥手,“谈其他的。你,你结婚了?”
“是的。”
“小孩呢?”
“女孩,6岁。”
“哦,我也是女孩,小一岁。5岁。”
“不过,孩子不是我生的,”我清了清喉咙,“我老婆带过来的,她离过婚。”
“哦。我,可能最终也会和你老婆那样,不过可能没有福气再找到你这样的人了。你们俩,那个过的怎么样?”
“什么?哪个?”
“那个呀!性——生——活!“她几乎把嘴巴贴在我耳朵上喊。
我不习惯地晃了晃头,回避地说:“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妻子说。)
(“我对这个有阴影。”妻子说。)
(“你怎么这么久呢!快点吧,我疼!”妻子说。)
(“我要吐了!”妻子说。)
(“实在对不起!”妻子说。)
她把自己的杯子打落在地上,碎了。我趁机拿回我的电话,想打电话给关羽。但是我现在又不敢打了。我说什么呀?我说我把她的老婆灌醉了?
我把她扶回到沙发上。电扇停了,恩雅也不唱歌了。我对她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懦夫!”她猛地翻过身来,象骑一匹马一样地骑着我,“你真的不敢?”
“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不敢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突然间蹦出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只是嘴巴上说敢而已。你怎么从关羽那里一点也没有学到手?”她一把扯下发簪,满头长发象水一样朝我脸上扑来。她附下身,紧紧咬住我的耳根。“你不敢呀!真不敢吗?”
(“求求你,今天不要走了,别回去了!好吗?”)
(“我不回去。我永远在你身边。每时每刻。”)
(“你发誓!”)
(“我发誓!”)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一怒而起,把她压在下面。“你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把她那件白衬衣象塑料包装纸那样撕了开来。
她把我的头按在她的胸脯上。我又闻到了一股久违的香气,这股香气形成一条无形的锁链紧紧缠住我的脖子,使我透不过气来。
(“对啦。哈哈,记住,香奈尔。我老婆用的香水。记住这个味道,我老婆的味道。哈哈!”)
我脱开她的缠绕,从沙发上起来,朝门口逃去。在我穿鞋子的时候,我听到里面的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坐在楼下的车上。没有把车子发动,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呼吸倒是越来越急促。我放心不下楼上的她,我咒骂那个该死的关羽。我还是感觉特别气闷,车内混浊的气味让我头晕。我又从车子出来,重重关上车门。“砰”地一声,很清响。我这才感觉到四周死寂一片,几乎听得到对面黑黝黝的那幢楼里面每一个细响,这些细响碰在每一个玻璃窗上,都发出清脆的“哌哌”的声音。(“哌哌!莎芬的Ace球落地就是这样的声音。”)到处是一模一样的楼,到处是一模一样的声音。我记不得我和关羽的老婆说了什么话了,我好像只是“哌哌!哌哌!”地和她说了一晚,她也“哌哌!哌哌!”地回答我。她哭的时候也是“哌哌!哌哌!”,我此刻心跳声也是“哌哌!哌哌!”我走到车后,打开后车厢(哌!),取出我的拍子和网球。关上车厢(哌!)。
我把拍子高高擎起,将网球一个一个击向对面那幢楼。哌!哌!哌!
责任编辑衣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