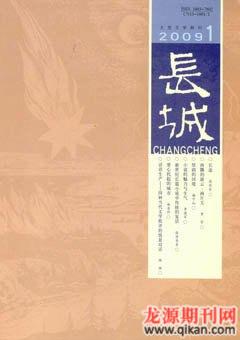杨绛:撤消问题
黑 马
采访了不少译界名人,但仍然与翻译大师杨绛先生缘悭一面,为此深感遗憾。我在1980年代初做研究生时就反复通读了杨先生的文学论集《春泥集》,所受震撼难以言说,只能说它令在那之前读到的大多数文学批评在我眼中黯然失色(我是从欣赏美文的角度看待它的,它当然不能代替那些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部头著作的学术价值),私下以为那是将学术与情思交融的纯美之作,跨论文和散文两个领域,而在两个领域内都独显魅力,弥足珍贵。其精妙可意会不可言传;其神韵可追随难以效仿。曾感叹,学问做到这个大自在的份上,可以说是接近审美极致了。
可是,采访杨先生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但我知道以我的浅陋,即使有机会采访她,似乎只能做些与英国现代派文学相关的话题。1930年代在英国留学并研究英国文学的几位大师如钱锺书、萧乾和叶君健离去后似乎只有杨宪益先生和杨绛先生还健在了。
有一次有电视台为杨宪益先生拍摄专题片,杨先生的外甥女赵蘅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可以趁机提些问题,既满足了我的愿望,也为电视片补充些"专业"内容。我当然求之不得,便备好录音笔上阵了。我提了一些英国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以期得到这位少有的中国见证人的稀有答复。但这个愿望基本落空了。杨宪益先生说他读的专业是古希腊文学,喜欢的是法国文学,后来改学英国文学,但那个年代英国大学的课堂上只讲古典文学,最多讲到狄更斯,而现代作家则不涉及,全靠自己业余读一些,因此他对英国现代文学印象不深。看来能深入回忆当年英国现代文学盛景的似乎只有杨绛先生了,而杨绛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似乎并没有涉及到英国现代作家,原因何在?于是要采访杨绛讨教个究竟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北京某报发表了一篇某位翻译《堂•吉诃德》的西班牙语教授的访谈,其谈话内容的焦点是对本书首译的完全否定,而这个译者恰恰是杨绛。这位教授称他在课堂上把杨译当成“反面教材”进行分析云云。此文一出,即引起译界哗然,不少翻译家接受《文汇读书周报》采访时都对该教授批评杨译的低俗方式表态,批评甚至指责。我在接受采访时不无气愤地指出该教授利用公家的课堂以“运动员”身份充当“裁判员”,把同一本书的首译本说成是反面教材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言辞比较激烈。我虽然不懂西班牙文,但觉得无论如何不应该对一个老前辈如此出言不逊,后来者对三十年前的开山之作本应抱以敬重和感激才是,即便那首译可能有诸多缺陷。该教授随之在报纸上发表谈话反驳。见此情形,杨绛先生写了文章表达自己息事宁人的愿望,她欢迎批评,但认为双方如此交锋不必要,应到此为止。
杨的文章写好后急需传真到上海,但杨家没有传真机,报社就差我到杨家取稿子,然后复印传真。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见到杨绛先生。
去时我本来准备了《春泥集》和《洗澡》等书打算请杨先生签名留念的,但到了杨家楼下的刹那间觉得不妥,就把书留在了车里,径自上楼去取稿子。
见到杨绛的第一面,觉得与报纸上看到的近照很像,并不像95岁高龄的老人,倒像70来岁似的。杨先生在宽大的写字桌旁站起,步履轻捷地拿着准备好的稿子走过来递给我。我接了稿子,道了谢,就准备告辞。但杨先生说要我留下“尊姓大名”和电话,并要我坐下凉快一下。那天正是一个7月的桑拿天,我仅仅从车里走出上三楼的工夫,T恤衫就湿了一片。杨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还亲自把小电扇向我这边拉了拉对着我吹,说希望我当场看一看稿子,那样写还有什么欠缺,她可以增删。至此,我十分感动,也为杨先生在95岁高龄上身子骨如此硬朗、精神矍铄感到高兴。杨绛确实不同凡响。可惜她和钱先生都拒绝上电视,否则如果有摄像机拍下她的生活画面让广大读者看到她的状态该多好!我忙说不用看,说着我拿出名片留给她,并说传完稿子我会把原稿送回来。她看了名片上我的姓名,恍然大悟,说:“你就是毕冰宾呀。”我想她立即想到了我在报纸上就此做的答记者问。
既已暴露真实身份,我也就不隐瞒什么,再次表示那位教授的话太过分,超出了翻译批评的界限。杨先生说:她的译文是在“文革”后期翻译出来的,是接受的一项任务。为翻译得更准确,她并没有从英译和法译本转译,而是自学了西班牙文,因此过程很是艰难,所以早期的版本里肯定有错误,指出她的错误是对的。但令她感到难过的是,这些批评她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她后期的再版译本呢,每再版一次她都要做一次修改,这次教授谈话中指出的那些错误她都在新版中改正了。“我不是骄傲自大、有错不改的人!”这个时候,我看到杨先生眼神有些焦急,似乎有点湿润,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看到这位我十分景仰的老人如此诚恳、焦虑,我只能默默地叨念:“有点太过了。”对此杨先生似乎轻声说了一个“是”字,但马上又说:这事就到此为止吧,不说了。
我回去后就赶紧把稿子复印传真给了上海。传真完又挂号把原稿寄还给了杨先生,然后才坐下来读她的文章。杨先生的字竟然写得如此有力、清晰,不少还是繁体,几乎是一气呵成,极少改动,改动处也用涂改液抹得干干净净。大师就是大师,体现在一举一动,一笔一画中。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恍惚记起我在杨家看到的场景和杨先生的音容:那是80年代前后盖起的几栋高知高干楼,三层红砖小楼,一梯两户,首层每家有一个几平米的小花园。那种房子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别墅级的了。杨家(其实是钱家)住三楼,房子的格局现在看来比较一般,但有一个大客厅。似乎那个家基本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装修,地面没有瓷砖,十分朴素。更朴素的是杨先生的衣着。很多书中都刊有杨绛中青年时代身着旗袍、画了淡妆的优雅照片,与现在简朴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那天我见到的杨绛穿着最普通的居家衣服和布鞋在屋里走动着,像个一般居民楼里的家庭主妇。进她家也不用换鞋或戴鞋套。
还有她那口带着无锡腔的北京话,柔中带刚,毫无老气横秋。
我走的时候杨先生执意要从沙发上起身送我几步,步伐很是灵活,根本不用人搀扶。
那件不愉快的事就以杨绛给《文汇读书周报》的一封信做了了结。那封信写得心平气和,既承认了自己早期译本的错误,肯定别人批评的对,又说明自己的译文再版时做了修订更正,还提出了对一些译法的探讨。她特别劝告为她“仗义执言”的人“不要小题大做”,要化“误解”为“了解”。看到杨先生焦虑伤心的情景,再读这封信,当然我的感受就不同了。可能别人看到的是平淡,我看到的则是雍容大度,大度就大度在她深感受了伤害,但在信中绝不指责对方没有看她修改后的译本,仅仅是平静地说明她后期的译本中已经做了修正,而这一点恰恰是一般不了解内情的人容易忽略的。我恰恰看到了她在说这番话时眼中转瞬即逝的那一星湿润,因此我感触很深。对一个年高德劭的文化老人,这样的伤害确实很深,但她还是要息事宁人。这就是大度。
就这样匆匆结识了杨绛先生,本可以到此为止,只留下以上的印象。但我心有不甘,还是想了却那个酝酿多年的采访心愿,给杨绛先生打电话要求方便时录音采访。杨家的电话由阿姨接听,记下内容转告给杨先生,再电话通知我可以打电话与杨先生交谈。
电话里杨先生说她已经95岁高龄,“我现在是个大聋子”,谁来都要在耳边大声喊,她也会情不自禁大声回答,那样谈学术问题太累,身体不能承受。
但我强调说,毕竟杨先生在这个年龄上还在翻译写作,思维如此活跃,记忆力如此强健,表达如此流畅,连走路的步态都还那么硬朗,我怎能仅因为一个“聋”就放弃一个大好的机会记录下她的一段别人不曾关注过的经历?我特别强调只问杨先生在英国读书的问题,这是她的作品中的一个空白,如果她能回答些问题,无疑是广大读者的福气。我一再表示,我们不对谈,只提了问题,请她小声独白,我录音,然后我整理录音即可,是口述实录。但她说她不愿意被录音,即使录了音,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帮我确认录音稿。于是干脆地说那就简单聊几句吧。“我说,你听”。
杨先生说她在牛津是自费旁听,不是正式学生。但作为“补课”,她跟着钱先生读了很多英国文学作品,从古典到19世纪的作家都读了个遍。但因为不参加考试,也不拿学位,所以就没有研究谁。也说不上特别喜欢谁。我一再要求举几个例子。杨先生就举了Gorge Eliot和Jane Austen,说很喜欢。特别说到Austen,塑造人物鲜活,过目不忘。为此,杨先生强调小说情节很重要,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这是好小说的要素。相比之下她不喜欢Charlotte Bronte,说Jane Eyre不是纯粹的创作,有大量个人的影子在其中。她特别让我记住,好小说一定得塑造鲜明的人物,一定要有生动的情节。
杨先生大声喊了半天,我生怕她累病,就一再说您的这些话不录下来让读者了解太可惜了。她才妥协说,我可以写个采访提纲寄去,“看情况可能会回答你”。
我知道我不能再得寸进尺,强求一个95岁的老人。于是拟了一个提纲送去。估计杨先生会在每个问题下写几行字。也许她觉得无聊,就此不再理会。但我没想到的是她在第二天傍晚就让家里的阿姨小吴打来电话,说可以在电话上回答我。
杨先生的声音依然那么清晰,纤柔的无锡口音普通话,语调柔中有刚,语速中等偏快,几乎没有任何语气助词,干净利落脆生。她说她来电话不是要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要“撤消”我的问题,撤消的理由则有很多。我在她的谈话开始后才意识到这不是敷衍我,而是个长谈,撤消这些问题的理由岂不是从反面在回答我的问题吗?我这才马上抓过手边的纸和笔边听边记。随后根据潦草的记录和新鲜的记忆马上整理成文。我平生第一次做了电话“采访”。
这份电话记录以口述实录形式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杨先生在电话中说过不要看我的电话记录稿,不要寄,也别发,就当是听她聊天而已。但我以为她的话是客气和谦虚,也理解她无法确认谈话记录的苦衷,那将花费她多少心血和时间啊,为这些寻常的谈话实在不必打扰她,就想当然地径自将稿子拿去发表了。
这个谈话道出了杨先生修了英国文学却很少做英国文学研究的苦衷,道出了她一直热衷于文学创作却到85岁上才迟迟写出名著《洗澡》的原因,也顺便说到了钱锺书先生致力于写一部研究西方文学的巨著但终于扼腕的历史性失落。我急速地记着笔记时,都感到了杨先生在电话那一端以闲谈的口吻道出这些遗憾的伤感心情,也感到了她内心巨大的坚强忍耐力量。联想到她的近作《我们仨》中那将大悲化作粘泥絮的历史叙述,我分明能感到这个95岁的文学巨匠,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老妇人,有着一颗怎样坚强的心在支撑她波澜不惊、雍容大度!我能记下她的只言片语,那是吉光片羽,该是多么荣幸。
但记录发表几天后杨先生打电话给一位大姐要她转话给我说她为此生气了,因为我没有听她的话,私下把谈话记录拿去发表了。那位大姐指出记录中一处有误,但我保证我没听错。
为此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没能善解人意,让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受惊了。于是写了一封短信给杨先生致歉。这还是我第一次向被采访者道歉,因为我十分尊重敬仰她。
后来我几番揣摩,估计杨先生是不喜欢这种“口述实录”的形式,德高望重的先生不愿意把这些寻常化了的学术谈话公之于众,因为电话上的话毕竟会显得不够学术,正如她先前所说,回答那些问题是需要写一本书的,怎能轻易几句话打发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其实我觉得先生是多虑了,让广大读者听听这些学术巨擘的“寻常语”,反倒觉得新鲜可亲。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如那位大姐所说:杨先生现在就想平静地做她的学问,不想惹什么麻烦。或许我的善良竟会伤害杨先生。
但误会是不可挽回了,我只能深深地抱歉。那个记录稿,真实准确地记录了杨先生一次学术性闲谈,也是我第一次做“口述实录”,之所以实录下第一人称的谈话,是因为我想我是出于对真实的追求,为既不录像也不录音的杨先生记下最真实的声音,让读者领略她在95岁上如此幽默反讽的谈话风采。只可惜,我不能再次犯错误把它公开于此了。
写这篇印象记时,刚刚从书店买到杨绛先生2007年出版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是她用寻常语道出的关于生/死的智慧之书。我恍然大悟:那年,正是杨先生为这本独特的思想录苦心孤诣定稿之时,她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她是多么不愿意受到外界的无端打扰,可还是发生了那件令她难以平静的事件。当然还有,我发表的电话实录也干扰了她,里面有些话如果是经她推敲后写出来,可能是另一番语气,不会那么直白,被涉及的人可能会感到不那么自惭形秽。可能这是她当初对我说"不要寄,也别发"的真实含义吧。我现在只能做如是猜测。那篇谈话记录稿的发表肯定也令杨先生心绪不宁了一阵子,影响了她平静的写作心境,因此我还应该再次致歉,无论如何那不是她想让那番话公诸于世的方式,我想。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