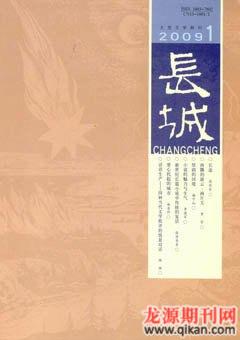小说的魅力与生气
李建军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于揭晓了。结果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人意料之中。正像任何评奖都难免遭遇质疑和批评一样,本届的“茅奖”也引起了专家和读者的质疑。批评家王彬彬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认为在本届获奖的作品中,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青年批评家于仲达更是在网上撰文,针对个别获奖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质疑。一次评奖的成败是非,有时一目了然,有时则很难说清———对那些让人欲说还休的问题,不如姑且置之一旁,因为,天长日久,自然会水落石出,是非昭然。
所以,与其谈论那些不值得谈论的作品,与其纠缠于那些一时很难说清的问题,还不如先来谈论那些值得谈论的作品,从而认识那些对文学批评来讲须臾不可少的尺度和标准。例如,谈谈给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茅奖”带来荣光的《白鹿原》。如果说有的作品获奖,降低了“茅奖”的声誉和影响力,那么,《白鹿原》的获奖则极大地提升了“茅奖”的公信力,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白鹿原》虽然还没有达到中边皆甜的经典作品的境界,也的确不是无瑕可指的完美之作,但是,它以一种包容的创作态度,吸纳了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的艺术经验,从而在许多方面臻达高度成熟的境界,标志着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无疑是中国文学最近一个世纪最杰出的长篇小说。
那么,《白鹿原》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的启示呢?
《白鹿原》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把故事性看作小说的重要特质,并能不厌其烦地营构充满悬念张力的故事情节。其实,传统小说,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大都是通过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的讲—听式叙述,来达到与读者的交流目的,这一点,我们无论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巴尔扎克、梅里美、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是从中国的以《红楼梦》及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代表的古典及现代优秀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但从福楼拜开始,中经亨利•詹姆斯、卢伯克,另一种倾向就占了上风,这就是轻视讲述,而重视描写,即为了追求一种直接的印象效果,而要求作者退出,或保持中立、冷漠的态度,小说由此而变为具有戏剧风格的写—读式展示。这种小说叙事方式,在现代派小说中很有市场,它导致了小说的“可写性”与“可读性”的分离,把小说这一最具可读性的大众文体,变为一种只有可写性的贵族文体。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平等、亲近的我—你关系,被异化为一种冷冰冰的我—它关系。
陈忠实在写《白鹿原》的时候,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没有读者的小说,是没有生命的。而小说的可读性,从某种程度上讲,决定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小说家一定要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一个从不忽视情节的意义和魅力的人。陈忠实在《关于〈白鹿原〉的答问》一文中说:“可读性的问题是我所认真考虑过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个。构思这部作品时,文坛上有一种‘淡化情节的说词,以为要彻底否定现实主义的过时传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淡化情节,写一种情绪或一种感觉……我们的作品不被读者欣赏,恐怕更不能完全责怪读者档次太低,而在于我们自我欣赏从而囿于死谷。必须解决可读性问题,只有使读者在对作品产生阅读兴趣并吸引他读完,其次才可能谈及接受的问题。”{1}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序言《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一文中有这样的妙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2}“魔法师”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标准,一个小说家必须通过他讲的故事,使他的作品对读者产生一种魔力,或者有如罗兰•巴尔特所讲的小说的“吸陷作用”{3};而读者呢,“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4}。在论诗给人的美感时,中国古人也说过“冷水浇背,陡然一惊”{5},这同纳博科夫的话一样,都是迁想妙得的高论!我们读陈忠实《白鹿原》这样的小说,就曾有过这种强烈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正是陈忠实通过故事的“魔法”传达给我们的。在《白鹿原》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些与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然而,现在的许多小说家,却越来越不会讲故事了。如果你对这些小说家说他不会讲故事,他会心安理得,因为,在他看来,小说与故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相反,如果你说他会讲故事,他倒有可能不怎么乐意,因为,这几乎等于说他不会写小说了。他不知道,其实真正的好小说,内里都有如金圣叹评《水浒》时所说的“令读者心痒无挠处”的好故事,而读者也常常是奔着去读一个好故事,才去读小说的。正如梁实秋先生在《现代的小说》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般民众之所以要读小说,是因为要读故事……故事是需要的,尤其是在小说里,故事是惟一的骨干,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
至于故事的讲法,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其类型也是能数得清的。作家讲故事的方法,在于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微妙的变化,却不存在谁一夜之间发明或发现了一种全新讲法的奇迹。陈忠实《白鹿原》就讲故事的方法来看,可以说一点新意也没有,金圣叹评《水浒》、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时已说得很完备,也就那么几种罢了。只不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够用这些方法翻奇出新,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就要靠作家的本事了。
讲故事的方法固然忽视不得,但更为重要的是对读者要有诚恳的态度,不要故弄玄虚,故作高深。读罗伯-格里耶等人的作品和马原、孙甘露、北村的小说,总觉得这些作者太扎势子,绕来绕去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普通读者哪有闲工夫来陪他们没头没脑地作“少年侃”(Skaz,俄语词,该词用来指某种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形式),只好让少数专门家去给他们举行“先锋派”的命名仪式。在这些小说家和那些评论家看来,一种小说的“现代技巧”,远比读者阅读故事的需求重要。针对专注于形式和技巧而忽略故事性的倾向,毛姆在《论小说写作》一文中批评说:“也许,近年来人们对艺术上各种形式的技巧试验感兴趣表明了一件事实,即我们的文明正在解体……”我想他所说的“文明”中,大概就包括有对古典小说以从容的态度和巧妙的方式讲故事的传统,因为,他接下来说道:“我有故事要讲,我把故事看作是乐趣。在我看来单是故事本身就足够成为目标了;而现在有相当长的时间,知识分子却瞧不起讲故事……”而另一方面的事实却是,“喜欢听故事和喜欢看产生戏剧的跳舞和摹拟表演,同样是人之常情。从侦探小说的流行可以看出这种爱好至今不衰,连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也看它们,当然并不当回事,可是的确看它们……”{6}汪曾祺先生是在小说中讲故事的高手,他的不二法门,其实也一点都不神秘,不过是要为读者着想而已:“作者在叙述时随时不忘记对面有个读者,随时要观察读者的反应,他是不是感兴趣,有没有厌烦?……写小说,是跟人聊天……写小说的人要诚恳,谦虚,不矜持,不卖弄,对读者十分地尊重。否则,读者觉得你污辱了他!”{7}设身处地为读者想,恰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追求的境界,与春天的暖日、夏天的树阴、秋天的豆棚和冬天的火炉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要能舒散身心的疲劳、消释生活的沉闷、添培人生的经验的。想想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和蒲留仙的道边茶座,怎不令人悠然而起神往之情。总之,小说的故事性不仅是维系作者与读者的纽带,而且还决定着小说的命运,如果故事被放逐出小说,则不仅意味着小说失去很多的读者,而且最终会导致小说的消亡。
小说是写人的艺术。把人摆放到中心位置,着力刻画神完气足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小说家的中心任务。一部小说若没有塑造出一群气韵饱满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它就不可能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是被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规律。花大力气刻画圆整的人物形象,是《白鹿原》成功的又一个原因。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呼之欲出的活的人物。陈忠实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既注意把握和展示人物心理、性格结构中矛盾、复杂的方面,又不是静态地去写,而是在符合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在曲折、起伏的情节中,充分揭示人物身上深在的各个层面。你在这里很少看到以某种抽象品质为依据塑造的固定死板、性格层面单一的人物形象。人物大都是在善与恶的交替中、好与坏的对立中、顺与逆的转化中、生与死的煎熬中、悲与欢的折磨中、离与合的颠簸中很难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和固定的心性。你很难简单地说哪个人物是纯粹好的,也很难说哪个人物一无是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每个人的生死沉浮中都有一些让人感叹唏嘘的悲剧意味。面对这些人物,你只会产生一种对人的同情态度:活着是艰辛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你用悲悯的眼光去关注。作者写出了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也显示了自己对生命博大、肫挚的同情态度:“我同样不敢轻视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结局。他们任何一个的结局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他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经历了那么多的欢乐或灾难而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死亡的悲哀远远超过了诞生时的无意识哭叫。”{8}由于有了对人物的尊重和怜悯,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多少有了一些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质和“复调小说”的意味。虽然我们不好说在这方面他已达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彻底而自觉的境界,但他的充满冲突、充满斗争的小说世界,也绝不是那种习见的、以单个观念或主题为基础的苍白的统一体,而是富有意味的、内在于若干对立观念或声音的对话关系中的富有人性的统一体。
我们可以通过与《创业史》的比较,来认识《白鹿原》的拓展与升华。在《创业史》中,现实否定历史,“好人”否定“坏人”,“政治”否定一切。在《创业史》里,只有一种声音,在高亢地无节制地独白着。而在《白鹿原》中,历史在同现实对话,并在对话中对现实发出有力的质询。人物之间,甚至在一个人的内部都有对话在激烈地进行着。具体些说,这两部作品中的一些人物的经历和遭遇有极大的相似性,如李翠娥和田小娥,白占魁与鹿黑娃,都是所谓的“不正经”的女人或带些痞气和匪气的男人。但柳青写李翠娥时,直接用以“风骚有名”来评价她,并以嘲讽的口气和概述的语言,写她如何好逸恶劳,如何“男女平等”地同白占魁上城吃馆子;对白占魁,柳青也是用情感态度很明显的语言来进行评价性描述,从而给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和政治定位{9}。陈忠实在写田小娥的时候,也用了一次“婊子”{10},但那是那个“回忆”的人的声音,而不是作者的评价。陈忠实让田小娥以各种形式为自己辩护,并通过作者的相对客观的叙述,来表现她性格构成的复杂侧面:她缺乏性格上的独立性和内在坚定性,因此,她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她不乏同情心,偶尔也表现出让人感动的正义之举(如以大不敬的方式显示了对鹿子霖的轻蔑)。这种“对话”性,在她的鬼魂凭附到鹿三身上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力,使她为自己的辩护在启发读者反思自鹿原社会残酷和不宽容的同时,对其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当然,柳青和陈忠实对待人物的不同态度和方式,根本上讲,是由特定的时代状况决定的。黑格尔说:“在一个时代里如果出现了抽象的信仰,定得很完备的教条,固定的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那就离开史诗所要求的具体(一般与特殊尚未分裂)而家常亲切(摆脱了外来文化的束缚)的精神状态了。”{11}对小说来讲也一样。有的时候,“对话”式写作,是需要相应的时代条件的,就这一点来讲,陈忠实显然比柳青要幸运一些。
人物在陈忠实的小说中如此重要,但在现代派小说中,却同故事的命运一样,受到空前的冷落和否定。一些现代派小说把人物刻画同内在情绪和心理的描述对立起来了。甚至认为把人物当作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的规则也过时了,小说创作的方向,是消解人物,是注重叙述方式。法国的“新小说”派从理论到实践,都不给人物留地位。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一文中对“人物丰满的形象”进行否定,而让无名无姓的“我”篡夺了小说人物的位置,这个 “我”“既没有鲜明的轮廓,又难以形容,无从捉摸,形迹隐蔽”,而往昔的人物则“由于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或者成为这万能的‘我的附属品,或者只是一些幻象、梦幻、噩梦、幻想、反照、模态等”{12}。我们在中国当代,尤其是当前的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极端的“独白”式小说。人物没有生气,缺乏性格上的浑圆和个性的鲜明,在作者的一元话语的独白中完全被动地缄默着。人物完全处于分裂的、不自由的情境中,而这正是由作者的无限膨胀的那个“我”造成的。他们只不过是作者摆弄的提线木偶而已。
总之,故事使小说充满“魔力”,人物使小说充满生气,它们构成了小说的重要基元,是每个小说家都忽视不得的。获奖可以使一个作家在短时期内获得媒体的关注,可以使它获得外在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一部小说的生命力,却是决定于它本身的价值,决定于它是不是一部有趣的、塑造出了活的人物形象的小说。
这就是《白鹿原》提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注解:
{1}陈忠实:《生命之雨》,第437页,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第25页,申慧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3}卡勒尔:《罗兰•巴尔特》,第123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4}《文学讲稿》,第26页。
{5}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第1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6}吕同六主编:《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卷,第260-261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7}汪曾祺:《漫评〈烟壶〉》,《文艺报》,1984年第4期。
{8}陈忠实:《生命之雨》,第435页。
{9}《柳青文集》上卷,第14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白鹿原》,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1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2}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第555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