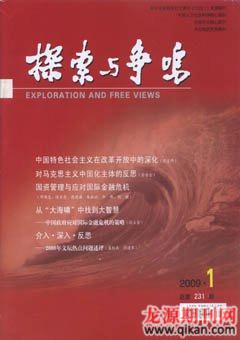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反思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前反思的阶段,另一个是反思的阶段。目前我们正处于反思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做出自觉的反思。本文重点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主体及其历史作用。
关 键 词 前反思 反思 主体 扬弃 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
作者 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从前反思阶段到反思阶段
按照我们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不妨把这个阶段称为“前反思阶段”(the pre-reflective period)。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人关注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引入中国,使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显然,这个阶段的努力主要是纵身向外的,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因而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前反思的”(pre-reflective)。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MEGA1)和《列宁全集》第一版的翻译和出版,从总体上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引入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
第二个阶段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今天仍在发展中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反思阶段”(the reflective period)。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人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化为如何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理论做出全面的反思和清理。显而易见,这个阶段的主要努力是反身向内的,因而是“反思的”(reflective),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反思和反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使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走得更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正是这个反思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尽管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MEGA2)和《列宁全集》第二版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仍然在进行之中,这一标志已表明,当代中国人正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试图从总体上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它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
如果我们上面的见解被接受的话,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理论做出认真的反思。本文的反思主要涉及下面这个问题: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如同人们在探讨全球化问题时,很少去追问:究竟谁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体?有趣的是,人们也很少去追问:究竟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由于这方面的反思的匮乏,人们常常习惯于以“匿名主体”的方式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从而使这方面的讨论很难深入下去。毋庸讳言,为了弄清问题,人们是不可能把这方面的追问长期搁置起来的。事实上,只有认真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及其局限性,才能明白,尽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谁都不会否认,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有些地方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么,究竟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呢?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从事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和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的党外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然而,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无一例外地置身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现实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而也间接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翻译并介绍到中国来。众所周知,在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党员遭到搜捕和迫害,而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也被视为非法。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历尽艰难险阻,通过日本、苏联、香港等渠道,打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译介进来,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其二,把已经翻译或介绍进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条理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从而既在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中遭遇到的种种具体问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变得家喻户晓了,而他们的伟大思想则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上述两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第一方面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无法传播到中国,从而也无法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没有第二方面的工作,即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也无法实现“中国化”,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②
今天,当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中国社会曾经走过的历史道路时发现:从总体上看,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两方面的工作。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深受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正如《毛泽东选集》中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以下简称《决议》)所指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1]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由于小资产阶级无法建立自己的政党,因而其民主革命分子转而在中国共产党内寻找出路。其中的一部分经过改造转化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2] 《决议》还细致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上的具体表现及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严重影响。
诚然,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优秀的,但其中一小部分人的思想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某些消极性的影响。
对中国化进程中历史教训的反思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一个方面工作,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介绍和传播来说,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少数人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想倾向的感染,从而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译介和传播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比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中,马克思写下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其中一段话的德语原文如下:Mit einem Worte: Ihr Koennt die Philosophie nicht aufheben, ohne sie zu verwirklichen.[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第3卷中的译文如下:“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4]另一段话的德语原文如下:Die Philosophie kann sich nicht verwirklichen ohnedie Aufhebung des proletariats,das Proletariat kann sich nicht aufheben ohne die Verwirklichung der Philosophie.其译文则是:“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5] 我们注意到,德语动词aufheben竟然全部被译为“消灭”。
由于这样的译文的影响,理论界有不少人撰文探讨马克思如何“消灭哲学”。其实,这根本上就是一个伪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所使用的德语动词aufheben主要来自黑格尔,而在黑格尔哲学中,aufhebe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它的含义不是“消灭”,而是“扬弃”。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在这里表明它所包含的真正的双重意义,这种双重意义是我们在否定物里所经常看见的,即:扬弃是否定并且同时又是保存。”③ 可见,在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马克思那里,aufheben无疑应该被译为“扬弃”,其含义是既有抛弃又有保留,而精通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事实上,年仅19岁的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就已经表明:“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6] 何况,青年马克思在学习法学时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的转移表明哲学对他的思想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我们上面提到的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在谈到法学研究中的感受时,毫不犹豫地写道:“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7] 即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只要人们认真研读上下文,也会明白,马克思根本不可能说出“消灭哲学”这样的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话来。实际上,在我们前面引证的马克思的两段德语原文之前,还有下面这样一段话:Die Emanzipation des Deutschen ist die Emanzipation des Menschen.Der Kopf dieser Emanzipation ist die Philosophie, ihr herz das Proletariat.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第3卷把它译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8] 从这段准确的译文中可以看出,既然马克思把人的解放的“头脑”理解为哲学,把人的解放的“心脏”理解为无产阶级,怎么可能去“消灭哲学”或“消灭”无产阶级呢?显然,aufheben只能被译为“扬弃”,而不能被译为“消灭”。
所以,上面提到的两段译文应该做如下的修改,第一段应改为:“一句话,你们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扬弃哲学。”第二段则应改为:“哲学不扬弃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扬弃哲学。”一旦翻译上的问题被纠正了,所谓“消灭哲学”也就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当然,我们这里关注的焦点不是马克思的这段话如何翻译,而是作为翻译者的主体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翻译?或者换一种提问的方式:在翻译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否纯属偶然?我们认为,这种在翻译的过程中把语词含义极化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层的原因的。事实上,主体之所以把aufheben译为“消灭”,因为他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想倾向的驱动。这一个案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帆风顺的。
就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即在把已经翻译或介绍进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也是充满坎坷的。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左”、右倾思想路线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思想路线也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9]这就启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旦主体的思想观念受到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错误的思想倾向的影响,中国化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一偏差的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就教条主义而言,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本本主义”。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小册子,严肃地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0] 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流行的这种以本本主义为特征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毛泽东主张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以便在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制定合理的斗争策略。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就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无论是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还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无论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等著作,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中,毛泽东这样写道:“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11] 在毛泽东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教条主义贻害无穷,只有彻底地抛弃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周密的调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就经验主义而言,乍看上去,它与教条主义正好相反,其实,它们是殊途同归,都属于主观主义的范畴。在毛泽东看来,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经验很丰富,这些经验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但如果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1942)中,毛泽东指出:“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12] 毛泽东认为,克服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倾向,不但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且要善于把实践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升到理论的层面上。比如,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毛泽东强调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3] 显而易见,朴素的经验主义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也是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尽管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它们在思想方法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党内的情况表明,教条主义比经验主义的危害更大,更值得警惕。事实上,只有坚持不懈地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展开积极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可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不泛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应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做出深刻的反思,而这样的反思正是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注释:
①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攻关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基本理论》(课题批准号:04JZD002)、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创新研究基地2005年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项目批准号:05FCZD008)、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3)和 2002年教育部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趋势研究》(课题批准号:02JAZJD720005)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③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5页。另外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又写道:“说到这里,我们便须记取德文中的Aufheben(扬弃)一字的双层意义。扬弃一词有时含有取消或舍弃之意,依此意义,譬如我们说,一条法律或一种制度被扬弃了。其次,扬弃又含有保持或保存之意。在这意义下,我们常说,某种东西是好好地被扬弃(保存起来)了。这个词的两种用法,便得这词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意义,实不可视为偶然之事,也不能因此便责斥语言产生混乱。反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语言具有思辨的精神,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参阅黑格尔:《小逻辑》,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3页。
参考文献:
[1][2][9][11][12][1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91、993、996、789、818-819、814.
[3]Marx Engels Werke, Band 1. Berlin: Dietz Verlag,1970:384.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6、214、214.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13.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编辑 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