摺刀的锋芒
宁 二
我还记得看到它的那一刻,黑色的磁带盒子藏在一架色彩艳丽、异族风情浓郁的英文游记手册中,灰头土脸。3年前,75泰铢,购自泰北清迈某间英文书店。作为旅游商品,它的封面过于素朴了:头顶黑底红字,“Karenni”,齐腰一道白线,“Songs from Karenni Refugees:Phary Reh”,岩洞占了底部画面,巨石重压的角落,是两个年轻人抱着吉他的背影。
背影中的一个,应该是Phary Reh,泰国夜丰颂难民营中的克伦尼(Karenni)族年轻歌手。“无国界之友”(Friends Without Borders)200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既极简主义又自然主义,泰国艺术家Suwichanon在清迈附近的夜丰颂旅行,听到了难民Phay Reh的歌声,深受触动,便把岩洞及竹屋当录音棚,用MD简单录音,做成了两把木吉他伴奏的《克伦尼难民的歌》,并英译了4首歌词。
《别担心,妈妈》《诺言》《我们的时代》《欢迎来到克伦尼》《牺牲》《别忘记》《伟大的母亲》《起来》《共同奋斗》《永远和你在一起》《朋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祖国》,12首歌的英译标题直抒胸臆,和所有思乡的歌曲一样,它们自顾自浅吟低唱诉说离绪,在哀伤中透露着身为跨国流浪者的迟疑和渴望。
一遍一遍,这些难民营里的抗议心曲听得久了,便似活了,像褪色的旗帜在细雨清风中飘摇。无论和中国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相比,还是和美国民权运动的著名抗议歌曲例如《We Shall Overeome》相比。寄人篱下的克伦尼年轻人的歌声都平静得像一把摺刀。“克伦尼,热爱和平的克伦尼,我们终将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多年血战之后,这群被缅甸军政府赶出故乡克耶邦的国际非法移民,刀锋向内,痛苦的锋芒只能割向自己的血肉。
“我们,高贵的克伦尼,有自己的国家;我们,高贵的克伦尼,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共同奋斗,美丽的家园终将回到我们的怀抱。”中南半岛山地民族温柔的个性与身为难民的无助混杂,恍惚中歌声竟似纤弱的啜泣,伴着熟悉的英美民谣节奏型,主音吉他的SOLO欲说还休,没有酣畅淋漓,没有大声呼喊,突然提高的音量像一个孩子拖着稚嫩声腔的怯怯求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来自缅甸的音乐。然而Phary Reh应该不同意人们将他的创作称为缅甸的歌。和掸人、克钦人、克伦人一样。近20万人口的克伦尼人一直试图民族自治,多年奋斗遭到缅人中央政府镇压,这些缅甸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几乎全部臣服,不屈服者要么还在山林里艰苦打游击,要么越过边境,逃到泰国,在受到严格管制的难民营里做卑微的无身份者。这亦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泰缅边境居然有近20个难民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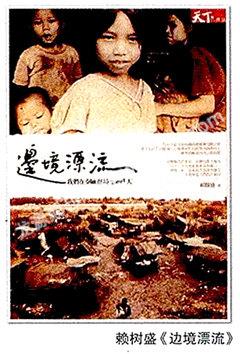
我不曾去过这些地区,媒体上,缅甸是比朝鲜还要神秘的国度。如果它殖民地的历史还能从乔治·奥威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缅甸岁月》中窥得一斑,那么如今在军政府控制下的缅甸便真如热带雨林,深幽、缄默和阴郁。在缅甸当大英帝国殖民地警察的5年时光,是奥威尔反殖民主义思想的起点,他对它爱恨交织。他曾以一位骄傲的白人的视角,描写了缅北曼德勒地区一场皮威戏表演:
“那死人般惨白的圆脸,还有僵硬的动作,都令她像魔鬼一样诡异。音乐的拍子发生变化,女孩儿用刺耳的嗓音开始歌唱。节奏快速扬抑,欢欣而又惨烈。下面的人群接着她的歌声,上百个声音一起吟唱起刺耳的音节来。女孩依旧保持那奇怪的曲身姿态,却扭过头去,撅起来的臀部冲向观众……”
这是我此前对缅甸音乐唯一的印象,来自高等白人的东方主义情调与撅起臀部所凸显的欲望想象。时空倒错,我不曾亲身了解缅人的传统,却先听到了反叛者Phary Reh的创作——若奥威尔还活着,他该如何理解一个在英国殖民者退去,却又为自己的缅人兄长内部殖民的克伦尼人的歌唱?
“妈妈,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想念你,我们天各一方,我想念你。妈妈,对你的爱我深埋心间,有一天,我一定会重返故乡……”Phary Reh反复吟唱着思乡的歌谣。据说在泰缅中部边境位于美索的克伦人难民营中,同样流行着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然而他们和克伦尼人一样,无家可回,“就算拿起枪杆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放下枪杆,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赖树盛《边境漂流》一书记下了这句克伦族前军官彭财的困惑。
身为白北海外和平服务团的成员,赖树盛在美索镇做义工6年,这部真诚之作详细描述了泰缅难民营的各种情况,若是把它和《缅甸岁月》对比来读,可窥得见缅甸大地百年的孤独。一个细节令人心动,他说,现在仍有缅甸境内的克伦族人将自己的孩子偷偷送到泰国的难民营来,为的,就是在难民营他们还能够学习克伦语,而不至必须接受大缅甸的同化教育。
又一年,我终于能去早已归顺中央的缅北掸帮旅行,在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景栋,买了两张据说是掸帮最流行的歌手的磁带。像一只装满美式音乐的音乐匣子,我们的车热闹地穿越缅北苍茫静谧的群山,布鲁斯、爵士、流行摇滚、饶舌、R&B,快乐的生活一一来过。“他们是掸人,但用缅甸话唱歌,唱的是爱情。”一听我提及昂山素姬和僧侣革命就禁口不言的掸族姑娘告诉我。那奇异的一路,我自然地想起了难民营里仍以母语歌唱的Phary Reh。
基于单薄资料与同情心的想象注定是危险的,但克伦尼语言细碎的音节和发闷的吉他绝非战斗的号角。“哦,我的爱人,我们永远在一起,让我们为了自由努力奋斗,未来就在前方……”纤细歌声中,我听得见年轻的Phary Reh一直试图让他柔软的母语再坚硬一点,而我知道,掩饰不住的迟疑和欠缺的果敢指向的,是他们无所期待的未来,无助的求告只静静通向Phary Reh充满恐惧的心灵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