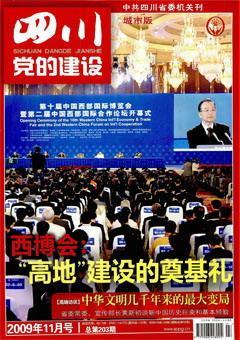“裸官”须严管等
华 晓
9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中纪委提出了近期反腐倡廉的五项具体任务,其中首次提到了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笔者对此是坚决叫好。
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民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说白了就是对“裸官”的管理。何谓“裸官”?裸官就是把钱财、妻儿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领导干部。自己则独自一人留在国内,“裸体”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就溜之大吉,潜逃到国外与亲友会合。
“裸官”之所以成为被监管的特殊对象,是因为“裸官”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已严重危害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据商务部2007年的统计,外逃贪官的总数已达4000多人,裹走了约500亿美元的财产,到今年人数更是增加到6万多人,而移民海外的“裸官”家属达到108万之众,每个人盗走的财产足可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坊问流传的“春眠不觉晓,处处贪官吵。夜来风雨声,裸官知多少”,是对这现象的辛辣写照。
“裸官”外逃的案例数不胜数:黑龙江石油原老总刘佐卿,向外转移资金1亿元后外逃:广东开平中行三任经理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盗走资金总计482亿美元后外逃;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被举报后潜逃美国;原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将10亿元汇出后,远逃加拿大“裸官”不除,国难未已。“裸官”潜逃到国外,大肆挥霍人民的血汗钱,业已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毒瘤。中纪委的决定表明了我党铲除这一危害国计民生、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毒瘤的决心。
治理“裸官”,关键是“以裸治裸”,以公开透明对付“裸奔”的干部。在我们现行的法律体系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早已存在,关键是要严格地予以执行!在1997年1月31日制定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也明确要求报告子女配偶出国境定居情况,但在实施过程中还缺乏一定的监督。
从监督的角度看,建议设置这样的一项规定,凡是需要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行使同意权的官员,必须公布配偶、子女的国籍(包括有无在国外的永久居留权),并就此报人大备案。对于那些“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裸官”,一律不予重用,尤其不能放到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岗位上去。
另外在出国的这一环节上,纪委和海关必须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民国(境)外出台更为严格的审核审计规定,尤其要对官员家属出国定居的经费来源进行深挖细查,从中发现官员贪腐的线索。
“裸官”须严管,中纪委的规定,反映了当前反腐工作的动向和特征,更是顺应了民意诉求,维护了公权力。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样的“紧箍咒”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反腐倡廉的制度创新,构建起完整的制度框架,通过具体制度来规范、监控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形成官员“不敢贪、不敢裸”的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宁静工作日”能为企业“挡拆”么
陈俊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今年以来,邻水县开展“企业发展环境优化年”活动,实行企业生产经营“宁静工作日”制度,深受企业的广泛欢迎。(2009年10月20日《四川工人日报》)
该县规定每月1日至25日为企业“宁静工作日”,在此期间,除上级安排的专项检查和县级涉及环保安全、治安、税收方面的检查外,各单位不得随意入企检查。同时,实行入企执法检查关口管理审批制度。各职能部门的入企执法检查,需报县政府分管县长批准,并到县监察局备案,持县政府纠风办开具的批准通知书和执法证件按规定入企检查。凡一个单位一年内两次出现违反上述规定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由纪检监察机关追究其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企业“宁静工作日”不是邻水县的首创,笔者在网络上搜索得知,此前河北冀州市、安徽明光市、陕西城固县、内蒙古扎兰屯市等地方都推行过类似的制度。所谓“宁静”,就是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受或少受外来干扰——主要是相关部门不必要的或违规的介入,能够专心致力于自身的发展。综合来看,各地的规定,主旨如出一辙,内容大同小异,显现出各地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的不当作为,以及由此酿成的不良后果,已广受社会诟病。在有的地方,三天两头下来的“检查”、“调研”、“收费”、“处罚”,名目繁多,层出不穷,既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因而,我省邻水县出台“宁静工作日¨制度,替企业“挡拆”,着力优化企业经营环境,其治理的初衷和决心值得肯定。如果相关规定能够得到切实执行的话,企业当可充分享受“宁静工作日”带来的惬意。
然而,在期待“宁静”的同时,我们对这种制度在实效性方面的隐忧也不可不察。比如,有些地方规定,在“宁静工作日”中,企业对不符合规定的“检查”或“收费”,可以拒绝或上报相关部门。但在实际操作中,那些可以“检查”或“收费”的政府部门,往往是“强势”部门。面对它们的要求,企业有胆量与之冲撞么?基于利弊衡量,企业会不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策略呢?如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式没有理顺,没有法治的保障,某些政府部门能免得了向企业“开刀”的冲动么?会不会制度出来时轰轰烈烈,过后就偃旗息鼓呢?另外,“宁静工作日”的设置,在阻挡干扰的同时,会不会也为些企业逃避监管、从事违法行为提供机会呢?
对照现实,制度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形或走样,应当引起相关方面的足够关注。必须承认,“宁静工作日”的出现,本身说明了在不少地方,相关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关系不太规范。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一些政府部门没有认清职责所在,没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好的环境,反而成为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麻烦制造者”。“宁静工作日”制度,试图为理清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提供一种途径,而其实际效果,也必将成为考量政府职能转变的某种标志。
(作者单位:大竹县柏林煤矿)
喜见劳务输出大省出现“民工荒”
张峰夏熊飞
民工荒,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是用工需大干求的种表现,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随着全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内地一些省会城市也出现了这种现象。9月2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四川也现民工荒建筑工月薪5000》节目,对四川的“民工荒”作了专题报道。
曾几何时,进城务工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不管是种了半辈子田的农民,还是刚初中毕业的孩子,都削尖脑袋想往城市挤,去追求一种比农村更好的城市生活,每年前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地务工的农民数以千万计。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涌入,导致用工供给严重高于需求,一度形成了“民工慌”——民工心慌找不到工作。
2008年的金融大风暴,使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无奈之下只好选择返乡寻求机会。而四川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进城务工的农民遍及全国各地,在金融危机中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自然也是十分庞大。
随着今年经济的复苏,各地用工需求扩大,可是却招不到充足的工人,为何往日农民进城的大潮没有再次出现呢?
农民工不愿再进城务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城市压力的加大,二是家乡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物价不断上涨,可是工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城市生活的压力不断加大。其次他们在城市很难找到归属感与获得认同,在各个方面都遭受着来自城市、来自城市人的歧视。再者进城务工将孩子留在家里,使孩子无法得到良好的照顾与教育
城市中的种种不如意,使他们不愿再长途跋涉前往务工,这是“民工荒”出现的一个原因。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农民工家乡的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我省城乡统筹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推进,农民工有了另外的选择,不进城务工照样可以过得很幸福,这就说明如今的农村已经大变样,也充满了机会。而素有“打工第一镇”之称的金堂县竹篙镇,今年有相当多的农民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就地就业,即为明证。
随着我省经济不断发展,四川已逐渐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最强劲的助推器。特别是我省提出“两个加快”以来,给广大农民工在本乡本土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这既是广大农民兄弟的迫切愿望,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为家乡建设出了把力,何乐而不为?
“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这是一种具有全局战略高度的举措,此举必将推动四川经济迈上一个全新的高度。随着我省“两个加快”不断取得新成绩,提供的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多、待遇会越来越好,我省也必将能够由大量的劳务输出转化为劳动力“自产自销”,这份宝贵的劳务资源,也将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