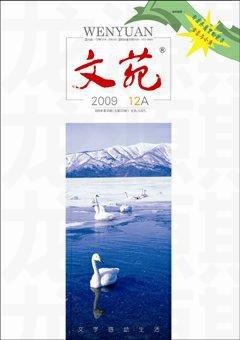老打字机前的爱情守望
梅 寒
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在1935年。彼时,他正在哥根廷大学学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租住的房子就在她家所在的那条街道。而她,正是他一位要好同学的房东的女儿。是受同学之邀前去拜访时遇上她的,那一年,她才23岁,正是美丽俏皮又略带羞涩的年纪。
最初的相识,不过限于彼此间淡淡的几声招呼。他们,并没有更深入的交流。那样不远不近的交往,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1937年,他开始写博士论文。那时,学校要求学生的论文必须要打印成稿才能交给导师,这让他犯了难,他不会打字,更没有钱去买一台打字机回来。她不知怎么就听说了他的困境,主动上门找到他。她说,她父亲工厂里恰好有一台淘汰的打字机,而她恰好想练习打字。那个主意自然让他喜出望外,但他的笑容很快又被一层淡淡的愁云笼罩:我没有多少钱,不过一个穷学生,给不了你报酬。看他一脸的窘迫,她调皮地笑:我的报酬,是要你陪我走遍哥根廷的每一个角落。也许,那时,爱情的种子已悄然在她的心里生根发芽。只是那时他还懵懂不知。
他们的交往由此开始。他埋头苦写论文,完成后看着她坐在打印机前“嗒嗒”飞快地打出来。“穿着玫瑰红的棉布长裙的伊姆加德,端坐在矮矮的长凳上,修长的腰肢挺直着,金黄的长发挽在脑后。她的眼神澄澈而欢快……”多年以后,当年一起工作的场景还在他的脑海中经久盘旋。那个场景,成了追随他一生的温暖回忆。
他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她每为他打印完一篇论文,他便带她到哥根廷的一个地方。晨光初显的街边,他们一起聆听过晨钟的清响;阳光明媚的午后,他们一起在广场上逗弄过可爱的鸽子;华灯初上时他们一起细数过一盏又一盏的街灯。整整四年,他数百万字的论文,在她的悉心帮助下,终于顺利完成。哥根廷的大街小巷,也因此留下了他们年轻快乐的脚印。情深不必言爱,纵不说,那份爱,还是悄悄地来了。
可那份爱,终还是不能说、不可说。满怀一腔报国志外出求学的他,纵有爱情温暖相伴,到底还是意难平。家贫国弱,有更重的责任沉沉地压在他的肩上。哥根廷再美,也只能是他的第二故乡。异域他乡,他常无端地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我怅望灰天,常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总还是恋着那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总还是要寻着自己的根回来。
他的归期渐近,她却一无所知。深夜的打印机前,她仍在兢兢业业地替他打印着文稿。离情却已在他的眼里泛滥成一片迷离的泪光,轻轻地搭了自己的手,在她的肩上:让我为你揉揉肩吧……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她没回头,可他分明还是感觉到了她的肩膀在轻轻地颤抖:留在这里,我也需要你,好么?
“这里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回到祖国去……伊姆加德小姐,一定有一个比我更好且更爱你的男子,他愿意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呵护你一生的。”他说这话时是1945年10月2日,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时间。
没有再挽留,纵心底被离别的痛填得满满。回转身,她给他一个带泪的微笑,又在他的文稿上轻轻地打上一行:一路平安!但请不要忘记。
就那样走,彼此没有再回头。此后,他归国,将全部的心思扑到自己钟爱一生的文化事业上。没有再去刻意打听过她的消息,也没有再给她任何自己的音信。不能深爱,莫如相忘。他以为,那是他能给她的最好的关怀。
他怎么会想到,当初那个痴姑娘,会把一生的岁月交给了思念交给了他。2000年,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导演要拍一部有关他的专题片,专程去哥根廷打听她的下落。竟然意外地找到她,还是当年的老房間,还是那台银灰色老旧的打字机,只是昔日的红颜已变白发,她的精神却仍然很好:瞧,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一直在等他回来。我的手指依然勤快灵活呢,我甚至还能打字!此语一出,前去探访的女导演已泪湿眼眶。
2009年7月11日上午九时,他,季羡林,一位备受世人敬仰的国学大师,静静地走完自己98年的尘世岁月,仙逝而去。而她,那位在大师的记忆里温暖他一生的德国女子伊姆加德,是否还守在那台打字机边痴痴地等待?结果已不再重要。从决定等待他回来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爱,已在她的生命里,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巨树,他来,爱在,他不来,爱,仍旧在。这样的爱,让世俗之人不敢妄谈爱情。■
(发稿编辑:刘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