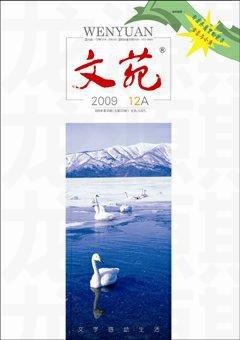一个叫“母亲”的人
罗伯特.万德斯里克
疗养院里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当我走在通往姐姐所住病房的长长走廊里时,这股气味紧紧地追随着我,中间还夹杂着从右边食堂里散发出来的感恩节大餐的诱人香味。终于,我转了个弯,走进了病房区。
这时,我看到一位用皮带束在轮椅里的老太太,她的身体僵直,岁月让她弯下了腰。看到我走过来,老太太颤抖着嘴唇含糊不清地咕哝着:“弗兰基,是你吗?弗兰基,我的宝贝儿!我的好孩子!妈知道你會回来的!”
老太太颤巍巍地伸出双臂,似乎要拥抱走向她的弗兰基,我看了看四周,走廊里没有别人,只有老太太和我两个人。我放慢脚步,小心地走向墙边,想从她的轮椅旁绕过去,但她挥着胳膊拦住了我。“弗兰基,我的孩子,”她说着,眼里流出了泪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在她的身边停了下来,俯下身看着老人历尽沧桑的眼睛。“我说过我会回来的,妈妈。对不起,让您等得太久了,但您看,我现在还是回来了。”我抱了抱她,老太太马上抱住了我,她心灵的空虚仿佛都在拥抱中变得充实了。
爱在老人的拥抱中流淌着,尽管她的身躯瘦弱不堪,在她拥抱着期盼已久的爱子时,仿佛又焕发了青春。她伏在我的肩头抽泣着,呢喃着只有她内心能听懂的话语。她紧紧拥抱着我,再也舍不得放开双手。
终于,老人伴着泪水从久远的回忆中回过神来,虚弱地说:“把我推回房里,弗兰基。”她用瘦骨嶙峋的右手指着路,我们找到了她的病房,屋里充满了母爱的温暖。墙上挂满了她年轻时的照片,正中央的一张已经发了黄的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士兵,照片上有一行字:“我爱你,妈妈,我会回来的。”下面是手写的签名“弗兰基”。日期是“1942年2月”。
在老人的梳妆台上有一面折好的旗帜,用玻璃纸包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方的镜子里镶着一张褪了色的信纸,上面写着“西部盟军电报……”我不忍看下去。
我的心里不安起来,想着各种可能。弗兰基经历了一场他希望结束的战争后回来了吗?或者是为了他的祖国、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妈妈而牺牲在战场?他知道妈妈有多爱他吗?今天是否就是他们母子分别多年后相约重逢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老人的名字,至今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弗兰基是被爱着的,他的妈妈能活到今天就是想告诉他这句话。几天后,老人在睡眠中安详地走了,她的心愿终于了了。我代替她的儿子对她说了一声“我爱你,妈妈”。无论弗兰基现在在哪儿。能抱着她说这句话是我的幸福,因为她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她是一个叫做“母亲”的人。■
(发稿编辑:宋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