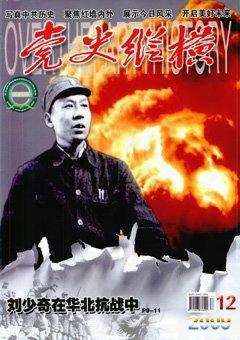44字中法建交联合公报的问世
于欣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分裂的同时,美法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中法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压力走到了一起。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公报极简短,中文仅44个字,却是两国幕后秘密运作艰苦谈判的结果。
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略封锁,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红色中国的关系。
戴高乐抛橄榄枝,秘派富尔访华
戴高乐将军自故乡科隆贝教堂村东山再起,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于1959年1月再主爱丽舍宫后,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推行戴高乐主义,维护法国及西欧利益,与美国相抗衡。他欲在中苏关系交恶之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升巴黎战略地位,于是委托参议员埃德加·富尔赴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作半官方试探会谈。富尔是法国前总理,曾于1957年访华,主张中法建交。
富尔以漫游亚洲四国为掩护,于1963年10月22日至11月5日在中国逗留15天,秘密和周恩来、陈毅六次会谈,并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与西欧大国、在联合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法兰西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正是新中国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富尔来访十分重视,决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与富尔的会谈;并指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
1963年10月22日上午,深秋的首都机场天高云淡。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情握手。中方早已知道富尔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探讨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的。所以,对富尔的来访给予高规格的礼遇。
在机场短暂的记者招待会上,富尔告诉记者:“此次访问纯属私人性质,绝不代表政府。”但在会后,他告诉张奚若:“我是受戴高乐将军的指令而来中国的,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周恩来精神饱满,微笑着与富尔握手。
“已经6年多了,总理一点儿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翩的周恩来。
6年前,作为法国总理的富尔曾踏上中国这块神秘而辽阔的土地。访华期间,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并与他多次交谈。也就是在这次访华时,富尔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富尔寒暄道:“总理到过巴黎?”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一句问话勾起了周恩来对往事的回忆。他何尝不想再一次踏上那块留有青春岁月的热土。但是在中法没有建交时,他只能把这个夙愿深深地埋在心底。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短暂的寒暄后,谈话很快转入正题。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这是一封特殊的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戴高乐知道富尔将同中国领导人接触,并且表示非常关注法国同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他在信中指出:“完全相信阁下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以及阁下听到中国领导人所说的。”
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是要避免一旦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的局面。
聪明的周恩来很快明白了戴高乐的“良苦用心”。他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看,随即又把信递回给了富尔,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
周恩来早已料到了台湾问题将是会谈中的最大难题。就跟打仗一样,他决定先扫除外围障碍。
“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周恩来提这个问题是试探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因为法国政府过去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西方一致,实际上是要服从于美国的指挥棒。
对此,富尔爽快地回答说:“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但富尔不愧为谈判高手,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
周恩来认为时机到了,应该明确我方的态度了。他坚定地说:“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13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派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时机成熟,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
对周恩来表明的这两点,富尔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但对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采取含糊的态度。
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决不迁就和退让。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把话题巧妙地调换了一个“角度”反问道:“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政府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听了周恩来这番坚定明确而又入情入理的话,富尔的口气不得不软下来。他连忙表示,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这些问题可以研究。
“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困难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13年。”富尔一脸苦相,“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个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富尔所说的“错误”,是指1949年法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周恩来展外交魅力,智破谈判坚冰
10月25日,周恩来在陈毅外长的陪同下再次会见富尔。陈毅与周恩来一样也曾早年留学法国,可以说也是一个“法国通”。
这次会谈一开始,周恩来风趣地对富尔说:“按中国的话讲,你现在是钦差大臣,你可以代表法国考虑同中国建交的方式。”
富尔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的问题,而是幽默地说:“我们正在翻越阻隔我们的喜马拉雅山脉,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险峰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跨越。”
周恩来知道富尔所说的“险峰”即指台湾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阁下及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
富尔此次访华是充满了信心、有备而来的,如果没有收获他将无颜向总统交代。他不愿意让会谈那么快就陷入僵局。这时,富尔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让中国人选择。中法双方关于建交方式上的分歧十分明显。第一个为无条件建交方案,因回避台湾问题,中方不能接受。第二个为有条件建交方案,因法方认为“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再同中国建交”实行有一定的困难,也难以接受。第三个为延期建交方案,富尔表示法方不愿走这条路。因而这三个方案都行不通,会谈陷入了僵局。
回到西花厅,周恩来思前想后,反复权衡,决定在程序问题上作适当的让步和灵活变通。一个新的方案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
10月31日下午5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走进北京钓鱼台宾馆15号楼,与富尔的又一次会谈开始了。
会谈一开始就直入主题。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三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这个方案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即富尔提出的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换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主动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上述两个步骤作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法代表看到照会后会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应相应撤回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员看待,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可立即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视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关于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略微变通了一下,即没有要求法方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方默认的方式代替。但在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上,还留有余地。
听了周恩来提出的建交方案,富尔不由得暗暗叫好,并对周恩来过人的外交才智由衷地敬佩。他高兴地说:“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
但是,对方案中要求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互派大使这一点,富尔仍面有难色。
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动断交,那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介石不动,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确立台湾地位,而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事实上,法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办仍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表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富尔的这种设想,周恩来早已考虑到了。只要法国政府坚持不承认台湾驻法代表的外交身份,不承认他代表“中华民国”,在断交的程序和方式上采取模糊的办法,是可行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一去,台湾的驻法代表会因得不到外交身份的承认而感到难堪,最终导致自动断交。
中法双方唱双簧,逼走蒋介石
11月1日晚9时,上海和平饭店。周恩来与富尔继续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根据双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了一个新的直接建交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1.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3.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周恩来宣读完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对这样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既合情又合理的方案,富尔觉得难以提出任何异议了。他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意见。”
接下来的气氛就活跃多了。
周恩来笑了笑:“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我将尽力而为。”富尔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大厅内的时针已指向22点。
“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文件给你,明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你,中午两位上海市长请你和夫人吃饭,一位是前任市长陈毅元帅,一位是现任市长。”周恩来告诉富尔。
“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富尔这句法国式的幽默把周恩来和在场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11月5日,富尔结束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中国之行,带着收获,从昆明飞往缅甸仰光。在那里,富尔给戴高乐写了一份报告,随即将报告连同建交方案交给法国驻印使馆的一名外交官,让他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
11月22日,戴高乐在巴黎召见了富尔。他告诉富尔:“我同意报告的结论,准备中法两国相互承认。”
1964年1月9日,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同法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雅克·德博马舍开始谈判建交的具体事宜。临行前,戴高乐指示德博马舍:我方或对方都谈不上有什么条件。因此,主要是确定建交程序,愈简单愈好。至于中方所关心的同台湾断交问题,可以表示:在法国同北京建交后,如果中华民国政府同法国断交,法国政府将采取相应的决定。关于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毋庸置疑,北京与巴黎建立外交关系本身自然包含新的根本性的因素,法国政府将根据形势发展在适当的时候确定其立场。
声明是中法双方唱的双簧戏,它是根据双方事先协商的口径发表的。在法方确认其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条件下,中方不再坚持法方以书面形式声明它的这一立场,而由中方单方面声明,法方予以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
1月18日,中法双方在瑞士经过四轮谈判,正式签署中法建交的协议。为照顾法国的体面,中方同意法方的要求,把确认双方建交的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
1964年1月27日凌晨,从亚洲和欧洲同时发出的两则内容相同的电讯划破了长空的宁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被称为“外交核爆炸”,不仅使美英等国十分尴尬,更使蒋介石恼羞成怒。他万万没有想到,戴高乐这位过去的二战盟友会如此之快且毫不留情地要离他而去。他责令“外交部长”沈昌焕:“娘希匹!巴黎欺人太甚,立即声明断交。”此举正中戴高乐下怀。法国立即响应台湾的声明,指出:“法国不久将与台湾断交。”
2月10日,台湾“外交部”宣布自次日起正式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走驻巴黎的“大使馆”。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他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
戴高乐突然离世,中国降半旗
1964年五六月间,中法双方互派大使,法国第一任大使是佩耶,中国第一任大使是黄镇。
中法建交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得到顺利而稳步的发展,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也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中法建交后不久,法国就出现了一股“中国热”。1964年2月,我国一个艺术团在法国访问时演出京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巴黎首次演出时,观众的掌声持续了5分钟之久。《法兰西晚报》称赞京剧融舞蹈、杂技、话剧、诗歌、音乐、艺术于一炉,真是“奇妙无比”。法国电视台专门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况,店铺里的荔枝和竹笋销售一空,有些旅行社着手组织法国游客去中国度假,有些地方还宣布要度一次中国式的周末。
中法建交,同时也把中法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距离拉得更近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控制和干涉的戴高乐十分赞赏。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曾讲到“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他说:“我是个军人,打过22年仗。戴高乐将军也是个军人。”1964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外宾时,称赞戴高乐为“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乐对毛泽东、周恩来也很尊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度,比历史还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自豪的人”。
在以后短短的几个月中,法国方面通过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表示戴高乐愿意访华的要求,但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在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上迈出第一步。自尊心极强的戴高乐怕给世人留下“屈尊就驾、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在中国,当时根据国际形势也有一条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互访,必须“他先我后”。为打破僵局,戴高乐先迈出了一小步。1965年,他派出了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马尔罗访问中国。戴高乐此举除了想加强中法政治对话外,主要还是想争取周恩来先访法,以便他下一年访问柬埔寨和日本时访问中国。
然而,此时的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忙于内政,难以脱身出国访问。
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建立区域”和“改革议院”两个法律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失败,不得不宣布辞去总统职位。戴高乐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后,访问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
1970年3月2日,戴高乐非常器重的老部下、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致信戴高乐,建议他访华。马纳克在信中这样写道:中国人总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于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7月,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们。对毛泽东来说,接见一个法国政府的部长,这是一个特例,全是因为戴高乐的缘故。在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的话题不时地停留在戴高乐身上。
参加会见的马纳克在7月30日给戴高乐的信中又特意传递了这个信息。他在信中写道:“你本人、你的榜样和你的行动,在所有的谈话中占压倒地位,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戴高乐将军感动了,他决心要去中国。9月8日,戴高乐对即将前往北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任参赞的外甥女科尔比说:“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
就在戴高乐计划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也正准备转达给戴高乐一份正式邀请书。为此,周恩来派了一位秘密使者到巴黎,这就是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
然而,就在邀请即将送达之际,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
1970年11月9日晚上7点25分,戴高乐将军因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而撒手人寰。这一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撰写他的回忆录。
中国政府惊闻戴高乐去世的消息后,决定以高规格吊唁,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悼念。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获悉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唁电中表示,相信“在戴高乐将军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法两国的良好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将会继续得到发展”。
戴高乐将军的宗教悼念仪式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举行,中国政府任命黄镇大使为中国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举办的这次悼念仪式。戴高乐的墓地上竖有两个写着中文的大花圈,寄托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戴高乐的哀思。
在北京,悼念的气氛同样是非常隆重的。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参加了使馆举行的吊唁仪式。中国还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
中国隆重而肃穆地悼念戴高乐的逝世,在法国官方和各阶层人士,特别是戴高乐的生前友好和家属中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戴高乐夫人发来的感谢电,电报说:“您友好的来电和悼念戴高乐将军的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真诚地感谢您在我的痛苦之中对我表示的同情。”
法国新闻媒介对毛泽东发唁电非常重视,法国电视台一收到毛泽东的唁电,立即全文播发,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态度”。其他的电台也反复播送全文,并且都在评论中说,在各国领导人的唁电中,人们特别注意毛泽东主席发来的唁电。巴黎各大报也以显著位置和醒目标题全文刊载,并认为这是中国“对一个西方世界政治家给予的史无前例的荣誉”。
对戴高乐生前未能实现访华的愿望,世界舆论普遍为之惋惜,这在中法关系史上留下了遗憾。但值得告慰的是,在戴高乐将军逝世后,中法友好关系继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