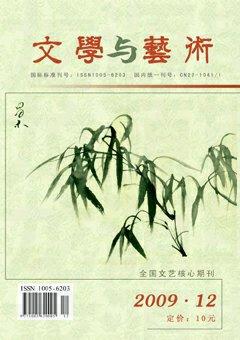灵魂皈依之所
穆国库
【摘要】北宋大文豪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才式文人。他的思想及人格魅力一直以来都影响着后继的学人,但他的一生多灾多难,在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中他找到了安放灵魂的场所——佛禅思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文学。
【关键词】苏轼;佛禅思想;灵魂皈依
苏轼一生膺服儒家,是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是以履行仁义忠孝、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为毕生志愿的。对如何治国平天下,他有自己的主张和抱负,甚至说带有一些理想色彩。他在应试礼部时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向往尧舜禹汤的“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仁义忠厚之道,提倡赏善罚恶以感化引导天下之人同奉“君子长者之道”,“归于仁”。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形势不如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论文中主张治国以“仁义为本”,强调德治、礼治,明确社会等级秩序“严君臣,笃父子,形忠孝而显仁义”,[1]但尽管如此,还应该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什么“醇儒”。他的思想发展情况如果非要划分不同的时期,那么贬谪黄州应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转折。黄州之前,其思想主要应在儒家范畴之内。经过了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在黄州闲居思过时开始以佛教的“中道”来反思自身,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向佛教靠拢的迹象。
从苏轼的诗文来看,在他此后的生涯中,不管是官居高位的短暂顺境,还是在贬谪到偏远的岭南、海南时的逆境,他总是对佛教禅宗怀有虔诚的感情,或是拜佛祈祷、或是读经写经、或是与僧人交游、或是书写表达佛教义理、禅悟的诗文、或是为寺院写记写铭、或是绘制佛像,直到从海南北归,一路所经过的佛寺几乎都留下了他参拜的足迹。这一迹象的发端不是从黄州开始的,在苏轼遭贬黄州之前,就已经有过与佛教徒的密切接触,在僧人中结交了很多朋友。二十岁时就与成都中和胜相院(后改为大圣慈寺)僧大觉怀琏、宝月惟简、惟度交往。应惟简之请于英宗治平四年九月,居家丁父忧时写了《中和胜相院记》。任凤翔签判是苏轼一生坎坷仕途的开始,此时他开始受同僚王彭(字大年)的影响研读佛经。[2]元丰初年知徐州时,他听从禅僧应言的建议凿清冷河口引水入废河道成功抗洪保全了徐州。他初入仕途,人生尚无多大挫折,对佛学之好只是初有兴趣、始知大略而已。作于湖州的《送刘寺丞赴余姚》诗云:“我老人间万事休,君亦洗心从佛主。手香新写《法界观》,眼净不觑登伽女”。表明他对佛经已经初有所悟,并且已经初露万事皆休、洗心从佛的心迹。“乌台诗案”是促使苏轼进一步接近佛家思想的重要契机因由。由于在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所以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参禅礼佛、结交寺僧。躬耕于东坡之时,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东坡居士”的雅号(所谓“居士”是指在家修行佛法的儒者)。据苏轼元丰七年(1084)四月即将离开黄州时所写的《黄州安国寺记》载,他在黄州期间已经真心地“归诚”于佛教,并定期到城南安国寺去,以佛教的中道、一切皆空的思想指导打坐、静思,以消除心中的郁闷和烦恼,求得内心的清净。[3]
在苏轼的一生中,他与许多大德高僧交往频繁。苏轼与东林常总禅师谈论禅法,对常总所说“无情说法”的道理进行了参究,有所醒悟,他将悟境以偈写出献给常总:“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这里体现出了苏轼很高的禅悟境界。有人甚至把苏轼归为常总的嗣法弟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苏轼著名的理趣诗《题西林壁》也是写于与常总的交游过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用禅悟的方法来解,就可以看作苏轼已经超脱于世俗人生之上,简单的诗句里满是禅家的玄机。苏轼和禅僧佛印了元的交往也为人们所熟知,甚至民间也流传了许多关于苏轼和佛印的逸闻趣事,且多是斗智和较量机锋的故事。而与苏轼交往最为密切的僧人当数参寥子,在苏轼的诗文中提到最多的也是这位参寥子。参寥子是一位著名的诗僧,苏轼与他唱和往还频繁,尤其在苏轼失意之时,参寥子的友情曾极大地温暖过苏轼。苏轼在谪居黄州时,隐遁山林的参寥子曾不远千里至贬所致问。苏轼守杭州时,参寥子又多次探望。在其著名的词篇《八声甘州·送参寥子》中,苏轼不禁感叹:“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此外,与苏轼交好的禅僧还有很多。与这些僧徒交往就不可避免地进行谈佛论法,加上苏轼的人生处境不断的恶化,而佛家所提倡的一些空静、中道等观念正契合了苏轼的困厄处境,所以很容易得到苏轼的接受认可。
苏轼学佛的最大特点是并不执意追求“信”与“不信”,而是既不盲目迷信,也不沉溺其中,他只是通过佛理进行思考,以求得对人生真谛的大彻大悟。他说得好,“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无所得故而得”,只有断绝一切功利之念,才能获得对佛理、对人生的彻悟。
在苏轼的诗文著作中不仅有相当数量的以佛教、禅宗为题材的作品,而且在创作风格、气势、情趣和意境方面,也能找到深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诗文。例如他有一首《西江月·过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这里既有对佛家术语的直接采用(佛家用“弹指”计量时间),又有对佛家空寂观念的引申与发挥。苏轼在这里凭吊恩师欧阳修乃是用达语表哀情,在佛法的洗涤下,这一世俗的师友之情得到了一种升华,升华到对人的生命本质的关怀。
“期于达”是苏轼潜心佛老所祈望的一种境界。所谓“达”,指识见通达而不滞阻,心胸豁达能因缘自适,乃至履危犯难而泰然自若。在苏轼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这种襟怀和修养是很突出的。苏轼在作品中常常因物兴感、即景生悲,又随手扫灭情累归于达观,自设矛盾,又自我解脱,不使自己走向颓废与玩世。例如《百步洪》由陶醉林泉胜景,进而感叹人世沧桑:“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上联正感慨陈迹尚存而人事已非,下联忽转入开解和自信。“但应此心无所住”即是《金刚经》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住”也就是板滞僵化,无所住才能达到圆通透脱。苏轼的方外友人释惠洪曾指出:“东坡盖五主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钱谦益也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4]上述二人都看到了苏轼艺术风格的个性特征,并明确指出他渊源于释家,这是很有见地的。苏轼善于把对各家思想的感悟融会到诗文创作中,他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佛讲“空寂”,禅讲“即心即佛”讲“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又讲“心即无心”;苏轼那些流传千古的诗文之中正是因为融入了佛禅思想的智慧,才显得那么空灵飞动。可以说佛禅的浸润不但安放了苏轼的灵魂,也成就了东坡的文名。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张晶,《禅与唐宋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