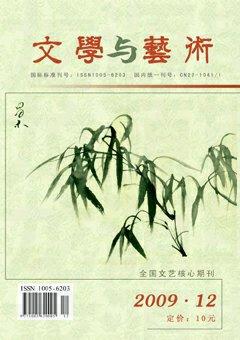失败的碰壁者——论池莉笔下的知识男性
郑 璞
【摘要】在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市民文化的冲击和抵御。面对现实,池莉作品中的男性知识分子大多显得迂腐,虚伪和不适应。知识分子的先锋性、精英性被世俗化消解。
【关键词】池莉;知识分子;男性
人生三部曲阶段,池莉小说描写的多是计划经济下几近停滞的人生景观。三部曲时期男主人公面对人生困顿,体现出安分守纪、坚忍宽慰的生活态度,他们是困守的一群。随着时代变迁,池莉作品中的男人对现实有了或是自觉的、或是被迫的突围意识。在突围的男性中,有一群特殊的人,那就是知识分子。之所以说知识男性是特殊的一群,是因为他们在承受着诸如女性的期望,物质生活的压迫的同时,还承受着九十年代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对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操守的检验。众所周知,池莉的作品褒扬市民文化,否定知识分子文化。因此,她笔下的知识男性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大多显得迂腐,虚伪和不适应。他们是突围的男人中落魄的失败者。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以一种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先驱的角色凌驾于一般庸众之上。知识分子不屑于某种具体目标的达成,他们热衷于对精神世界进行关照和反思,面对现实,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比如心高气傲、眼高手低、过于自矜自洁等等自身的弱点,甚至导致某些沮丧、彷徨、虚无情绪的产生。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感官享受、物质刺激、利益追逐冲击着知识分子艰苦而高深的精神跋涉。原有的价值体系迅速瓦解,以经济为本位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商品化成为肯定性价值占据着理想的地位,伴随经济地位的急剧下滑,知识分子不再以精神导师的角色出现。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是精神荒漠和信仰无序。这种不平衡的心态使知识分子的弱点暴露无遗。池莉曾批评知识分子:“他重在精神,自感是名士是精英,双脚离地向上升腾,所思所虑直指人类永恒的归宿,现实感常常错位。”[1]王朔就曾评判知识分子那种“无孔不入的优越感”,称“他们控制着社会全部的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2]
《口红》中的宁岸原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弥漫着温情主义和理想主义。宁岸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位人民教师,后任厂长,生活还不错。但改革开放之后厂子倒闭了,教师也当不成了,物质上的日愈贫困导致心态发生裂变:一方面为自己清贫为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而骄傲;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的想大把挣钱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文化比他低个层次的赵耀根的暴富极大的刺激了宁岸,他毅然下海。但下海之后他却事事不如意。市场这个瞬息万变耳虞我诈的大环境让他这个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最后一个孤傲的知识分子因无法面对失败而坠入吸毒、走私、赌博的深渊。宁岸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表现出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认的政治”。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就会成为一种压迫形式,他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而扭曲的承认不仅给对象造成可怕的创伤,并且会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3]拒绝“承认”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宁岸就是这样一个被拒绝者。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现代社会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严,具有了可以分享社会平等关注的可能。就像泰勒举出的例证那样,每个人都可以被称为先生、小姐,而不是只有部分人被称为老爷、太太。[4]但是这种虚假的平等从来也没有成为生活的现实,等级的划分或根据社会身份获得的尊严感,几乎是未做宣告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观念或不成文的习惯法。宁岸试图突围就是渴望自己被世人认可。
宁岸的失败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对世俗社会的不适应。现实生活使知识分子面临许许多多的困境和难题,无法规避,只有勇敢的面对。但令人遗憾的是,宁岸却选择了回避。将回避作为自己现实生存策略的宁岸,并非是对尚未认识到的现代商业社会的一种主动拒绝,相反却是精神上或物质上被现代商业社会撞得头破血流的一种被迫选择,于是这样的回避,带给他的是更大的精神危机——物质与精神自信的双重失落。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此后,文化精英所要面对的,已经由政治权威转为市场规律。对他们来说,或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没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导师心态,真理在手的优越感,以及因遭受政治迫害而产生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的一钱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唐·吉可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是因其‘道德、‘理想与‘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5]
在世俗化欲望的冲击下,如果说宁岸的突围经历着心灵挣扎和灵魂争战,体验着灵肉冲突和痛苦,那么《你以为你是谁》中另一个知识男性湖北大学的李教授就是完全自觉的被世俗文化同化。
小说中的李老师被刻画的穷酸迂腐可笑。他总是为自己的世俗生活寻找崇高的借口,打着形而上的幌子过着形而下的生活。居住在汉口洞庭里小市民圈子中的他多方论证自己与市民居住一起的理由 :一是他们都是革命工人的后代,而他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他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这里,而是为了“体验生活”。在这里“由于有了高级的精神生活,李老师的内心获得了平衡。他安心安意的居住在洞庭里16号,既学跳舞也学打牌,既敢喝高度白酒也敢唱它一嗓子卡拉ok,既愤世嫉俗也同流合污,比如不时接受陆武桥的邀请,去参加一些公款吃喝的饭局。……我不去我怎么深入了解社会生活及流行语言?怎么会认识海参和鲍鱼?鱼翅和燕窝?”他既得陆武桥的好处,又从精神上瞧不起陆武桥。“如果恰巧这时候陆武桥抖擞的经过他家窗前,他就会鄙视的低沉的说:‘不就是为了几个臭钱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除此之外,小子,你还有什么?”
对知识分子如此嘲讽实际上在大声呼告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他们丧失了按超越自我坚守真理的现实批判精神。按照路易斯·科塞的说法,知识分子不仅是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还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6]知识分子的要义是具有超越自我及其所属专业的公共关怀和为真理而独立不倚的现实批判精神。中国古代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有道统作为精神上的支撑,有学统提供知识和学理上的资源。他们有自我牺牲精神及使命感和责任感,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泰然处之。而大众的确对这两大传统敬畏不已,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物化时代、欲望膨胀、消费人生,说的重一点无异于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在时时撩动你的“本我”欲望,使你向人的自然本能、生命原欲滑落,甚至是一落千丈。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7]
【参考文献】
[1]池莉.《写作的意义》[J].池莉文集(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243—244
[2]王朔.《王朔自白》[c].文艺争鸣.1983(4)
[3][4]孟繁华.《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万方数据
[5]陈平原.《近百年中国文化精英的失落》[J].21世纪.1993(6)
[6]许纪霖.《另一种启蒙·自序》[M]花城出版社.1999.8
[7]阎真.《做人和当作家》[J].文学漫谈—名家专访.奥博教育网
作者简介:郑璞(1978-- ),湖南长沙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