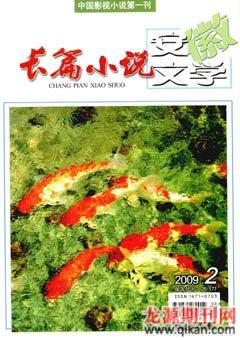流泪的舞蹈(外一章)
曾明山
解开的一袭长发,惊鸿照影,飞瀑流泻掩住了你削弱的一对肩头。
爱人,你长长的秀发挑逗着我的柔肠,心湖因你的飞扬而摇荡。你芬芳的发香让我在三月的风中神思恍惚,倾伏于这生命的青草之中,我为爱情感动得泪流。爱人,飘动的长发是抽自你体内的情丝吗?我甘愿作它俘获的一只青绿色的翠鸟。
翩然而起的蝶是我爱情的信物,旋于你的秀发之顶,静美成一只紫罗兰色的蝴蝶结。
不要回眸,爱人,不要那么美丽的一个转身,然后让风吹动你鬓云蔽月的长发,我将无法抵御你光彩照人的容颜。
一种什么样的黛眉儿?
春天在体内消消生长,你最初的舒展小心翼翼,柔弱地接受阳光之手的抚摸。一场春讯过后,你生长成为春天身上最传神、最动人心魂的部位。一叶黛眉儿是一个女人对春天和爱情的倾诉。清亮的眉眼在初春的河堤上守望,爱人,刚绽开柳眉儿的爱人,并不吝啬自己的身体,而渴望被爱情采摘。
柳枝儿轻俏地飞扬,是暖人的风禁不住你葱笼的绿意,还是你的心萌发如悠扬的笛哨?
我嫉恨这悠悠拂过你面庞的风,能轻吻你的一对黛眉,这穿过你衣带的黄莺,百转千声地在你的身边歌唱。
惊叹于你精致的眉,令我日夜揣想,那弯轻烟之下你风情万种的容颜。
牐
与一棵柳共舞,我感受得到你脉脉的爱意。用我刚性的手臂圈住你的柔软,爱人,你还有什么值得惊惧的。我们的枝条相交缠,叶叶相覆盖,我们的命运共同生长共同呼吸于一条绿堤上了。哦,我的爱人,我的双唇卷起如同一叶柳笛,日夜在你香软的耳畔歌唱。
我知道,你至媚的风骨最终会在某个风起的日子伤害我,我漂泊的爱情将会无法在你纷披的枝子上着陆。爱人,你每一次解怀而舞,都是对我心灵的一次重创,我无可回避,却不禁失声痛哭,爱人,我们爱情的种子不过是点点柳絮,把生生世世的诺言写在风雨里。
也许,只有在一次次的砍伐之中,伤口一次次结痂,血液一次次染湿罗裙,我们的爱情才能在另一片土壤里重绽新绿。
牐
是什么使得你们飞扬?一朵一朵挂着茸毛的泪花漫天飞舞,遮蒙了天空和日月。从来没有如此灿烂的飞雪,这三月扑面而来的柳絮,浪漫了一个春天的主题。是春天的白雪吗?呵,不,爱人,只有我只知道,这是来自你眼角中晶莹的泪花。当生命从一根攀折的柳条开始,女人,你卑贱而又顽强地生长在田畈溪畔,不求悉心扶持,但求与世无争。东风揉碎了你的身骨,一腔柔肠化作万千绿条,你终于以最美的姿态站成一帧风景。如水的柔情是你,轻狂也是你与生俱来,我美丽的爱人,可怜的爱人,世界上最美丽最辉煌的泪花,积蓄了太多的苦难与辛酸,而于此刻奔涌而出,你失声痛哭,漫天飘舞的泪花淹没了这天地。
几度飞花,渐吹尽枝头香絮。你最后的宣言逝于水中,浮萍是你的传说中唯一的踪影。
每一朵柳絮,都是一个关于爱人的传说。
江 南
大泽地人家
站在东洞庭湖西岸的土地上,望不尽的长江东逝水,到此驻步,倾吐出数以亿吨的泥沙,遂成大荒洲。主宰这片土地的,是千百年来自生自灭的芦苇。芦苇正抽穗拔节,莹润如玉,白发三千丈,密匝匝如坚固的长墙。太阳以一个大圆轮廓定格在亘古大泽的水天一色中,苍苍茫茫,照临古今几多慨叹。穿行于芦荡之中,心消融于类似北方红高粱的雄浑之中。在芦荡深处蓦见一户人家,我一如沙漠中发现绿洲的狂喜。房舍筑在土台上,土台完全是人力的创造。狗猛然叫起来,叫出了湖洲的荒漠孤寂。狗便以这种方式表达见到人类的欢喜。在土场上我见到一对夫妇,汉子的肌体乌金般厚重发亮,女人很俊俏,发梢上结着丝带,衣裳却朴实甚至粗糙。
这儿没有电灯电视,夫妇俩护理着这片芦苇,闲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女人问我:“你是从良心堡来的吧?”良心堡是百里芦荡中的一个小集镇。
“我从岳阳来,嫂子。”我说。
女人的目光就有些呆滞,望着白白的大泽出神,说:“做女时我也在岳州住过哩。”记忆便渗出了久久封闭的硬壳。花儿般年纪的她从那座古城走出来,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一群男人赤身裸体在毒毒的太阳底下,唱着淫邪的野曲,下半截钉在泥中埋植芦苇茎。他们把健壮的芦苇茎杆,削成一段三节,在新淤洲土上埋植。这种方法收效快,产量高,比自然繁殖要快三、四年。女人没有看到过如此原始的图画,脸蛋儿红了。第二年苇子长起来的时候,湖洲人的爱情也扎根了。
天黑的时候,蚊子没头没脑的闯入口鼻。我早早地钻进了蚊帐,哪里睡得着,听见女主人说:“叫他给住在城里的闺女带个信,也捎几尺缎子来做衣裳。”
“不有吗?都撂在箱子里。”
女人忽然抽泣,说:“有的,我还要。”
男人说:“公路快修进来了,到时到处是商场,有得地方你花钱。”
我的眼泪就刷刷流了下来。
南湖探幽
我到南湖是在秋天。客车在连接岳阳与长沙的通道紫荆大堤上奔跑时,车窗中的南湖就令我惊叹了。南湖水涨,紫荆大堤就像一条狭长的飘带漂浮在水面上。堤旁是垂柳,而水漫至离堤面二三尺处。丰腴而不觉臃肿,柔软而不生滑腻,没有一丝喧嚣和繁华,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南湖。
南湖是八百里洞庭的一个子湖,宛若一掌温润的碧玉遗落在洞庭身侧。山是青黛的,便如沉静的秋妇的眉,印染着渺茫的灰黑。水是冷清的,恰如黛眉下一泓秋波。黛眉因秋波而生情意,秋波因了眉峰而生精神。因此要看南湖水,不妨先看看南湖的山。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但巴陵山野的秋色,绝对是清,而没有寂寥;绝对是静,而非落寞。在初秋的日子里上得山来,走在齐家岭,亦或是姜家咀的山间小路上,“空山寂历道心生,虚谷迢遥野鸟声”,有一分空明,又有一分野趣。山很静,走在山路上,阳光也柔和,从三眼桥到齐家岭的一段路,皆淹没在高低的杂树里。间或有一箭风从林中窜出,撩起了你的衣裾,细细的甘味就弥漫了口鼻。向山中望去,路绕一个弯,没入了林中,而晚烟萦树,或有几个学子抱书而行。
所谓“秋水伊人”,水之秋色则不容分说,在初次凝眸时就浸入到你的身骨中去了。
生命的流水
在我面前摆着一盘植物,它枝条挺拨,发出碧绿的嫩芽,绽出缤纷的花朵。我认为它是一个物质构成,在大自然里它是一种存在,有着事物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由此得到的结论是:生命是一种存在,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归要消亡,因此生命是悲凉和无奈的。而活着的人们,无论贵贱贫富,都是这个世界上平等的一员,最终要如草木一样生生灭灭。在忧伤的河流之上,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影子:我是中国千百万群众中普通的一员,在劳碌的尘世中终其一生,曾经怀抱的理想和浪漫也许将渐渐湮没。
应该说,垂暮者对住落日感叹人生易老,从政者在风雨飘摇中觉察到政治角力的险恶,诗人对着落红哀伤青春不再。我们对社会,自然的认识就是这样开始的,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有欢欣喜悦,也有落泪惆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真切地体验生命,思考生命了。大自然提供了繁杂多样的事物供我们观察,对每一株植物或奔跑着的动物,我们都可以拿来作标本式的研究,体味生存的各种形态。
生命的流水昼夜不息,一个人是不可能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
生命是一个过程
生命是一个过程,一个在离开母亲的怀抱之后的故事。
任何一个流浪者,当他第一次踏上一片陌生的土地时,面对不同的风俗、人情和深层次意义上的文化心理、文化背景时,就不得不陷入到深深的忧伤中去。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情结,文化的、亲情的、环境的,心灵渴望摆脱,重新纳入到异国他乡的社会中去,思绪却屡屡在奔波、疲惫、失败亦或成功的喜悦之中,渗透着泪水回忆起故乡,这近乎是一种绝望的感觉,环顾四周,成功的欢乐在陌生的人群中降低了它的分量,忧伤却无人可以理解和分担。岁月流逝,流浪者铸就了两种迥异的情感和性格特征:坚强的外表和脆弱的心灵,两者的矛盾又使之呈现出浮躁、变异和反叛的悲剧色彩。流浪者都怀着美丽的梦,坚信远方可以找到自已的归宿,找到自已向往的生活,这种坚定的信仰使严酷的生活洗礼变成了一种美的体验和实践,或者说是苦难的体验和实践。在大自然和社会玩弄的游戏规则中,一个个悲怆、浪漫、绮丽的故事流传下来,中国的文化史因此而增添了色彩。
无疑,社会的迁徙有助于文化的交流,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迁徙就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进步,铸铁和凿井技术西传就是西汉时民族融合的一个结果。有理由相信,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延续到现在的民工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大迁徙,每年春运期间,经广州火车站北上回家过年和南下打工的人潮有上千万,广东一些较发达的乡镇,外来流动人口已超过了本地人口。不同的是,历史上的迁徙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扎根落户,融入到当地的土著中去,被当地文化同化或是改变当地文化。现代的大迁徙却是在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实现的,除了一部分人通过分配、调动取得当地户口外,大部分人只能作为暂住人口停留下来,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靠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谋生,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原籍地,这就赋予了善感的心灵以更多“流浪”的色彩,不被接受,没有故乡,疲惫的旅程永远找不到精神安憩的家园。
今晚,我是在一种十分真实的情感使然下写这篇文字,我时时陷入到深深的苦闷之中。我生于江南,长于江南,草长莺飞是我梦乡抹不去的风景,构成了我文化心态的原色。我无法抛弃我的故乡,更不忍心离开我年迈的母亲。在艰难的生活中,我愈行愈远我的故乡,但我不会回头。
责任编辑 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