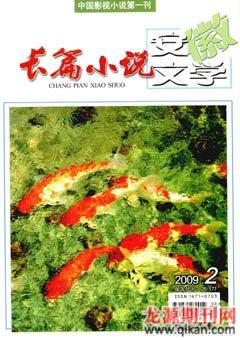母亲的心在天涯
对于母亲来说,我这个儿子也是一个很遥远的记忆了。
我从上海下放那年,父亲刚刚去世。我是瞒着母亲报名上山下乡的。走的那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母亲泪如泉涌,她无法想象十七岁的儿子在当时人称西伯利亚的淮北地区将怎样生活。母亲只知道我去的地方很穷,没有电,有时候煤油灯也点不起;红芋干是常年的主食;交通很落后,从村里到县城,要步行走三十五里。我离开上海的那些年月,她常暗自流泪。每每和邻居们聊天,我便是她永远的话题。好在她周围的邻居,几乎每家都有插队知青,都和她有同样的话题,时间一长了,倒也不怎么太伤心了。
那是个计划经济的年月,买东西几乎都凭票证。我家的香烟票、糖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几乎都归我了。也许是因为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外地吧,因此母亲常告诫我的姊妹们,说我够苦的了,事事都该让着我。也许是年轻吧,我对母亲给我的优待不以为然。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想我的。我只知道,每探亲一次,母亲就流一次眼泪;每分别一次,母亲在头天夜里就睡不着,流着泪帮我整理行装。后来母亲开玩笑地说,她的眼泪在我插队期间都己流干了。1976年母亲因病住院,手术后醒过来第一声呼唤的就是我的名字。那一刻,我的心被母亲的爱深深震撼了。插队的岁月里,我只知道自己在受苦,在经受磨难。言谈举止之间,好像全世界的苦难都让我一人担当了。然而,我有一刻能像母亲惦念我那样惦念她吗?
漫长的插队岁月终于过去了,我从阜阳到淮北,再从淮北到了白居易笔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古城宿州。我多次给母亲写信,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阜阳、淮北和宿州的种种好处。母亲半信半疑。我便竭力主张她来看看,年复一年的。忽然有一天,母亲愿意来我这儿住几天了。
母亲是由姐姐陪着来的。那一年母亲61岁,身体还算硬朗,她奇怪的是,我们这儿的火车站名叫宿县。我告诉她,宿州是刚刚成立的小市,和宿县在一起,上面还有地区。母亲不明白这些,她饶有兴致的东看西看。她看到的是完全不同于她想象的东西。八十年代初,刚刚成立的宿州市,还完全是小县城的规模。那时候宿州没有汴河路,淮海路也不过是一条窄窄的街。傍晚站在西关胜利路桥头往东看,路灯昏昏暗暗,整个城区沉寂在一片昏暗之中。对我的生活,母亲觉得还不错。我能吃上大米,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尽管那时候宿城买米买副食品都要票,但母亲仍然觉得我的生活并不比上海差。而姐姐却哪里都看不惯,说我这里活脱脱是个小县城。母亲就说,别挑剔了,这儿很好。
然而,母亲没住几天,却坚决地要走了,理由是,这里的公共厕所太脏。我无言以对,我觉得愧对母亲。一个小小的然而却关系到城市品味的公共厕所使母亲对我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我把小小的宿城夸过头了。母亲后来坚持要我回上海顶替她工作,与宿州的卫生太差有一定关系。
母亲的年纪一天天见老了。岁月的风霜逐渐染白了她的头发,她对我的思念常常在梦里。我在她的梦里还是小小的童年,还是小小的少年。一梦醒来,往往眼泪沾湿了枕巾。三十多年过去了,上海的兄弟姐妹都成家了,我的儿子也在上海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飘零在外的我依然是母亲的心病。然而,她不知道今天的宿州已经建设成了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上海有的我们这里都有,而我们这里的土特产上海却未必有。我的住房绝对比上海宽敞,而且绝对有卫生间!我对母亲说这些,她将信将疑,思绪还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记忆里。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鼓动下,母亲终于答应到我这里住几天。去年,她已八十有二,能吃能睡,身体依然硬朗。中秋节我去上海接她,我们上了卧铺,一觉醒来就到了宿州。母亲对交通的便捷无可挑剔。出租车经胜利路,过淮海路,到汴河路,一直到家,也不过十多分钟。母亲一路上惊讶不已:这就是宿州吗?过去的小县城到哪里去了?对我那虽然陈旧但十分宽敞的住房,母亲觉得真是不错。特别是对宿城的小吃,母亲更是赞不绝口。我陪她去超市,去广场。母亲很疑惑说,和上海一样啊!
然而,母亲却觉得孤单。我每天上班不能陪她,别人也难以在语言上和她交流;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知干什么好。每天晚上我不回来,她也不睡觉,就那么坐着等着。不知不觉,母亲就在我这里住了八个月。终于有一天,她提出来要回家,我说这儿不是家吗?母亲不以为然,她说在上海住惯了,在我这里找不到家的感觉。我这里再好,她也认为不是她的家,她看我过得很好,也就放心了。
“五一”长假时,弟弟从上海来接母亲,他惊讶母亲红光满面,竟然吃胖了。我把80多岁的母亲送上车。母亲没有了分别时惯有的眼泪,她抓住我的手说,你要多来看我啊。我感觉母亲的手很有力,真的很硬朗。
夜幕淹没了远去的列车,长长的汽笛声在夜空中徘徊。我怅然远望,突然有了种心酸的感觉。几十年两地的来来去去,几十年岁月的煎煎熬熬,熬大了我,熬老了母亲。母亲对她的儿子永远是无私的,而作为她的儿子却未必。
母亲的心在天涯啊!
作者简介 许桂林,作家,现居安徽宿州,著有《两个世界之间》、《永远的记忆》。
责任编辑 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