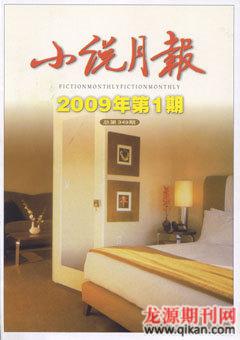端午诗篇
叶 弥
某年的端午节前一天,市电信局统一迁移了妨碍交通的电线杆,粉盒巷巷口那根粗大的木电线杆从此与这里的居民告别了。目击者说,这根原木的电线杆下端已经腐朽,它配不上粉盒巷了,早就应该换掉了。那几个换电线杆的工人还说。看吧,过不了几年,这地上的电线杆全都埋到地底下去了,你们一根都看不见的。
电线杆迁走那天,巷子里的住户脸上都带着微笑,只有燕婆婆是不高兴的。电线杆倒下的那一刻,她也在场,围着做饭的围裙,手指上还沾着面粉。两只眼睛吃惊地转来转去。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她终于张嘴发出不满的声音:“水泥哪有木头好?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原木?”
谁都没有理睬她。燕婆婆失神地转身朝家里去。经过一家门口,有一个比她还老的老头在晒太阳,她仿佛找到了能说话的人,站到他边上说:“你也知道的,1950年端午节,竖这根电线杆的时候,区长都来看了。多少人跑到这根电线杆下面拍照留念……多少人!你知道的。”老头看看她,语气尖锐地问:“你为什么要生气?”
燕婆婆的生气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她不会和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糟老头说。回到家,她洗掉手指上的面粉,开始大箱小柜地翻。到了中午,女儿燕兰回来了,她还在翻来翻去地找什么。燕兰看看厨房里冷冰冰的没动静,就问:“妈,中午了,小葫芦就要到家了。你还在找什么呢?”燕婆婆直起身子,急急地说:“我想起长顺的爸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就是1950年端午节那天,在巷口的电线杆下面拍的——我给他拍的。”燕兰说:“你又忘了,长顺爸爸死的那天,那张照片不是被你烧了吗?你动不动就忘掉。当时是怎样劝你不要烧的?……不过也不能怪你,你当时哭糊涂了。”燕兰做了一个鬼脸,“我看爸爸死时你也没这么伤心。”燕婆婆听了有些惆怅,半晌才说:“燕兰,这辈子我对不住三个人,一个是你爸爸,一个是长顺的爸爸,还有一个是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想了差不多四十年,才想出来答案。当初,如果我对得起我自己,就对得起你的爸爸,也对得起长顺爸爸……”燕兰打断她的话:“妈,你搬一个凳子坐下来说话吧。我去烧饭。”燕婆婆不满地喊了起来:“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话岔开来。我对你唠叨这些话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不要走我的老路。”燕兰举起双手朝母亲转过身来,表示投降。燕婆婆哼了一声,孩子气地说:“我才不高兴对牛弹琴呢!我把话说给你听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我自己。你要替长顺想想……替你自己想想。”燕兰想,唉!妈妈把一些老得掉牙的话每次都说得有滋有味富有新意,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燕兰急急急忙忙地和好一团面,揪出一只一只实心小团子,朝烧开的水里扔了进去,又扔进去青菜和虾仁。做好这些,她才对着锅子悄悄地笑了。妈妈的话她听了多少年,嘴上讲不爱听,心里却从未厌倦过。因为她每次听到的时候,面前总是浮现出一幅景象:一对父子端午节前一天的晚上到湖边去摘芦苇叶子,有时候还顺带着摘些野菖蒲。他们连夜出发,摇着自己“吱呀”作响的小船,摇到第二天的清晨,到达城边。父亲把船泊在码头上,拉着儿子一起来到粉盒巷。总是有一扇打开的门在迎接他们,也总是儿子拿着苇叶和菖蒲抢着走在父亲的前面。他们喝完女主人给他们准备的新茶,吃掉女主人做的馄饨,也不说什么话,父子两人就回去了。回到码头上,摇着小船往家里赶,家里还有一个女人不管多晚也要等着他们回来一起吃晚饭。
这对父子就是少年的长顺和他的爸爸。
在燕兰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长顺的那张脸,永远是清新的,淡得像烟的茸毛上带着早晨的露气,仿佛一棵小小的冬青树。后来这张脸渐渐拉长,又变圆,长出了胡须,爬上了皱纹,染上了风尘,还滋生了一些复杂的似是而非的神色。但是燕兰对此视而不见,她心里的长顺永远是清新的。
——锅里的团子烧开了,飘出了香味。燕兰回过头对母亲说:“妈,今天和你说句实话,虽说我现在离了婚,但长顺还有家庭。他的老婆要是到我的报社来闹一闹,我的前途就全完了。”燕兰好像不经意地与母亲的眼光一碰,郑重地停了一下才挪开目光。她的潜台词很明显,与感情相比,她更看重前途。燕婆婆带着哄劝的口气小声说:“哪里就会这样呢?……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后悔药很难吃,非常难吃。”门口响起一串脚步声,燕兰紧张地打断燕婆婆的话:“妈。快别说了。你听,小葫芦的脚步声。”
话音刚落,燕婆婆的外孙女雷晓薇在门口富有诗意地自言自语:“啊!我好像闻到了端午节的粽子香了。”走过她身边的一个孩子奚落道:“粽香在哪儿呢?没见过你这样的馋鬼!所以你胖得像只小葫芦。小葫芦,哈哈,小葫芦。”
雷晓薇的外号叫小葫芦。雷晓薇是个乐观主义者,别人叫她小葫芦,她从不生气,反而说这个外号太好了,听着让人浑身舒服。她的态度直接导致了这个外号的流行,流行到后来,连她的家人都叫她小葫芦。这时候她一脚跨进了门,脸上挂着微笑,显然对别人的奚落抱着宽容的态度。
居住在粉盒巷的人都知道,小葫芦最爱吃粽子。鸿兴福粽子店每天都供应大量的粽子,什么香肠馅的,蛋黄馅的,莲子馅的,栗子馅的,豆沙馅的,猪肉馅的……但是小葫芦不在乎粽子是什么馅,她在乎包粽子用什么样的叶子。她要的叶子长在长顺叔叔家门口的湖边。这种叶子包出来的粽子,哪怕是白馅,她也吃得有滋有味。燕婆婆说她这个习惯与燕兰一样,是从小养成的,改不了的。
每年刚到元宵节,小葫芦就盼着过端午节了。在她看来,元宵节下来马上就应该过端午节。过了元宵节,她会翻开日历,把端午节的那一页撕下来,藏到枕头底下。这个举动无非表达了一点:她热切地盼着端午节的到来。这还不算,快到端午节的那几天,她便理所当然地开始做吃粽子的梦,理直气壮地在梦里流口水。在那几天,粉盒巷的老老小小总会看到她的枕头高高地待在楝树枝上晒太阳,隔年的一串串黄色楝树子在枕头下面随风轻摇。谁也不会为此去责怪她,她今年过了年也才十岁。燕婆婆还会指着枕头上那个淡淡的似圆非圆的印痕对别人强调:“想粽子想的!”口气里充满爱怜,好像只有她家的孩子才会流口水。
小葫芦进来后,燕兰漫不经心地问她:“今天学校里有什么事?”小葫芦说:“学校里面没有什么事,学校外面有事——爸爸和他的新夫人等在学校门外看我,还有巷子口的电线杆迁掉了……阿弥陀佛!”她最后念的那一句佛号把屋里的两个女人惹得开心地笑了。
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两家人在意味深长地忙碌着。一家是长顺,他和儿子虎头照例会到门口的湖边采摘苇叶,顺带再采一把野菖蒲。土地里残留的农药过多,野菖蒲不如以前那么香。幸好苇叶的香味还和以前一样……还有一家是燕婆婆。吃好晚饭,燕婆婆就忙碌开了:先给长顺家里打个电话,既是确定一下明天一早长顺和虎头是否有时间进城,同时也是尽一下礼节。然后她照例要检查一下早就放在冰箱里的“明前”茶叶。这是特意留给长顺喝的,包得里三层外三层。她要打开层层包装闻一闻,判断味道是否还完好醇正。一切准备就绪,她才会坐到桌子边上,掀开盖在馄饨皮上的湿毛巾,开始包馄饨,这时候嘴巴开始忙起来了。她只管说,并不在乎有没有人听。小葫芦在她的小房间里做作业,燕兰骑着自行车出去买蜂蜜,大桥下面有一个养蜂人,他的蜂蜜是全市最好吃的。燕兰买完蜂蜜后还不会回家,当她回家时,她的头发一定经过理发店的师傅打理过了。
燕婆婆一个人坐在桌子边上包着馄饨,心平气和地说:“现在的事,想不通也要想通的。因为社会进步了。你看,木头的电线杆换成了水泥的,以后还要通通藏到地底下去。我当年在报社当摄影记者的时候,全报社就只有一架‘海鸥牌照相机。现在呢。燕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架进口相机。所以,那根木头的电线杆确实应该拆掉了,不能因为我在它下面给长顺的爸爸拍过照,就恋恋不舍。长顺爸爸死得早,他死的时候,城里和乡下还没连公交车站呢。现在倒好,长顺开着自己的小汽车,四只小轮子一滚,半个小时就到粉盒巷了。想当年,长顺的爸爸要摇一夜的船啊!”
她接着回忆当时的她如何在早晨的四点钟就起来包馄饨;燕兰的爸爸如何在这一天的早晨避而不见长顺的爸爸,他如何嘲笑长顺的爸爸是“土包子贾宝玉”;长顺和燕兰那时候如何两小无猜。可惜燕兰长大以后坚决不肯和长顺好下去,她说长顺与她差距太大,别的不说,光说一点,长顺在地里刨食,养得了她吗?这个小没良心的,从小就看出她心眼儿大。人家长顺现在是大厂的老板了。人家没忘了她,每年的端午节都带着儿子虎头来送芦叶和菖蒲……有情有义的,像他的爸爸。
这样没完没了唠叨着,不知不觉地燕兰已经回到了家里。燕兰对她说:“今天没买到蜂蜜,养蜂人被城管赶走了,说他的蜂蜜不干净。呸!我看到防疫站的几个女人老是去买他的蜂蜜呢。”燕婆婆刚才独自说了许多话,有些累了,不想多讲,就皱皱眉头表示不满。她抬起眼睛看看女儿,又皱皱眉头。燕兰顺着她的目光摸摸自己的头发,笑着解释:“回来把自行车放下,我走着去理发店。”她放下手,想了一想,满面笑容地说:“我还是去远一点的理发店,巷子里总有那么几个讨厌鬼,被她们碰见了又得说三道四的。”她所说的“讨厌鬼”是指巷子里的几个年轻女人,那些女人只要一看见她上理发店就会取笑她:“哎呀大记者,你也有时间上理发店来啦?是不是端午节到了,你家长顺要来了?”
长顺和她的故事巷子里的年轻女人们都知道,她们当着燕兰的面总是嘲笑她,奚落她。实际上她们私下都原谅她,羡慕她。照她们的话说,有这么一个男人一辈子牵挂自己,是福分。但她们又说,如果光为了感情拆散人家的一个家庭,是发昏。幸好燕兰从不发昏,所以她们从心底里佩服她。
燕婆婆说:“我看你也不要去理头发了——你光给长顺看自己的头发,从来不给人家真心。头发有啥用!”燕兰愣了一下,语气里有点不快:“妈,你懂什么?你不是总说你那时候很无奈吗?现在的女人比你们那时候还无奈呢,别看表面上女人一个个都很光鲜的。”说完她就走了。
燕婆婆对着手里的馄饨说:“啥?无奈?怎么一代比一代无奈呢?……”她一眼看到小葫芦走了过来,拉过她,真诚地对小葫芦说:“孩子,我看你跟虎头很般配的,以后就嫁给虎头好不好?”小葫芦大大方方地应承:“那好啊!我喜欢虎头!”这一老一小笑眯眯地眼睛对着眼睛,显出一样的天真。
电话铃响了。燕婆婆擦擦手站起来去接,她刚走到电话前,电话不响了。她愣在那儿,片刻,电话铃又响了,她一把抓起来一听,是长顺的妻子。长顺的妻子不停地抽泣,说的话断断续续。燕婆婆的听力本来就不好,这一下着急得把电话从左耳贴到右耳,再从右耳挪到左耳。小葫芦走过去抢了电话,自报了家门。等到长顺的妻子说完以后,她搁下电话对燕婆婆说:“我明天见不着长顺叔叔了。他犯了法,被公安局抓到杭州去了。”燕婆婆问:“犯了什么法?”小葫芦说:“虎头妈妈说,是钱的问题。……明天我也见不着虎头了,他不知怎样伤心呢!”
燕婆婆受了刺激。她受了刺激愈加不能控制自己的嘴巴:“你说长顺是个什么样的命啊?那时候你妈不要他,就是嫌他家里穷。现在他当了大厂长,有了那么多的钱,有别墅,有汽车。上次你妈跟我说,长顺手上的钻石戒指三万多块钱呢!光是一条鳄鱼皮带就是一万。钱多得坐牢去了……”
她自己也觉得话太多了,便甩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电话铃又响了,把燕婆婆吓了一跳。她跑过去拿起听筒,还是长顺的妻子。长顺的妻子,这个温顺的女人与刚才判若两人,在电话里大吼大叫。她的音量如此大,大得燕婆婆听得一清二楚。原来虎头不见了,长顺和虎头摘下的芦叶也不见了,就是说,虎头肯定拿了芦叶到燕婆婆家里去了。长顺的妻子最后愤怒地说,她的公公一辈子的心系在姓燕的女人身上,临了也没得到好果子吃。她的男人也是这样。她不希望她的儿子走爷爷和父亲的老路……这回是燕婆婆哭起来了,她扔下电话,仿佛长顺的妻子站在面前,她低声下气地唠叨说,当初她也硬着头皮扛到了二十九岁,心里想只要扛下去,父母兄弟没有了办法,也就让她与长顺的爸爸结婚了。没想到这件事让单位的同事知道了,他们对她说,你呀,好歹嫁个军官或者嫁个知识分子之类的,再不济也要嫁个工人阶级啊!一个记者嫁给一个农民,这是荒唐的。你看,就为了别人的一句闲话。
燕兰回来了,新剪的头发,脸上被电吹风吹得红红的。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她睁大好看的杏眼说:“我们每年也就受他一些芦苇叶子,与他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你们不要害怕。”燕婆婆嘀咕道:“我可没害怕。”燕兰摸摸头发,她的头发刚剪短了一些,正好披到肩膀上,经过理发师傅的调理,它蓬松温暖,乌黑发亮,散发出一股香味。燕兰懊恼地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犯法。对不起我刚做好的头发。”突然小葫芦说话了,在这之前她紧闭着嘴巴一言不发。她说:“你要是后悔了就去剪个秃子呀!”燕兰伸手打了她一下,生气地说:“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没教养。”
小葫芦朝后退了一步,但是她的双眼紧盯着燕兰,表明她现在正与母亲对抗着。燕兰上前推了她一把,说:“你傻不傻啊?为人家的事跟你妈对抗。我知道你是为那几只粽子,这样吧,我明天开车到湖边去摘些回来,让你外婆给你包几个。好吧?”小葫芦是个开朗大度的孩子,她马上点了点头,说:“好的。谢谢妈妈!”燕兰搂过她,说:“世界很无奈,知道吧?女人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难。唉,现在跟你说这些你懂不了的。”她转头吩咐燕婆婆:“妈,我到报社去一趟,处理一下事情,再把汽车开回来。等会儿虎头要是来了,让他等着我,我把他送回家。”
燕兰急急忙忙地走了。她是报社公认的能干女人,她现在就是副主编了,也许过不了多久她就是主编。她的生存状态也许有些问题,因为她经常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她四十岁不到,却有了更年期症状:月经失调,心慌气短。她每天都很累,食欲不振,性欲衰退。她看到的男人全是竞争的对象,只有长顺,在她想念他的时候,她还能感觉到心底里的温暖。但是就在刚才,她听到长顺犯法的一瞬间,她就与长顺彻底分手了。为什么呢?答案是:世界很无奈,聪明女人知道什么是不能放弃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
燕兰,总是被别的女人佩服的燕兰,是无比理性的女人。
小葫芦来到巷口,坐在石栏上,她要在这里等虎头。五月湿润的带着花香的空气让人很受用,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美妙幻想的世界,但是该发生的还是在发生着。
燕婆婆也来了,她给自己的头上扣了一顶黑色的绒线帽。这顶绒线帽太大了,显得她头重脚轻。她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她说:“电线杆搬走,真是好事情,你看看,巷口变得这么宽。什么都在变,就是我家的女人没变。”她思路一下子跳到很远,中间没有一点交代:“长顺的爸爸是四月份死的,那年端午节快到的时候,我还想,这个端午节燕兰吃不到长顺家的芦叶包的粽子了。没想到端午节的那天,天还没亮,门上就响起了敲门声。我一想,不好了,准是长顺来了。跌跌撞撞跑出去开门,正是长顺送芦叶来了,他一个人摇着船摇了一夜。他那年才十五岁。我后来对你妈说,你嫁给长顺吧!长顺多好?你妈那时候是十四岁,她也是像你那么说——那好!”燕婆婆虽说有气无力,还是唠叨够了才回屋休息,留下小葫芦一个人等着虎头。
虎头来了。他手里拿着芦叶,家里发生的大事使他情绪低落。今天晚上,公安局的人把他父亲带走后,他不想去上学了,也不想再去踢足球,更不想与任何一位女同学说话。但是他看见了地上的芦叶,就打定主意要进城去。他从小就知道,送芦叶到粉盒巷,对于爸爸来说是一件大事。他要替爸爸完成这件事。他拿了叶子,搭上末班公交车,正如他母亲猜测的那样,去粉盒巷了。
两个孩子相见,就像两片云碰见一样,是融洽而随意的。然后,他们说了一些话,一起来到家门口,放下芦叶,又手牵手地离开家门,出了巷子,渐行渐远。
在路上,虎头还在不放心地问她:“你真要去杭州看我爸爸?”
小葫芦说:“真!咱们去看他,还要给他买几只粽子去。”虎头说:“那你要逃学了。”
小葫芦回答:“要逃了。”
虎头现在完全听从小葫芦的指挥:“我们怎么才能到杭州?”
小葫芦胸有成竹地说:“咱们到码头上去搭船。有一年我爸爸就是从码头上搭船带我去杭州玩的。我还记得下了船在什么地方坐汽车到西湖。”
虎头并不问她到了西湖以后怎么办,是不是到了西湖就能见到他爸爸,而是为另一个问题担忧:“我妈说了,我爸爸出了事,你家会看不起我们的。我妈还说,你外婆耳朵根子软,你妈太讲实际。我爸爸犯了法,就不是一个好人了。好人和坏人是不能往来的……”
小葫芦果断地打断虎头的话:“虎头,别老说他们大人的事。”她脑中灵光一闪,说出一句深情的话:“大人才讲是非。我们小孩只讲爱情。”
原刊责编 刘建东
【作者简介】叶弥,本名周洁,女,江苏苏州人。1994年业余开始小说创作。著有小说集《成长如蜕》、《钱币的正反两面》、《粉红手册》、《市民们》、《去吧,变成紫色》、《天鹅绒》,长篇小说《美哉少年》。曾获得江苏省第一、二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一届蒲松龄世界华语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贞丰杯”短篇小说奖。作品入选多种年度优秀小说选本,并有中篇小说《小男人》列入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现居苏州。为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